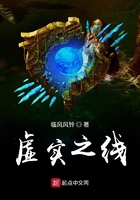从面店出来,我迫不及待地点了一根烟,为了让这根烟抽得闲适一些,我在店门口站定下来。临近子夜,就算马上飞奔回家,我也是个晚归的人。一个需要自觉地把被子抱到客厅沙发上去睡的人。一个第二天要看女朋友脸色的人。
街道拐弯处,有个身形瘦小的人寻寻觅觅地朝这边过来,走了几步,在一家已经关门的小店门口停了下来,脸朝我这边。他在暗处,我看不清他的脸,但我想他和我一样,都知道在一百米开外有一个家伙在看着自己。突然,他动作飞快地往墙上贴了一张纸,然后迅速掉头离开了。我对自己说,哦,一个贴小广告的人。
我走到小店门口,拿出手机,揿亮屏幕,照在墙上。
寻人启事
安天,男,71岁,如有见到者请致电:1391408XXXX孟慧茵
下面是一张头像照,一个戴眼镜的老头,表情严肃,尽管这张脸满满当当占了大半张纸,但看起来依然瘦削、干瘪。除了姓名、性别、年龄和联系电话,再无别的介绍,从文字透露的信息来看,寻人者似乎找人的意愿并不迫切,也缺乏诚意。没提酬谢,甚至连个“谢”字都没有。
我慢慢往家走,心里盘算着回头怎么跟女朋友解释晚归的原因。是讲实话呢,还是编个她更能接受的谎话?说谎话,意味着以后可能要用更多的谎话来圆。而说实话的结果,往往还是避免不了要用谎话来安抚被实话打击到的人。
没想到,我的女朋友竟然还没睡,就在门后站着,两条胳膊打着穷结,用那种我熟悉的犹如看一个陌生人一样的眼光冷冷地看着我,显得我之前的蹑手蹑脚十分可笑。我换鞋的时候,她就那样站着,两条腿微微叉开,僵硬地杵在我跟前,右膝盖上有一块淡淡的青紫。我缓缓直起腰,避开她的目光。她挡在我面前,打着穷结,一副不给出一个让她满意的晚归的理由就不让我进去的架势。
吃过晚饭,我没有洗碗。不洗是为了证明今晚我是在家吃的饭。昨天我的女朋友反复质问我,这个月,你在家吃过几顿晚饭?
快十一点了,外面淅淅沥沥地下起了雨,我的女朋友没有回来,也没打电话。她这是在报复我吗?或者经过昨晚的争执,她已经想好了一走了之。我打开衣橱门,她的衣物都在,常用的行李箱也在。我隐隐有些失望。
洗完澡上床前,我想了想,还是打了她的手机。她语气欢快地告诉我,今晚几个闺蜜聚会,刚结束,她已经打上车了,再有一会儿就到家了。她好像已经把昨天的不快忘记了。
在小区南门口站了二十分钟,我也没等到我心情大好的女朋友。我很想抽根烟,然而匆忙下楼,光想着要拿伞,连睡衣都没换,钥匙也忘带了。
传达室里的两个门卫正在热烈地谈论着什么,每次我退到传达室门口去看墙上的钟,那个鼻子上有颗大痦子的保安都会冲我点点头。已经十一点二十五分了,我怀疑我的女朋友可能已经从小区北门回家了。
在楼下,我摁了几遍我家的对讲机,没有应答。我想是不是做好挨骂的准备,胡乱摁一个别人家的,央求对方给开一下门,后来想想还是算了,就算上去了,也只是在家门口站着,还是进不去。
终于等来了一个晚归的邻居,我跟在她后面进了单元门。上楼的时候,这个胖胖的女邻居不安地回头看了我一眼,互相都觉得对方陌生。到二楼,我停下来,她继续往上走,拐上二楼半,她突然发力跑了起来,好像她刚逃过一劫,而危险还没完全消除。
我还是摁了自家的门铃,当然没人来给我开门,倒是屋里面我的手机铃声响了起来。会是谁的电话呢?我站在门口听完一遍手机铃声。当它又响起时,我确定这个电话是我女朋友打的。她就是这么一个偏执的人,如果别人不接她的电话,那她就会不管不顾地一直打下去。
我重又下到底楼站着,手撑住单元门,防止它合上。本来想巴结一下女朋友的,现在好了,连家门都进不去了。雨势渐渐大了起来,我近乎绝望地意识到我的女朋友今晚不回来了。看来只能去门口保安那里借电话打110喊开锁的人了。
传达室里,只有一个保安在,就是今晚朝我点过好几次头的那个。他正抱着一只带手柄的不锈钢锅在喝着汤水,锅有痰盂那么大,盖住了他大半张脸。我看见他的喉结动了一下,过了一会儿又动一下,与此同时,他的身体后仰,后仰,再后仰。
出小区往右大概400米,有个公共汽车站。已经过了运营时间,位于快车道和慢车道之间的站台上一个人也没有。灯箱广告上是正在上映的《归来》的海报,我一屁股坐在巩俐脸前的长条椅上。马路上的车不多,偶尔有一辆车经过,也是开得飞快。坐久了,我觉得自己像是被疾驰而过的汽车丢弃在这里的。而这辆车的司机是我的前妻。三年前,她无法忍受和我在一起过看不到前景的生活,一脚把我踹下了车,紧接着一脚油门,加速奔向了新生活。
一个尖声细气的声音在我身后用本地腔的普通话十分客气地说,你能再说得详细一点吗?我扭身,从两个广告灯箱间探出头去,看见一个个子矮小的老人正在打电话。我突然伸出的脑袋吓了他一跳,他短促地看了我一眼,往站台另一头走去。
回过身来,我还在想刚才那张脸,似曾相识,可那声音是陌生的。一个老头,声音却那么尖细,如果我曾经听到过,一定不会忘记的。
打完电话,那个老人从广告牌后走到前面,友善但不乏警觉地看了我一眼。他把手里的电话放进口袋,把伞放在椅子上,将斜挎在身上的包费劲地摘下来,也放在椅子上。他低头看了看,大概不满意这样的摆放,又把包拿起来放到远一点的位置,中间留出一个屁股的位置,之后才撑着自己的膝盖慢慢坐了下来。这一番调整似乎让他有些累了,他坐下后首先点了一根烟,抽了两口,定了定神,然后摸摸索索地从随身的包里掏出一支笔、一个小本,他把小本翻了几页,找到他要的那页,一边抽烟一边眯缝着眼往上写着什么。他和我之间隔着一条长椅,我从侧面又看了他几眼,最后确定自己根本不认识这个人。
不断有烟味往我这边飘过来,我把脑袋转向另一边,可烟味还是不依不饶地往我鼻孔里钻。一根烟抽完,他又点了一根。妈的,太过分了,看来这里是坐不下去了。在我经过老人跟前时,他把脚和前倾的身子往里收了收,同时抬头看了我一眼。这一对视让我想起来了,这张脸我还真见过,就在昨天,差不多也是这个时间。我还在犹豫,他忽然说,走啦?语气里充满了遗憾,好像在刚才过去的半个小时里,我们相谈甚欢,他还意犹未尽。
老头仰脸眼巴巴地看着我。他这是在等我的回答吗?不等我开口,他已经替我回答了,时间不早了,是该回去睡觉了。
我吃不准这个老头是不是需要帮助。我回忆着寻人启事上的信息,好像没有提到这个老头脑子有问题。但精神疾病这类病光看外表是不可靠的,就像我的前妻,一个在外人看来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女人,一名擅长和数字打交道的会计,你不能说她不正常吧,可如果她正常,那就是我不正常。
但是你怎么穿着睡衣就出来了?
是啊,我怎么穿着睡衣就出来了,的确是有些不得体,可我怎么会料到自己会如此这般地坐在公共汽车站?这个解释起来有些麻烦。这时他又及时地替我做了回答,是和家里人生气了吧?一定是,大半夜的,穿了睡衣出来,还能是因为什么呢。
我苦笑着摇了摇头,这个人真是的,被人满世界地寻找着还有闲情操不相干的心。另外,这样的声音从这么老的一个身体里发出来,总让人感觉哪里不对劲。
你摇头是什么意思?他把笔往本子中间一夹,合上本子,似乎有了要和我好好谈谈的意思,你摇头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你家里人贴寻人启事在找你吗?
和我估计的不一样,他一点也不意外,只是有些害羞地说,我知道。停顿了一下,他声音更轻地补了一句,寻人启事就是我贴的。
我能抽你一根烟吗?重新坐下后,我伸出两根手指朝他比划了一下。哦,可以的,当然可以的。他的反应有点令人费解的受宠若惊,好像我抽他的烟是很给他面子的一件事。他掏出的是我平时不喜欢的混合型的烟,不过我仍然抽得非常享受。他也点了一根,并不怎么抽,而是暗中打量着我。我被他看得很不自在。我猜他是在判断我的身份,同时等着我利用抽这一口和下一口之间的空隙向他提问。谁让我正抽着他的烟呢,我于是问到,你为什么要贴寻人启事找自己?
唉——,他长长地叹了口气,让我觉得他的回答也短不了。果真,他说,这个嘛,说来话长。他摩挲着手中的本子,似乎在寻找一个好的切入点。他摩挲了很久,突然劈头冲我问到,你父母都健在吧?
我点点头。
他们有多大年龄?
和你差不多吧。
他们关系怎么样?
还行吧。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兄弟姊妹几个?
我有些不高兴了。我只不过抽了你一根烟,就被迫提了一个你想要我提的问题,还回答了那么多我不想回答的问题。这算怎么回事。
你结婚了吧?有孩子吗?
这后几个问题我不打算回答,就算他把整包烟给我,也不行。我皱起了眉头,毫不掩饰我的不快。显然他并不需要我的回答,更没注意到我的脸色。他继续说,我的两个孩子和你差不多大,也都成家了,出去单过了,家里就剩我们两个老的。
其实很多我这个年龄的家庭都是这样的,本来也没什么,但我们家特别啊,不是我特别,也不是两个孩子特别,是我家老太婆。我相信全世界都没有我们家这样的,你要上我家看看,肯定会让你大开眼界的。
转眼间,他就将我的问题搁在一边,把我带进了他的家庭,想不进去都不行。
我和她结婚四十三年,前二十来年还好,就不去说它了。自从她退休后,我的噩梦算是开始了。一开始,她是和一帮和她一样闲在家的人出去烧香,走得不远,就在附近,当天来回,或者出去个一两天,我也就当她是出去散心了。后来,越走越远,出去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有时候一出去就是个把礼拜,家里的事一点都不管,也不拿钱出来,自己的工资烧完了,就烧我们的积蓄。
他的脸上和语气里渐渐有了怒气。
再后来,她简直像变了一个人一样,认了一个装神弄鬼的师傅,从此对烧香拜佛着了魔,每天家里都是烟雾腾腾的,把家里弄得像个庙。她还想把我拉进她的组织,做梦。我是什么人?
他把手里的烟头扔在脚跟前,伸脚使劲錽了几下。他的怒意已经扩散到了脚尖,那个香烟屁股被他錽成了碎末,好像那就是他老婆的组织,然后他语气坚定地对上一个问题做出了回答:我是个有自己的信仰和判断的人。
他的声音又细又尖,心平气和地说话时也就罢了,一旦有了情绪,嗓门高了,声音尖得就像是刀叉刮擦在玻璃上,让人产生不适感。我真想立刻站起来,走掉。但是他适时地递了一根烟给我,并且殷勤地帮我点上。好吧,我承认自己是个烟鬼,刚才那根烟由于离上一根时间太久,我抽得不过瘾。而且,他讲了一通,并没讲到点上,我没在里面找到必然的逻辑联系。另外,只要他不问关于我的问题,我愿意忍受这样的折磨,只是时间越短越好。
他也意识到自己的嗓门太高了,平复了一下情绪,恢复到之前那种虽然怪异我还能忍受的嗓音。
也不知道她用了什么巫术,家里的人都站到了她那一边,连孩子们也向着她,让我随她去,说她这一辈子吃了很多苦,不容易。可是谁的一辈子又容易呢?他的脸朝向我,面露愠色,目光牢牢地盯着我的眼睛,语气却是无奈的,带着一点急躁,小伙子,你说呢?
我心里一咯噔,这样的口吻,这样的眼光,我再熟悉不过了。我的父母不管一开始和我聊什么,最后总是会顺利地拐到无后为大这个话题上,说他们这一辈子不容易,到他们这个年龄,也没什么盼头了,无非是盼着能有个第三代,也算是对上头祖宗有个交代,末了,四道目光从不同角度逼向我,催促说,你倒是表个态啊。
我能说什么呢?我真怕这个老头接下来也这么给我来一句,赶紧点头表示同意。
我也不是一个不讲理的人,可做人做事要有个度啊,吃多了会撑,拉多了会脱水,不是吗?
我又点点头。
有时候我劝她适可而止,刚一开口,她就咪咪嘛嘛念一通经,求佛祖原谅我。笑话,我有什么可原谅的,真正该求得原谅的是她,不是吗?
我继续点头。
我算是受够了,我的忍耐也是有极限的,狗急了还会跳墙呢。
我当然还是点头,不过这一次是由衷的。
你看她把这个家都弄成什么样了。他的声音不自觉地又提了起来,你知道她这些年烧掉了多少钱?你肯定想不到,我来算给你看。不等我反应,他已经打开了本子,翻到最后一页。最后一页用过了,上面有字,他凑到眼前看了看,而后又往前翻了一页,那一页也有字,这一次他看了半天,又狐疑地看了看我,仿佛在回忆这些字是什么时候写上去的。我忍不住瞄了一眼,上面密密麻麻地写了大半张。他又往前连翻了两页,总算是空白页了。他拿起笔,往上写了一个数字,想想,又写了一个,并且在上下两个数字间加了个乘号,然后开始计算。他做得非常认真,嘴里念念有词的。
算出一个数字来后,他在数字外面画了一个方框,接着在边上又写了另外一个,并且跟我解释,方框里算出来的是什么,这一次算的又是个什么。给我感觉他要算的是一笔及其复杂的账,最终得出的那个数字一定是骇人听闻的,一定跟他的寻人启事有着必然的联系。
我的前妻在跟我离婚前也给我算过一笔账,为了让那些数字更直观,她用Excel做成了图表,打印出来,从那几根持续下挫的线上很容易看出她结婚后的各项指数一直在下降。
我的前妻习惯用账面上的数字来记录日常生活和归纳人生得失。她在单位做了多年账,另外还在外面兼职给两家小公司做账。当然做得最用心的还是家里的这一本,每月的收支结余,每年的投资盈亏,她都了然于心,过后还要做分析和调整。她和我结婚前认为我有可能是一只潜力股,而她当时已经三十三岁了,再不把自己抛出去,恐怕要变成垃圾股。事实证明,这是她一次失败的投资。她另一个特点是做事果断干练,一旦认识到自己的失误,当机立断改弦易辙。所以我们的婚结得快离得也干脆。
上个月,她突然给我发了个短信,要求见面,见了面先问我这两年过得怎么样,然后直截了当地告诉我,自己过得不好。示弱不是她的风格,就我对她的了解,示弱通常是她要提出让对方为难的要求的前兆。她言简意赅地回顾了自己离婚后的生活,情感和资产方面的投资均不顺利,尤其是前者。眼看着快四十了,深深的挫败感让她决定用余下的岁月做个长线投资,投资方向已经明确了,那就是生个孩子。说干就干,她环顾四周,比较各项数据,尤其是投入成本和风险,最后选定了一个知根知底的合伙投资人,那个合伙人就是我,她的前夫。
我的反应完全在她的意料之中,虽然急,她还是尽量控制着情绪,循循善诱地做说服引导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她还分别找了我的父母和她的父母,四个老人坐下来一合计,认为有个孩子,无论对她,对我,还是对于各自的大家庭,都是一件好事。
这几个礼拜,我三番五次地被她约邀到家里,商量投资事宜。我甚至没有勇气拒绝。因为我不去,她就该来登我的门了。反正我觉得她想复婚的决心和当初离婚的决心一样坚决。
算出来了,算出来了。老头把本子递到我手上。方框里的这个数字很长,我默默数了数,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是个七位数。
现在轮到我打量他了,我上上下下地看了他两遍,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家里可以拿出五百多万来烧的人。我提醒他,是不是算错了。他一听,不乐意了,从我手里拿过本子,说,就这我还是少算了呢。我再一次重新审视我身边的这个老头,瘦归瘦,却肤色健康,几乎没有老人斑,头发整齐地向后梳着,头顶微秃,两鬓略有斑白,镜片后的目光炯炯有神,至于精神,就更矍铄了。我完全可以确定,他不需要我的帮助。反过来,也许他可以帮我一个忙,把电话借我用一下。
可笑的是,她竟然说这些都是为了保家里人的平安,是替家里人烧的,可是谁让她烧了?他用笔尖一下一下地戳着本子上的数字,左边眉毛尾端的一根特别长的寿眉随着他说话的节奏抖动着,他盯牢我问,谁委托她烧了?
我怎么知道。我烦躁起来,这个老头问题怎么这么多。我没心情附和他,干脆提醒说,你讲了这么多,还是没讲为什么要贴寻人启事找自己。
他再一次露出羞涩的表情来,同时也不无得意,他说,我贴寻人启事找自己也是没办法的办法。我这哪是找我自己,是在帮她找她自己呀。我就是想看看,她心里还有没有这个家,有没有我这个老头子,还知不知道自己是这个家里的一分子。她该醒醒了,再这样下去,这个家真的只能拆掉了。
他进一步跟我解释,寻人启事上的照片和名字是他的,没错,不过留的是他老伴的电话。那个孟慧茵就是他老伴。他现在每天在外面晃,尽可能走远一点,想着总归会有热心人给她打电话的。这些天她去外地烧香了,他就是想看看他老太婆接到电话会不会马上赶回来,说着他脸上露出了狡黠的笑容。
又是一次艰难而漫长的恳谈,车轱辘话说了一遍又一遍,我的前妻也用最大限度的退让来表示她的诚意和决心。话说到最后,她抛出了一个新思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就是我配合她把孩子开发出来,复婚的事暂时不议,什么时候我愿意了,再拿到台面上来说。
从她家出来,她坚持要把我送到路口,并且更为坚持地要陪着我等出租车。她还有没表达完的诚意和决心。
夜深了,街上已经没什么人了。道路远处有一座桥,引桥末端的路面有几处不平,每一辆从桥上冲下来的汽车无一例外会在那里颠簸几下,从我这个角度看过去,很像是远远地在冲我点头打招呼。开得越快的车,头点得越是诚恳由衷。
出租车经过我常去的那家面店时,我让司机靠边停下。面店正要打烊,但老板还是动作麻利地给我下了一碗,我被迫跟着他下面的节奏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从面店出来,我迫不及待地点了一根烟,为了让这根烟抽得闲适一些,我在店门口站定下来。
连续多日的睡眠不足,加上抽了太多的烟,此刻我觉得头昏脑涨。想到回到家也并不意味着马上能躺到床上去,我更是感到浑身发软。我的女朋友和我的前妻从某种意义上属于一类人,偏执、任性、较真,只不过我的前妻要比女朋友冷静和世故。细一想,这么多年,在我生活中进进出出的女人好像都是这一类型的,好像我就是特别容易碰到这一类的女人。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我点点头,对自己说,没错,就是这样的。
那张寻人启事还在吗?我走到小店门口,揿亮手机屏幕,对着墙上,那张瘦削的老脸出现在光亮里的同时,我脑中灵光一现,闪过一个念头。由于激动,含在唇间的烟控制不住地抖动起来。
2014年5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