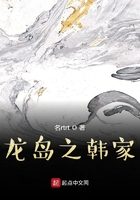我几乎是扶着门走进询问室的。
还没进门,我就感觉有了可以抓住的稻草,开始滔滔不绝的讲着我最近的状态,之后又为自己无法具体描述那种磨人的感受已经无法停止的思考感到懊恼,最后我干脆闭口,只字不提。
医生拍拍我的肩膀,告诉我没什么,大胆完整的说出来,这里就像一个树洞,什么都能装的下。可我哪里讲的出来?
见我不开口,医生开始问我一些专业性的问题,我回答了是与不是,随后让我做了表格。
我第一次见这些奇怪的题,每一题都是在询问我的感受,我记不得当时的感受,分不清上边所描述的严重程度应该如何分类,久久不能下笔。医生见状,又询问了我一些情况,并指导我做出选项。尽管如此,我还是不能准确的做出选择,磨蹭了很久,一咬牙,把不明情况的症状全部安排在了轻或没有的选项上。末了,我问医生,有没有能够停止思考的药,我每天晚上想到睡不着。
医生只是轻声说了句”不要急,也不要害怕,我会帮助你的。“便在病历本上“唰唰”写下几行大字。随后抬起头问道:“你现在什么想法?想要做出什么样的改变吗?”
什么样的改变,什么什么样的改变?我不知道生活还能变成怎样,能吃能睡不就是我现在所追求的东西吗?
我告诉医生,过去一周时间里,我茶不思饭不想,夜不能寐,即使我能忍受这样的生活,但我的身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不想让身边的人担心,不能让他们见到这样颓废的自己,仅此而已。
医生没有搭理我的话,仍旧问我你现在什么想法?想要做出什么样的改变?我感到有些崩溃,我已经将我所需要的东西完整阐述了一遍,至于感受上的东西,向来是十分模糊,似乎每日都只有一种感受,根本无法具体定义。我呆呆望着医生,再也说不出一句话。
他也没有显得不耐烦,又接连问了好几遍,最后在纸上写下几行药名,郑重的放到我手上,并告诉我如果想要变得更好,就必须听他的。
走出询问室时,我转头问了医生一句:“什么是不正常?我只是觉得生命不短,这算不正常吗?”
回校的路上,司机看到我手上提着的一小袋药,问了句:“去医院了?“
我点点头。
“年轻人,要注意保护身体,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就会发现身体大不如从前,很多事情就力不从心了。”
我笑笑,不再作答。童年的悲欢是何种体验,也已经记不清楚,它们又是否真的存在?大多数时候,我只是把压抑称为难过,头痛称作惊恐,这样的形容又是否有错?手上的药又是否真的能使我产生变化又会有何种变化?我不知道。
我不在乎生命能有多长或者多短,无论是二十年五十年一百年,还是七天,五天甚至一天,我只希望生活能够过的如同书本上所记录的那般真实的感受一遍,或许生命的长度本就不在于长短,而是取决于它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