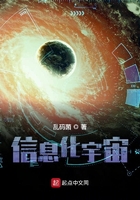一
我不知道我这算不算离家出走。
走出家门的那一刻,我妈其实在家。
我低低地说:“妈,我出去了。”
我妈当时正在电脑前看股票,听到我的话,头也没抬地说:“好,早点回来。”
我不动声色地转身离去,有种莫名的畅快。
我并没有打算离开之后再也不回来,我只是决心要用行动对她和爸爸做出抗议。
他们生了我,就不能放任不管。衣食无忧又怎样?别人养条小狗还会每天陪它玩耍、带它散步,而我的爸妈,我统计过,有一个星期我们见面不超过一个小时,说了不到十句话。
十八岁,有些人已经独立,可我还努力地想从父母手中汲取温暖。
不是不可笑的。
可我真的想知道,我对他们到底有多重要。
我背着背包,抽出手机卡,自北向南,一路走一路玩,十八年来,第一次尽情地享受自由。
然而很快就陷入困境,大手大脚惯了的我根本忘了规划自己那不多的出走资金。在乘船来到这个名为海安的小渔村后,我发现,找遍全身口袋和背包,我也只有十元零五角钱了。
为了给爸妈增加难度,我一直用的是好友小米的身份证。我们都是瓜子脸、扎马尾的少女,不仔细研究根本分辨不出。短时间内,相信他们很难找到我。
打电话向他们求救?不不不,那我出走这一趟还有什么意义!
面对蔚蓝无际的大海,我突然意识到,这一趟出走,已经变成一场冒险。
二
正午时分,送我过来的船已经离去,海边空无一人,咸腥的海风阵阵袭来,明晃晃的太阳照得人睁不开眼睛。我坐在树荫下,摸出最后一块巧克力,小口小口地吃掉,只觉得异常珍贵。
我的十元零五角钱是最后的救命稻草,绝对不能花在吃饭上,或许我可以拿着它解决今晚的住宿问题;或许明天我可以努力讲价,用它回到城市,找到取款机,让小米打钱救济我;又或许,这就是我自主创业的基金……
这样想着想着,我竟然渐渐睡去。
我是被一阵嘈杂声吵醒的。
我睁开双眼,一双双乌黑明亮的眼睛将我吓了一跳。见我醒来,他们一哄而散,嘻嘻哈哈地跑了开来。
大庭广众之下睡着,还被小孩子围观,我不由得脸红,摸了摸嘴角,还好还好,没流口水。
此时已经是傍晚,远处的海平面被夕阳染红,我抱膝坐在树下,阵阵的海浪声让我忽然有些恍惚。
出来这么多天,他们有没有发现我不见了呢?他们着急吗?他们开始找我了吗?还有,他们会内疚吗?妈妈会流眼泪吗?
应该不会,我还没见过她流泪。
这样胡思乱想的时候,那群孩子又回来了,他们之中,还拥着一个男人。
那人剃了一个非常短的头发,皮肤是古铜色的,高大健壮。他穿着一件橙色运动T恤,无论是外形还是气质都不似当地人。
我忽然明白孩子们为什么带他过来了,我连忙站起来,冲过去,兴奋地开口道:“你好,我叫叶景怡,从C市来的,你呢?”
他忽然定住,一言不发地看着我,神情有些飘忽不定。
就在我小心翼翼地想要再次自我介绍的时候,他忽然脸色大变,转身便走。
“喂,你别走啊!”我急得直跳脚。
可是他已经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好远。
我瞠目结舌地转过头,不解地看向旁边的孩子们,可他们显然也不明所以。
真是个怪人!我沮丧地坐下,翻出手机,犹豫着要不要向小米诉苦。
孩子们对我的手机产生了兴趣,我索性找出游戏,教他们开赛车、打小鸟。
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睛让我一时间忘了自己的处境与烦恼。
显然,我又做了件不太明智的事,因为手机很快就没电了,这就意味着,我想打电话找人求救也没办法了。
三
天色转暗,孩子们渐渐散去。有个小姑娘低声细语地邀我去她家吃饭,我犹豫了下,还是拒绝了。我教他们玩游戏又没有什么企图,这样冒冒失失地跑去别人家,别人家长肯定会觉得我不怀好意。
看了看宁静的海面,我站起来,脱了鞋子,挽起裤腿,走向海中。
海水比想象中要凉一些,海浪不断地拍打着我的小腿,非常舒服,我不由自主地又向前走了两步,思考着下海捕鱼的可行性。
身后忽然传来踏水的声音,我还没来得及回头,一股大力忽然将我向后拉去,两只手臂紧紧地箍住我的腰,飞快地将我拖到岸边。
色狼!我脑中顿时冒出了这两个字,然后大声地尖叫起来。
“闭嘴。”身后的人喝道。
我愣了一下,而后更大声地叫起来:“救命啊!救命啊!妈妈,妈妈,救我啊,我不想死啊!”
奇怪,在这样的时刻,脑中能想到的人只有妈妈。
那人忽然僵住,松开了手臂。
我的双脚已经回到了沙滩,刚得到自由,马上转身向他踢去。
儿时爸妈没空管我,专门把我往培训班送,跆拳道我当然是会的。然而他的反应也很快,迅速地抬手抓住了我的脚踝。
月光下,我看清了他的脸,瘦削的面容,高挺的鼻梁,一双剑眉,眼中有尴尬。
是那个怪人!
电光石火之间,我反应过来。
“你以为我要自杀?”
他松开我的脚踝,表情有些不自然。
我扑哧一声,哈哈大笑起来。
我一边笑一边说道:“你的想象力也太丰富了,我要自杀也不会跑到这里来啊。不不不,我才不会自杀呢,活着多好啊……”
他面容一滞,转身便走。
我忽然意识到,得罪他对我一点好处都没有,何况,别人刚刚是真心来“救”我的。
我连忙收敛了笑容,追上他,扯住他的衣角,哀求道:“恩人,我错了,我不该笑你。恩人,恩人,你不能不管我啊!”
他终于停下脚步,转过身来,问道:“你来这里干什么?”
“来旅游。我在海港附近闲逛,有人拉我坐船,说这里很好玩。”我老老实实地答道。
他不置可否,但眼中的神色显然在说“白痴”。
我讪讪地假装没看见。
“他们说你在海边待了一下午。”他又问。
为了面子,我不愿说是自己没脑子花光了钱,于是我眨了眨眼睛,可怜兮兮地说:“我钱包丢了,没钱住旅馆。”
他的神情没有改变,语气却终于缓和了一些:“把东西拿着,跟我走。”
终于有救了,我松了一口气,连忙穿了鞋,提起背包跟在他身后。
不知道为什么,我相信他是个好人。
他带着我一直向渔村后的山上走去。
山路并不崎岖,然而我依旧走得气喘吁吁的。我们走了没多久,他忽然转过身来,伸出手:“包给我。”
我顾不得客气了,连忙脱下背包交给他:“谢谢。”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我觉得他走得慢了许多。
又转了几个弯,我发现前方渐渐亮了起来。
我跟着他向亮灯处走去,原来是几幢小楼,一阵花香传来,越向前走便越浓郁。
我吃惊,难道他是隐居山林的富豪,我有这种运气?
然而大门口那块牌子很快便解答了我的疑惑——邵氏疗养院。
建这个疗养院的人眼光真好,这里气候如春,空气清新,依山傍海,与世隔绝,真是个疗养的好地方。
“阿霖,这么晚才回来。”门卫跟他打招呼,“哎,这是谁?”
他跟门卫简单地解释了我的来历,门卫笑呵呵地看了我一眼,便放我们进去。
原来他叫阿霖。我看了他一眼,猜想着他的身份。该不会是疗养院的院长吧?
他似乎明白我的疑问,但并没有出言解答,而是带我上了侧面那栋楼的三楼,打开一间名为“义工房”的房间:“这是我的房间,你今晚先睡这里。”
原来他是义工。看起来冷漠僵硬的一个人,竟然会来做义工,真是让人好奇。
房间很小,干净简洁,我刚刚走进去,他便关门离开了。
这天晚上,我躺在陌生的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
想到这是那个人的房间,我忽然觉得双颊烫得不得了,连忙用手捂住脸颊,闭上眼睛,强迫自己入睡。过了许久,我才终于陷入梦境。
这是我在邵氏疗养院的第一晚。
四
是的,我留在了邵氏疗养院。
我告诉他们自己已经大四了,没有课,愿意留在这里帮忙。事实上,他们也缺少帮手,所以我便很顺利地留了下来,还分到了一间自己的房间。
白天的疗养院真的像某个富人的别墅,三幢红顶小楼相互依偎着,泳池在阳光的照射下波光粼粼,院中大片大片盛开的杜鹃花让人有种置身花园的错觉……到处都可以休息,树荫下有沙发,泳池边有躺椅,还有一架紫色的双人秋千立在花坛边,随风晃动。
说是疗养院,可这里更像是一个养老院。住在这里的人全都是上了年纪的女性,老人会有的小毛病都有,但真正重病的人很少,所以两名医生也应付得过来。
她们大都保养得当,举止得体,外貌和同样年纪的普通老人相比年轻许多,而自理能力却远不及她们。
我猜想这些人应该非富即贵,所以才能承担疗养院的高昂费用。
住在隔壁宿舍的护士小敏证实了我的想法,然而她说完又有些不屑:“有钱有什么用,要么没有子女,要么和子女不亲近,亲戚朋友又不可靠,终究要在这种穷乡僻壤的地方度过余生,不到读遗嘱的时候,子女们是不会来的。”
我恻然,这里真应该展示给那些忙于赚钱而忽略亲情的人看,尤其是我的爸爸妈妈。
据小敏说,这里的鼎盛时期,每一个老人都有两个看护。可过不了多久,很多人都耐不住寂寞离开。后来也有人被高薪吸引过来,却鲜少有人留下。久而久之,老人们也都习惯了,院长索性把多出来的钱捐给了村里的学校。
我看着小敏年轻秀丽的脸庞,忍不住问她:“那你为什么留下来呢?”
她非常坦然:“曾经有看护在病人死后得到了大笔的遗产,我伺候赵太太已经三年,我相信她不会亏待我。”
我一时说不出话来,忽然想到,他呢,他留在这里,是为了什么呢?
我已经知道,他的名字叫唐霖。
我们每天都见面,却鲜少交流。
他似乎跟每个人都保持着距离,这里的工作人员跟他都不熟,却俨然以他为首,有什么事,总有人说去找下阿霖。
电灯坏了,去找下阿霖;今天的菜送错了,去找下阿霖;李太太发脾气摔东西了,快去找阿霖……
我见过他和老人说话的样子,面容柔和,低声细语,非常有耐心。
有一次,我看见他背老人上楼,步伐缓慢,小心稳妥,时不时还轻声跟老人说笑。
我不由得震撼,立在原地,久久没有移动。
他的外表和他的内心并不相符,我从未见过这样善良的男性。
我不好意思直视他的面容,却忍不住追踪他的背影。他站在我身旁时,我总会假装若无其事地低下头或转过脸。他一转身,我连忙抬起头,紧紧地盯住他高大的背影。他从来都只穿义工服,橙色的,温暖的。
我以为他肯定在这里待了很久,后来才知道,他也只比我早来半年。
他像一棵树木,沉默稳重,仿佛永远立在那里,让人觉得格外安全。
五
我的工作不算困难。
并不需要照顾老人们的饮食起居,只要每天陪她们说说话。
给张太太读报纸,给李太太读小说;有人信佛,便陪她念佛;有人信耶稣,便陪她读圣经;有人要聊天,便陪她聊天。
所谓的聊天其实更多的是倾听,她们并不在乎聊天的对象是谁,只需要倾诉。
年轻时曾得到多少倾慕,先生曾多么爱她,儿女刚出生时有多么可爱,打退小三时有多么果断……不同的人生,相同的晚年。
儿时的我也常一个人对着洋娃娃讲话,我理解她们的寂寞,所以愿意陪着她们。
她们有些人的先生已经过世,有些人的先生已经找到了更年轻的伴侣,但她们却依旧冠着夫姓,愿意别人叫自己某太太。
她们对过去付出了太多的感情,所以不愿开始新的生活,宁愿在这座花园里度过晚年。
而这里的院长,他们都称她为邵太太。据说她也住在这里,我却从未见过她,我猜想她也拥有一颗寂寞的心。
我给她们介绍近期的电视剧,原本矜持且疏远的太太们终于一同坐在大厅里看电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讨伐出轨的丈夫,鄙夷懦弱的妻子,咒骂阴险的小三。
有位老人不解:“前妻不过换了发型,转变了风格,他怎么就不认得她了?”
有人突然答道:“因为他从来没有爱过她,他最爱的是自己。”
看,谁说老人不是一座宝藏。
于是我待她们更加用心。
我教她们斗地主,输的人要用口红在脸上画画,连麻将桌上的老人们都被吸引过来,结果我这个师父被画得满脸都是,哇哇惨叫。
我不经意地转头,唐霖竟然站在门口,眼中有隐隐的笑意。
我连忙抱头鼠窜,留下身后一片笑声。
当晚,吃饭的时候碰见他,我假装若无其事,他却突然在我身旁说道:“脖子上没洗干净。”
我大惊,连忙拼命地擦脖子,待看到他上扬的嘴角时才明白,他是在开玩笑!
我先是板起脸,然后自己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开始我觉得他是一个怪人,后来又觉得他是一个好人,现在,我发现,他也会开玩笑,他也是个普通人。
我觉得我们之间的距离近了许多。
六
是赵太太最先点明了我的心思。
那一日,我坐在她脚下的草坪上替她读报。眼角的余光突然捕捉到一抹橙色的身影,我不由自主地转移了视线,忘记了手中的报纸。
片刻之后我才反应过来,连忙转回头来,却发现赵太太笑吟吟地看着我。
“你对阿霖……”她说。
我想都没想便否认:“不,怎么可能?”
她摸了摸我的头,掌心温暖:“我不会看错的,小景怡,你喜欢他。”
我顿时涨红了脸,依旧摇头:“我怎么会喜欢他呢?他多大了,三十岁?四十岁?不不不,他比我大那么多,我才不会喜欢他。”
“年纪大又怎么样。”李太太突然从树后冒了出来,“我老公比我大二十岁呢,爱情分什么年龄。”
“对,景怡,喜欢就要努力地争取。”张太太也不知从哪儿走了出来。
老人们渐渐地都集中过来,面带笑意地鼓励着我。
“可是、可是……”我讷讷地说,“他那么成熟,我觉得他不会喜欢我。”
李太太扑哧一笑,轻轻地点了点我的头:“傻孩子,相信我,他看你的眼神与看别人不同。”
“真的?”我惊喜。
“对,我也发现了,阿霖一看见你眼神就柔软了许多。”有人信誓旦旦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