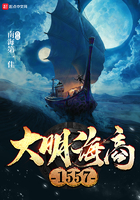“郎君事务繁忙,闲下能想起妾身已是万幸。”韩语蓉青葱手指交叠,声音轻快,已没了初见时的幽怨与压抑。
荀谌顺势握住她手,两人于亭中安坐:“蓉儿琴艺高明,就连我这粗通音律的人都觉得涤荡心灵,只可惜方才只听到一半,语蓉可否为我再弹一曲?”
“郎君所愿,不敢辞。”言罢从荀谌的咸猪手中抽身而出,又坐于琴前,指尖拨弄下一曲《阳春》带着扑面的春意而出,让人听之眼前浮现万物回春,清风和荡之感。
荀谌闭目,手在膝上打着节拍,他后世听惯了所谓电音摇滚,这极为冲和的古琴曲倒是有种千帆过境后的返璞归真。
一曲罢了,余音未绝,当荀谌睁开眼时,韩语蓉已凑到近前看他如痴如醉的享受神情:“郎君若是喜欢,日后蓉儿每日里都为郎君弹上几曲。”
荀谌见她面容隐在黑纱之下,心中一动,便探出手去将黑纱拨开,他到现在都不知道他这未婚妻子长相为何,好奇心一起便不可收拾。
韩语蓉躲之不及,被荀谌一招得手将黑纱掀开,一张精致的鹅蛋脸显露在荀谌面前。
明眸皓齿、琼鼻高挺,齿贝微咬唇下,似嗔非怒地盯着荀谌,长相颇有荀谌想象中那种大家闺秀的古典美感,尤其眼角一颗泪痣让人我见犹怜。
“郎君去冀州袁公手下与谁学的轻浮。”见黑纱已被掀起,韩语蓉干脆取掉黑纱斗笠,其梳垂鬟分肖髻,结鬟于头顶,余下长发垂下束起,宛如燕尾垂于肩上。
荀谌又不是未经情场的菜鸟,他顾左右言道:“我去冀州一去四五年,未曾见得蓉儿,近来又领了曹公之托,将行徐州事,这颠簸流离许多载,蓉儿竟连真面目都不肯示我?”
闻得此话,韩语蓉声音也低落下来:“郎君此去徐州,不知多久才能再次相见,是蓉儿考虑不周。”
荀谌牵起她手,撑开油纸伞,两人出了凉亭漫步在春雨中,春雨打得伞面淅淅沥沥,荀谌将伞往她那边一倾,任由春雨落在右肩。
“我此去徐州身怀重任,蓉儿放心,三五年内我必定将你从韩家接出。”
韩语蓉将伞面扶正,又往荀谌这边挤了挤,油纸伞本就不大,她见雨淋湿荀谌,却是甜蜜又有些心疼。
“郎君建功立业正当时,不必顾及儿女私情,家国为先,蓉儿自会在颍川等候郎君锦衣归来。”
肩膀接踵摩挲,透过单薄的衣物能隐约感受到对方的体温,雨幕中四下无人,唯有两人在雨幕中的模糊身影。
少顷,雨势变小有将歇之势,两人已步行到河滩滩头,前方停靠着早已备好的游春小船,荀谌转身正欲说话,谁知韩语蓉也转过身来开口,所距不过尺寸。
此情此景,荀谌往前微微探头,韩语蓉缓缓将眸子合上,两人唇齿相合,在这将歇的春雨中,只有掉落地上的油纸伞才最为孤独。
片刻后两人嘴唇分开,韩语蓉羞得背过身去脸色通红,荀谌只得拉着她上了小船,解开系在滩头的船绳,一撑竹竿,将船给荡入河中。
为了不留电灯泡,荀谌租船时给船夫放了天假。
小船五脏俱全,荀谌在船坞中烧了木炭,任船随波逐流去,他与韩语蓉两人在船坞中烤火,毕竟刚忘情之下也将衣衫给淋湿。
荀谌将外罩的轻衫给褪下,放在炭盆旁烘烤,韩语蓉在旁双手捂眼,只手指间露出几条足可见到其黑亮眼瞳的缝隙。
见她在一旁眨巴眼睛,荀谌伸手又要去帮她烘烤衣衫,她侧身一躲:“郎君不用管我,衣衫一会儿便干了。”
荀谌仍坚持道:“将外衫褪下我替你烘烤,若是得了风寒可不易好。”他意识中又不是见胳膊见肉的程度,哪用得着如此羞涩。
韩语蓉见他坚持,这才小嘴一瘪小心将外衫褪下,自己缩在炭盆另一侧盯着荀谌脸庞:“郎君去了冀州,就像换了个人一样。以往只会说些之乎者也的大道理,也不通情趣,像个榆木脑袋,现在却...却这般大胆。”
荀谌心道可不就是换了个人,他伸手凑近炭盆,感受木炭带来的余温:“蓉儿,今日下雨,所以我未将纸鸢带来,明日里我派人将亲手做的纸鸢送到你府上,也算是我的一份心意。”
韩语蓉听得此话,从腰间掏出一个锈有鸳鸯的香包递给荀谌:“郎君有心了,这是蓉儿闺中绣的香囊,里面都是些安神的草药,郎君每日里劳于心计,带此香囊愿郎君睡得安稳。”
荀谌接过香囊,上面针线细密,一见就是大家手艺,正是一副鸳鸯戏水的图样,见荀谌望来,韩语蓉又欲盖弥彰:“只是恰好挑了这副样式,郎君切勿多想。”
荀谌一刮她琼鼻,见得船外河中杏花花瓣随水流去,忽而道:“落花是否有意随流水?”
韩语蓉也望向船外碧波,怔怔出神道:“落花有意随流水,流水是否有情?”
“自是有情,流水潺潺携落花远去,离了尘俗纷扰,也不知要看尽多少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