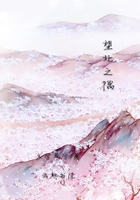周子兰一路追着阿生,渐渐来到了人声鼎沸的静陀寺门前,静陀寺在红霞山的山腰处,好在红霞山并不陡峭,山路十分缓和。不过一路未停歇的周子兰,此刻双手撑着膝盖,半伏着身子喘着粗气。
这小偷偷了东西,还以为他会往人迹罕至的穷头末巷里逃,想不到竟然还往多人的地方凑,才智如此堪忧居然还敢出来混小偷。
一路上山旁边的道路,挤挤挨挨停满了雕花马车,偶尔有新的马车过来,因寻不到停靠的地方,待车厢里的人下车后,又缓缓往前驶了过去。
静陀寺数人高的朱漆大门阔然向外开着,如同一头猎兽张着口,把过往的香客们迎了进去。寺里钟声悠扬,屡屡烟雾在寺庙的上空打着转,旋即消失。
周子兰自然知道今日是观音诞,所以对静陀寺此刻的热闹景象并无太多意外。
阿生与周子兰在隔着数丈远的地方互相对视着,谁都没有上前一步,亦无后退半步,如两只对峙咆哮着正在酝酿往上扑的狮子。
阿生忽地一个转身,游走在人群里,没入浪潮中,一眨眼的功夫,眼前的黄毛小子竟不见了,周子兰一边往前扒拉开人群,时而被熏香迷了眼睛,待寻回眼神之时,便彻底不见了阿生的去路。
该死的,她的菜钱,摸摸衣摆,发现自己两手空空,才记起来刚刚追的路上竟把今天早上买的菜食都给扔了。周子兰跺跺脚,欲哭无泪。目光触及人来人往的香客,只得咬牙往回走。她不愿待在这里,起码今天是不愿的。昔日的许多手帕交,挚友,十有八九今天会到静陀寺来上香祈福,她不能让她们看见她这个样子,自从嫁到京郊之后,她们就没有再与她有来往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规则是不会改变的,打从她下嫁那天起,就已经退出了京中贵眷圈子了。
周子兰刚迈开步子,就被一个高瘦的身躯挡住了去路。
她下意识抬头,入目是一张慈善的面孔,道姑发眉皆白,眉稍细长,顺着眼角垂着,高瘦的身架穿着宽大的袍子,颇有几分仙风道骨的味道。
“道姑让下路吧。”周子兰以手遮脸喃喃道。她得赶紧离开,不能让人给认出来。
“夫人今日是遇上什么不顺心之事?”道姑单手执掌,另一只手拿着佛珠,缓缓开口道。
周子兰撩了撩眼皮,看着道姑半眯着毫无焦距的双眼,确认对方是在与她说话,嘴里哼道:“我再不离开此处,恐怕还会有更多不顺心的事。”
道姑握着佛珠的手轻轻抬起,挡了周子兰的去处:“我猜测夫人今日不顺心之事跟钱财有关。”
周子兰猛然看向说话之人,下意识问道:“道姑怎么知道?”莫不是胡说的吧。
“夫人就不想知道如何破解灾口,取回钱财么。”
本来周子兰就在心里自认了倒霉,此刻听到说还可以拿回她的菜钱,双手拽着道姑急问“仙姑可是有办法?”
道姑心中冷笑,方才还毫不客气地叫她道姑,转头又改口叫仙姑了,世人还是愚昧啊,她不是什么仙姑,她只是收人钱财,替人消灾罢了。有个小丫头给了她一两银子,让她把这位夫人引到寺里的解签处,一两银子呢,这得化缘化多少天才有的数目。
“出家人不打妄语,夫人请随贫尼来吧。”
周子兰看了看周围的香客,确认没有眼熟的面孔,这才跟着道姑往寺里走。
走到解签处的花木桌子旁边,周子兰一屁股坐在小杌子上,迫不及待问:“仙姑现在可以说了么,我的钱袋子在哪里。”
这道姑要是说出让她先掏银子出来,她才给出锦囊妙计之类的话,她就掀桌子,别真以为她是涉世未深的姑娘。只见对面的人笑而不语,打着手势指向她的腹部,她顺手一摸,竟发现荷包又回到她身上了。
周子兰腾地一下站起来,带翻了身后的小杌子,此刻她哪有什么不明白的,这道姑定然是跟那小偷是一伙的,至于为什么要把荷包还给她,她也想不清楚,只知道带着她的银子赶紧走人就是了。
道姑干脆双手一摊,做出一个请便的动作,周子兰气得直咬牙,扭头便走。
桌子旁边的高瘦身子慢悠悠地坐下来,喝了一口茶,那位姑娘给了她两个任务,一是把钱袋子还给那位夫人,二是把她引到这里来,两个任务她都顺利完成了,此刻自然不必留人,反正银子她已经稳稳地纳入囊中了。
周子兰抬手用袖子遮着半边脸,急忙忙地往外走,一个熟悉又温和的声音传来。
“今日人多,当心脚下。”
短短的几个字传入周子兰耳中,瞬间如遭雷劈,让她忘了迈开步子。猛然转身,那张在梦中出现过千万回的脸庞跃入眼帘。尽管增添了几分岁月的痕迹,但她还是一眼便认出来了。
他怎么来了?
周子兰抖着唇,脑海深处的记忆汹涌翻滚着。18年前,面前的男子曾与她有私定终身的海誓山盟,还让她在家安心等他过来提亲,结果苦苦等来的却是他要娶太常寺卿嫡女的消息。听到消息的周子兰,不顾一切地冲到长晋伯府要一个说法,结果司彦竟当着长晋伯和容氏的面说她勾搭他,才致使他迷了心智。
不久后,她就成了京城中人茶余饭后的诟资,也是因为如此,她的父亲才逼着她下嫁到京郊的僻壤之地。周子兰回想着这十多年来不尽如意的生活,只恨自己当时瞎了眼,竟会相信司彦的鬼话。
顺着男子的眼光,周子兰看向他身旁的人,女子身穿紫红色褙子和配色的马面裙,耳垂上戴着的红宝石耳坠与发间的红宝石钗子交相辉映,衬出雍容姿态来。明明是与她年纪相仿的人,却好似双十年华的小姑娘一般娇媚。
那位便是司彦的发妻,太常寺卿的女儿,甄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