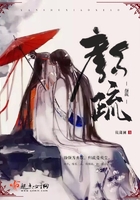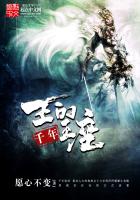月比人瘦,清清冷冷,连周边都绕了一圈毛茸茸的光亮。
信鸽在黑暗中振翅,落在齐王府房檐上,家丁打下信鸽,取下绑在腿上的黄色细管。
夏晗邺拆开那信来看,猛地面色大变,“侍书。”他对着身侧家丁说道,“去查,查一查那夜裴敬被杀的时候还有谁在场。”
“现在就去。“话说完,尤有些急不可耐,又补上一句。
“是。“随从见他这般着急,也不敢多说话,赶着就往外奔去。
夏晗邺捏紧手中的纸条,看来木青城已经在京城有了自己的眼线了,从前都是刘与风与他联络,这一次夏晗邺也没有给他去信。可是短短几天,那回信却径直落在了齐王府上。
已经几天了,刘与风虽然抗住了诏狱折磨,但是真相永远不会被公开了。柳州来了信,夏晗邺知道,刘与风或许会背着这个罪名过一辈子,但他必须选择。
双目合上,少年坚毅的脸上痛苦不堪,长久才能听到他将心中郁结的那一口闷气吐出。再睁眼时,是与之不同的精光,大步向前迈去。
与此同时,一封信也落在了萧府外的书桌上,“木青城。“萧林看着手中的信,唤出那个远在柳州的人的名字。一个本该死去的人却成了屠刀下的漏网之鱼,翻起了如此惊涛骇浪。
这是一封从马道长家里搜到的信,马道长藏得十分隐蔽,却终究被锦衣卫翻到了。萧林一直知道马道长背后有除了夏晗邺和刘与风外的第三股势力,却原来便是那个一直龟缩在边境的那个少年。
萧林将那信纸折合,大约过不了几天雪瑶便能回宫了吧,萧林嘴角勾起淡淡的笑,不似旁人看的那般渗人,甚至看了几分温润的书生气。
沁心和四娘都被关在齐王府的密室内,当夏晗邺推开门时,沁心从黑暗中回过头来,看着那个少年走了进来,浅笑说道“齐王殿下,今夜好兴致啊。“
“沁心姑娘住得可好?“夏晗邺走了进来,与沁心玩笑道,夏晗邺从前可没想到自己还有机会做这等大事,自然也就没修密室之类的东西,也就只能委屈美人屈居在这又黑又潮湿,临时修建小暗室中。
沁心听到夏晗邺这般问,一声苦笑却没有答话。
反倒是四娘,听到夏晗邺从外面进来,扑将过去,却被夏晗邺一手挡回,夏晗邺虽武艺不精,但对付一个四娘这般的弱女子却是绰绰有余。
夏晗邺没什么风度,四娘被他这一推,重重摔了回去,抬头恨眼看着夏晗邺。
“放我出去。“她的声音粗重,比之之前,全然不像之前那个娇滴滴柔弱弱的女子。
夏晗邺兀自端了根凳子坐在四娘面前,平静地看着他“你的靠山裴敬已经死了,我现在放你出去你能去哪儿呢?萧林等着杀你了灭口呢。“夏晗邺嘲讽地说道,这句话一出口,沁心猛然抬起头看向他,也不知在想些什么。
夏晗邺俯下身体,脸上含笑地看着四娘问道“你想活命吗?”
牢房中的刘与风半瘫在地上,他的眼睛被血水蒙住只能看见模模糊糊红色的世界,烛火影影绰绰,偶尔能听到断断续续微弱的声音。
他的一只手臂也被废掉了,耳朵里插着钢钉,全身也不知断了多少根骨头。他不知道还能撑多久,这口气一直没能落下。
萧林已经取了证据,造了口供,其中包括了与夏晗邺勾结,逼着他画押,这些天的酷刑都已经承受下来了,只这唯一一个念头支撑着他,不能画押,不能画押。
“侯爷,你受苦了。”言正钦就在刘与风的隔壁,将这些天的事情都看在眼里,他们同样对萧林恨之入骨却又无可奈何,此刻看着奄奄一息的刘与风生出一股同病相怜的感觉。
言正钦知道,他是大樾最后的一丝骨气在,若连他也倒下了,这天下才真的再看不到一丝清明。
刘与风耳朵里有铁钉,只能断断续续听到言正钦说话,用破锣一般的嗓子回道“我给你的信,你可收好了?”
言正钦摸了摸怀里的信,那是刘与风给他的,数个倍受折磨的夜晚,刘与风却坚持用血水在信纸上一笔一划地写着,言正钦不知道信的内容,刘与风只说,若是有一天他能出去,一定要代他将这封信给天下人看。
那热血铸成的书信,哪怕血迹已干却依然灼得人心口发疼,“你放心吧,侯爷,若有朝一日言某能从这里出去,天下定能人人皆知这信的内容。”
一阵脚步声传来,铁靴踏在地上,每一步都回荡在这寂静的狱里,随着钥匙打开牢门的房间,只听一个人声高声地喊道“刘与风,你招还是不招?”
虽然知道这深夜忽然的审问也是常有的,可是此刻刘与风已经是不成人样了,言正钦实在看不过去,一声喊道“你们这群没人性的畜生,猪狗尚且有怜悯之心,你们却是连猪狗都不如。”
向来锦衣卫是趾高气昂的,虽然皇上下令要留言正钦一条命,但是这种情况总免不了挨上两脚。
今日这锦衣卫倒是不似从前那些一般狗仗人势,只听他说“言大人可省些力气吧,提督让提审谁,咱们可敢不从?”说着低着的头颅微微上抬,露出一张年轻的脸,那双眼睛格外机警。
言江,刘与风认得,曾主动上门找过他,并给了他不少情报和线索,只是曾听闻他被贬为了洒扫太监,今日却无故出现在了这里。
马道长此刻很煎熬,因为家里明显有被人翻查过的痕迹,仔细查找却发现金银珠宝都没有丢,唯一丢的却是那最要命的信件。
马道长一生全靠坑蒙拐骗过活,也曾因骗局被人发现被追着打过。这辈子做过最大胆的事便是被木青城骗了进宫来,一辈子坑蒙拐骗最后反倒被人骗了。
能选择这一条路大约不过是因为他见过原本幸福的家因为女儿无端被锦衣卫抢走而哭救无门,也见过战争来时原本富庶的边境小城一夜之间化为断壁残垣,就连他自己,若不是为生活所迫,谁又会选择这样靠骗人活在夹缝之中的生活?
或许进宫,是他所过的所有事中,最正确的一件吧。
里里外外翻查了几遍确认不是自己弄丢了,马道长累得坐在地上,这一次只怕是逃不掉了。他才是最孤独的吧,甚至此刻身边连倾诉自己恐惧的人都没有,江湖浪荡一生,孤身一人进了京,他能猜测到自己的结局。
此刻的诏狱也是同样的死寂,言江已经走了,沉闷的空气中半点风都没有,昏暗中,刘与风沾染着血与污渍的额头青筋突起。
言江不过凑在刘与风耳边说了几句话,连言正钦也没听清他说的是什么。
黑暗中,只听到那粗粝的嗓音,喊着如同金属破裂一般的声音,他说着“来人,我要招供。”
牢房内安静,声音远远地传了出去,也不知刘与风哪里来的力气,一遍又一遍重复“来人,我要招供,我要招供。。。”
清晨,李才人正给樾帝整理着衣袍,樾帝将两只手排开,等着爱妾给自己扣上腰带。
所幸上次李才人一病几天也就好了,樾帝很高兴,趁此机会还晋了李才人位分封了美人。
“昨日和你对的诗还没对上来,且记着,今夜朕一定对上。”樾帝放下手转过身让李才人给他整理身后的衣物。
“参加齐王殿下。”还未等得李美人回答,却听到门外侍女行礼的声音,夏晗邺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
“儿子给父皇请安。”夏晗邺像是一路小跑进来,额上还带着汗迹,也没向李美人行礼,直愣愣地跪在了樾帝身前。
李美人看到樾帝心中有不悦,打先替他说道“何事这般急匆匆的,哪里有半点儿皇子的样子?”
“何事这般惊慌?”樾帝的衣服已经整理妥当了,却被夏晗邺拦在了皎梨殿,心虽有不快,但李美人也替他责备过了,倒也没多说什么,转过身看向夏晗邺问道。
“父皇,昨夜儿臣遇上一个妇人,说是裴敬裴大人的家眷,她告诉儿臣裴大人此案还有隐情,儿臣听她如此说不敢自作主张,这才鲁莽进宫,扰了父皇母妃清净。”夏晗邺说道。
“你说裴敬的事另有隐情?”樾帝知道夏晗邺对刘与风入狱一事耿耿于怀,但听他如此说也不由得想要多听几句,便吩咐道“你说来听听。”
却听夏晗邺说,“这事实在太过匪夷所思,父皇还是听听那妇人如何说吧,她已经等到宣武门外了,若是父皇同意,儿臣这便让人把她带进来。”
“让她进来吧。”樾帝说道。
随后,夏晗邺与李美人便跟着樾帝出了内室,走至前厅。很快,四娘便被人带着走到皎梨殿。
只见四娘一见了樾帝李美人便重重跪了下去,失声哭了出来,嘴里说道“民妇见过圣上娘娘,求圣上与娘娘为民妇做主啊,我家老爷被人害了。”
旁人见了樾帝都是恭恭敬敬的,哪里有像四娘这般上来便狼哭鬼嚎的?初一见这等泼妇,樾帝不由自主地身子往后躲了躲,这才想起当着李美人和夏晗邺面前有失身份,又坐直身体问道“你是何人?你家老爷又是谁?何人害了他?一句一句说清楚。”
只听那妇人哭着说道“我家老爷是前任工部尚书裴敬,要害他的人权势通天,乃是威北侯刘与风。”
樾帝只当这妇人死了家人疯了,人人都知道是刘与风杀人,她又何苦跑到这里来哭冤?却听到李美人说道“胡闹,谁人不知是刘与风杀的?他现下已经入了狱,不日便要斩首,你还想怎的?”
“可刘与风不过是受人之命,他背后还有人,若是旁人我还能为老爷报仇,但是那个人,却没有人能奈何得了他。”四娘说道。
“你的意思是朕也拿他没办法?那是何人?朕倒要听听。”樾帝听这妇人疯言疯语,也不知该笑还是该怒。
“那人便是当今锦衣卫提督——萧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