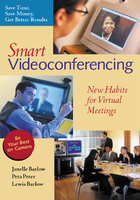就在这个时候,樾帝也在朝晖殿见到了言正钦。
他记得二十多年前的言正钦意气风发,他身居高位,天下尽在他的掌握中。可是,今天,言正钦双手带着镣铐,蓬头垢面,一双浑浊的眼在散乱的头发后面,看着樾帝。
他没有下跪,没有行礼,就是这么平静地看着樾帝。
樾帝也不生气,他还笑了,此刻过往扑面而来,峥嵘岁月、金戈铁马,都在这个人的身后,他笑了,“你老了。”他对着曾经的盟友说。
“陛下也不年轻了。”言正钦也跟着说。
樾帝从龙椅上站起身来,他踏下云梯,坐在最后一步梯上,他就这样随意地坐着,这一刻,他不是君王,言正钦也不是臣子。
他看着敞开的宫殿大门,天已经黑透了,雪还在簌簌地下“你还记得吗?塞北的雪才是真的大啊,那一年咱们打仗,晚上实在冷得不行,就烧着柴火,硬生生坐了一宿。”他说。
言正钦很自然地坐在樾帝身边,“怎么不记得?那时候你还是个藩王,大梁的人说来就来了,你二话不说,提着刀就和别人干起来了。当时我在兵部,朝廷派我去支援,就看着你带着手上几千的兵,站在城头上和别人打得热火朝天,要说你还真是厉害,打不过就用砖头扔,砸了多少大头兵啊。”
“哈哈哈。。。”两个人想到过去的岁月都笑了起来,年轻的岁月真好啊,樾帝身体后仰,两只手肘撑在身后的梯子上。
“你也不差啊,我记得那次咱们追击敌方,结果正入了对方的圈套,我转过身来,看见你拿着刀冲来冲去,有个冤大头被你遇上,半张脸都差点让你咬下来了。”那一年,樾帝才二十多岁,带着三千军就敢追军,反倒被敌人半路伏击,言夏正钦与他一起突围,到了最后,两个人身上都负了不小的伤,身侧只有十几个人。
“是啊,那个时候真好。”言正钦叹道,那个时候真好,樾帝还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而他,纵马轻狂“就是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要是你当皇帝多好,天下一定安稳。”
言正钦几乎将今夜当成他人生最后一个晚上度过,什么都敢说,什么都不忌讳。
“是啊,要说那个时候咱们的胆子可真大,你和太皇太后竟然敢提前半月密召我来京城,就是先皇死的时候,秘不发丧,赶在夏常煊之前宣读遗诏。”这些话,樾帝是从来不提的,也不允许别人提,但今天不一样了,他渐渐感到能陪自己说这些话的人越来越少了,也许等到言正钦之后就再也没有了吧。
“你说以前的那些人都去哪儿了?成乾,李一晖,虎林。。。怎么走着走着人就越来越少了。”樾帝当然知道这些人都去了哪里,他只是坐在这个位置上太冷了,太害怕了,他想起了曾经的盟友们,他们一个一个笑着向他走来,他看着那些人影,问一句,你们现在哪儿啊?
“陛下。”林正钦忽然收起了谈笑的表情“不要再杀人了。”他陪樾帝一路走来看眼着那些人一个一个从身边消失,那个鲜衣怒马的少年被权利与鲜血侵蚀变成了如今的不近人情的暴戾。
“我不想啊。”这些话说出来大约没有人会信吧,但是这的的确确是樾帝真实的感受,他指着身后富丽又独孤的龙椅“这个位置太高、太冷了,每当我一坐上去,我就感到害怕,我害怕,你信吗?”
这个位置前太过拥挤了,只有把挡在这个位置前的人都杀光,他才能安心。
“那你就这么信任萧林吗?”言正钦想起之前与萧林说过的话,他有心想把这些都说给樾帝听,但是言正钦知道他一定不会信。
“萧林?很好用。”樾帝想起那个从来阴冷的身影,好像从不和朝堂上的人走在一起,他是樾帝手中一个锋利的武器,不会有别的心思但是杀人却能又快又狠,当然这是樾帝的想法。
“你当真以为他就这么纯粹?”也不知这萧林用了什么方法,樾帝把一切的权利都交给了他。
“至少,他不会谋反。”
是啊,在樾帝心中所有人都能反,只有萧林不会,因为他没有反的动机。而在所有太监之中,萧林的政治能力和办事水平是最高的,若要选一个人信任,只非萧林莫属。言正钦看着樾帝算计的神情,然而那个最不可能的人却是最危险的人。
“那玉贵妃呢?陛下怎会如此宠信于她?朝中所有人都说陛下被妖妃蛊惑了,难道这些陛下都没有听说过吗?”言正钦问。
“她不过是个女子。”樾帝答道,眼中有运筹帷幄的自信“我需要这样一个人,所有人都会把过错记在她的头上。”
言正钦忽然明白了,玉贵妃或许有些手段,或许樾帝是真有三分喜欢她,可是一切的精明都比不过这个君临天下的男人。他才是真正想要肃清左右的人,是他想要高枕无忧,是他想要将所有认为有威胁的人都清除干净,而偏爱玉贵妃,能成为他做这所有事的理由。
只可惜算无遗策的陛下,步步算尽却反被人算。
话堵在言正钦口中已经说不出来了,今天来之前,他想过很多要劝的话,此刻却一句也不想说了。
言尽于此吧,或许,当年他真的错了。
送走了言正钦后,樾帝一个人疲惫地坐在龙椅上,独孤的感觉袭来,像是一个人走在黑夜中,寒冷与彷徨。当年的那个少年从朝晖殿走过,他桀骜的双眼,看着自己面前这个苍老的老人,紧抿的双唇不置一词,就这么错身而过。樾帝想要拉住他,可是少年走得好快,他大步向前,是笃定和挺拔的身影。
他累了,真的累了。
“奴才参见陛下。”萧林站在朝晖殿的门外,恭敬温顺地给樾帝行礼,勾下头,只能看到半边晦暗的脸庞。
“你来了。”樾帝半抬起眼眸,看着那个半跪的身影。
“是,陛下有什么吩咐?”清冽的嗓音在这浑浊的暗夜里徒增了几分明朗。
“好好待言首辅,不要让他死了。”樾帝吩咐道,这样的交待于他而言就是仅有的仁慈了。
“是。”萧林不置可否。
“对了,你前些日子在跟我说辽王,辽王有什么事吗?”樾帝想起萧林前段时间一提而过的辽王,当时他正烦言正钦的事,并没有过多地注意。
“有探子回报,辽王屯兵数万,好像有什么举动。”萧林答道。
厌烦的情绪不可抑止地涌上心头,事情一件接着一件,谋反谋反,怎么那么多人和谋反牵扯上关系?“萧林。”
“是。”声音简短、干净,没有多一分的拖泥带水。
“你说是不是今年年份不好?”他问。
“陛下多虑了,如今天下风调雨顺、百姓安泰,是天泽我大樾万民。”萧林答道。
“可先是大皇子,又是王进,再而又是言正钦,这一桩桩、一件件的事怎么没完没了?朕真的是倦了。”当真是多事之秋啊,这许多事情好像无穷无尽,怎么也办不完。
“是人心不好。”萧林说的话依旧是干练,这便是樾帝喜欢他的地方,他办的事又快又漂亮,也不会像那些言官一样天天吵吵嚷嚷,对什么事都要指手画脚,吵得樾帝头疼。
“等开了春,总要祭一下天,我才安心。”樾帝说道。
“是。”萧林不置可否,樾帝没有看到的是他低埋的脸上,阴暗的眼眸忽然一闪而过的精光,唇角微勾,就计上心来。
“没什么事了,你下去吧。”夜已经深了,樾帝也不想再去烦心那许多事了,至于辽王,总归还没有打起来,大家都等着过个好年,开了春再说吧。
“奴才告退。”行了一个标准礼,萧林半躬着身子缓缓退了出去。
“萧林。”萧林走到一半,樾帝忽然唤住了他,身形顿住。
“陛下还有什么吩咐?”萧林止住了脚步。
“好好干,莫要欺我。”声音疲倦却带着震慑人心的威严,好像他什么都知道,又好像不过随口一说。
僵硬的身形顿了顿,震惊的神色一晃而过,随即又是一副无懈可击的面具“是。”他不会问樾帝这样说话的缘由,也不会为自己辩驳什么,他要做的就是对樾帝的吩咐,无条件地顺从。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是年关。
这一年总的来说,大樾还是过得不错,虽然西北边发生了动乱,但不过几天朝廷也镇压住了。人们穿上簇新的衣服,欢欢喜喜地过起年。
叶哀哀今天很高兴,师兄们给她买了新衣服以及各种小玩意儿,此刻让她上街去买点炮仗,准备晚上一家人高高兴兴吃个年夜饭,并搞点发压岁钱、放炮仗的小活动。
今天街上沸沸扬扬,虽然天气冷得哈气成霜,不过抑止不住人们心中的热情。小孩儿三三两两地围在一起点炮仗,叫卖的人也尤其多,今天就算是再穷苦的人家也会上街来买点果脯、瓜子,晚上守夜的时候当做消遣。
“哎,你听说了吗?今天柳州城里施粥,听说辽王嫁女儿呢。”熙熙攘攘的街头,两个人缩着手从叶哀哀身边走过,两颗脑袋凑在一起说着什么。
叶哀哀本不该注意这些话的,但是有些话却恰恰就是这么巧,不偏不倚传入了她的耳朵里。
“是啊,怎么没听说?大名鼎鼎的玉和郡主成婚,这周围的城里谁人不知道啊?”路人乙附和道。
“哎,你说这人是谁啊?也没听说过哪个世家子弟要娶妻啊,能娶到辽王视为心肝肉的宝贝千金,总不能是默默无闻之辈吧?”两个人的八卦精神不死不休,虽是草民之身,但对王侯的家世,有着浓厚的兴趣。
叶哀哀站在小摊前挑选彩灯,渐渐也被他们的对话夺去了一半心神。
“谁知道呢?不过我有个弟兄在辽王府做事。我听说半年前好像有个什么公子去了辽王府,说门客不算门客,说佣人不算佣人,带了一万多人去,就这么一住就是半年。”路人乙以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并以与知情人士能扯上七拐八绕的关系而骄傲。
“何方神圣啊?这一次不会是他要娶的郡主吧?”
“好像就是他,我记得我们那兄弟说是姓。。。姓木吧,据说辽王把他尊为坐上宾客,客气得很。”
“这到底什么人啊?辽王管吃管住还送女儿?”
。。。。。。
两个人渐渐走远,半年前,带一万多人,姓木,那两个人不知道他是谁,叶哀哀却知道,难怪,难怪那一天会在岳林遇见他,原来,他就在柳州。
那个身影出现在眼前,高大、清瘦,目光如墨好像永远有浓得化不开的悲伤,料峭的身影像高山让人仰止,永不可攀附。
“姑娘,姑娘。”小贩见叶哀哀手上拿着一个灯笼,看了半天,眼睛都看直了,也不说买还是不买。
“啊?”叶哀哀抬起头来,眼睛里已经蒸腾起一股水汽,迷迷蒙蒙,悬而未落。
“你到底买不买啊?”小贩指着她手中的灯笼问道。
叶哀哀忽然弃下手中的灯笼,拔腿就跑,不管是不是他,她都要去见一面,只有见了才能安心。于那个人而言,或许她叶哀哀只是匆匆而过的一个过客,可于她,他却是她寂寂活了前半生全部的幻想和欢喜。
“好奇怪的人。”小贩仰长脖子,看着叶哀哀离开的背影不明就里。
叶哀哀牵了路上的一匹马就往前跑。
“喂,你干嘛牵我的马?”路边跑出来一个人,看着马蹄绝尘而去,手上的筷子还没有放下,就跑出来骂。显然是在路边吃早饭的,但是早饭还没吃完,马就被人骑走了。
“啪。”一个东西落在地上,那人低头去看,是一个钱袋,胀鼓鼓的,捡起来掂量掂量,实在有些分量。
也不知跑了多久,风呼呼地刮在脸上生疼,叶哀哀勾身紧紧勒着马缰,面色如这天气般寒冷。还好,柳州和怀州虽然是两个城,却是挨着的,她一路没有花费多长时间便到了。
柳州今天很多人啊,叶哀哀几乎没有花什么功夫就找了辽王府。因为辽王府的门前人太多了,大家都往这里涌,排着队领着冒着热气的白粥,而且辽王府如此壮阔的建筑,今天铺满红布,一片喜气洋洋,想不注意都难。
辽王,果真今天嫁女儿啊,真是好大的气派,红色的彩布从几条街外都结到了这里,辽王站起门前,与每个前来讨粥的百姓说着喜庆的话。
“明日大家还可以来,本王嫁女,施粥三天。”辽王站在门阶上,欢喜地说道,随着笑声,肥硕的肚子起起伏伏。
“好。”底下百姓一片叫好声。
“叶姑娘,你怎么在这里?”最不想出现的人出现了,俞二从叶哀哀身后走了过来,手上拿着几个贴着喜字的大红烛台,显然,是在帮辽王府打下手。
“啊?”叶哀哀强扯起一个笑容,也不管好不好看“听说你们少爷今天成亲了,特地来看一看。”每一个字、每一个呼吸,都牵扯着神经,连着心脏,叶哀哀从前都不知道心原来会有这么痛的时候。
“没有想到叶姑娘和我们少爷这么好,快进来坐吧,等着晚上喝喜酒,我们少爷见了你一定很高兴。”俞二说着便去扯叶哀哀的手。
叶哀哀像是被烫着一样,猛地缩回手,表情十分不自然。
俞二也觉得自己唐突了,叶哀哀虽然是江湖中人,但毕竟是女子,怎么能随意去拉她呢?随即有些憨憨地笑着,缓解尴尬“是我太毛手毛脚了,我是个粗人,叶姑娘你不要见外,快进去吧。”说着俞二便让开身子,把叶哀哀往里面请。
“我。。。我就不进去了,不要给你少爷添麻烦。”
“怎么会是添麻烦呢?你能来。。。”俞二本来还想多说两句话,却见叶哀哀已经翻身上马,往回走了。
“这叶姑娘今天可真奇怪。”俞二对忽然出现,又忽然离开的叶哀哀十分不解。
这算是落荒而逃吧,叶哀哀想,可是仪态和面子都不重要了,再呆下去一刻钟她就会崩溃,她就这样没有出息吧。
辽王府很热闹,木青城没有看到失意的叶哀哀。此刻的木青城换了一身大红的喜袍,长发用玉簪掼起,面庞如墨玉般清冷,他抿着双唇,幽深的瞳孔看着摆着眼前的两个牌位。
猩红的朱砂拓在厚重黝黑的松头上,先考木啸林,先妣王芝敏。
“爹,娘,儿子今天成亲了。”木青城揖了三个躬,将三炷香插在灵位面前的香坛中。
这个祠堂是辽王给他建的,供奉着父母的牌位,虽然不大,却让木青城平日里怀念父母时有了依托的地方。
“你们会不会怪我不与你们商量就擅自做主?”
牌位安静地屹立在那里,不能说话,木青城淡淡地笑了笑,拓然的脸上有些舒展,越发显得剑眉皓目,神情清雅“碧桃是个好女孩儿,你们若是见到她一定会喜欢她的。”他说。
“你们在天之灵保佑我们好不好?保佑我们夫妻恩爱,携手白头。”那本就不至眼底的笑容渐渐凝固,转瞬便是望之让人心寒的冰凉,像世间绝美的素色画卷,带着不可靠近的疏离“若是你们能看到这一天,就好了。”他长叹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