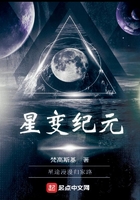公司里的那几棵桃树,早已开得是沸沸扬扬,空气中弥漫着醉人的花香。远远望去,就像一片红色的云霞一般。
蜜蜂在绯红色的花朵中飞来飞去,忙碌地穿梭于其中。
其中一棵桃树上面的一根枝条,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给砸断了,上面还留有刚开的花朵和未开的花苞,在失去树干的养分后,花儿渐渐地枯萎了下来,让人不觉心生惋惜。
年前还没放假的时候,陆广知曾经在一次开会的时候提到过,目前闳清公司收购上海电阻厂最大的障碍,就是电阻厂里那个负责投标的副厂长。
因为一旦上海电阻厂转制之后,他们这帮人就捞不到什么实惠了,所以他们才会极力阻挠闳清公司对电阻厂收购计划。
这个副厂长平时的主要任务,就是负责投标。
只要中标,他们就能根据标的物总额的相应比例拿到提成,至于电阻厂赚不赚钱,赔钱与否,那是电阻厂的事情,他们才不关心呢。
就是在他们这种丝毫不考虑电阻厂的利益,而是一味地奉行“惟中标论”的原则下,上海电阻厂一步一步地被逼上了绝路,使得这个国有大厂连年亏损,最后终于资不抵债,到了被挂牌出售的地步。
事到如今,即使不是闳清公司来收购上海电阻厂,也会有别的公司来负责接盘的。
而以上海电阻厂这个副厂长为首的这一帮人,即使心里有一百个不情愿,也无力回天了。
大厦将倾,他们再也无法阻止上海电阻厂兵败如山倒的那种颓势了,不得不无奈地接受了电阻厂将要被别的公司收购的事实。
闳清公司为了防止将来收购上海电阻厂时,怕到时候由于电阻厂的债务太多,影响到电阻厂的正常运转,还特意借了五十万给上海电阻厂,准备将来从安徽柳远环保设备有限公司给上海电阻厂的项目款中扣除。
上海电阻厂曾经和安徽柳远环保设备有限公司有一个合同,由于现在上海电阻厂已经处于半停产的状态,闳清公司就想把这个合同从上海电阻厂转到闳清,但是上海电阻厂坚决不同意,闳清公司最后也只好作罢。
去上班的路上,向子威问唐工,有没有上海电阻厂的最新消息。
唐工说:“有是有,但不是很乐观。他们说最低收购价不能少于六百万。再加上电阻厂的外债,估计没有一千万,恐怕拿不下来。”
齐天乐说:“我估计收购电阻厂有点危险,最近我刚刚听别人讲,上海电阻厂内部的几个人也想收购电阻厂,想把电阻厂变成他们自己的工厂。”
向子威说:“其实这样的例子多的很,我哥有一个同学,他现在的老板,以前就是一个国企的厂长。当年改制后,这个国企马上摇身一变,就成了他一个人的公司。有不少国有资产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厂里头头们的私有财产。如果有外人收购的话,他们就会故意把价格抬得高高的,让你收购不成。”
齐天乐说:“是啊,我担心的就是这种情况,如果电阻厂内部的人真要这样操作的话,闳清公司就彻底没戏了。”
车上的人都沉默不语了。
有一个上海的供货商来闳清时,顺便提到一个情况,说最近有小道消息讲,可能有一家温州公司要插手上海电阻厂了。
唐工回上海时,特意向以前的同事打听了一下,证实这家公司是来自温州的天力克公司。
天力克公司在上海设有办事处,据说规模很大,但是他们的主营业务是建材领域的,和电除尘行业并没有太大的交集。
何佳有些怀疑地说:“不会吧,他们公司就会虚张声势,表面上看上去规模很大,实际上现在连工资都发不下来。就他们那个样子,还想打上海电阻厂的主意呢!”
齐天乐慢悠悠地说:“这个还真不一定,有些公司不发工资,不一定是没有钱。像咱们公司,也不是每次都按时发工资的啊。”
何佳说:“好吧,就算你说的是事实……不过你可能没见过他们的老总,就是个如假包换的残疾人,每天只能坐在轮椅上……反正我是没有想到,他都残疾成那个样子了,还想插手收购上海电阻厂的事情。”
唐工听何佳讲到这里,噗嗤一声笑了出来:“你别管人家残疾不残疾,反正现在上海那边有不少的传言,具体哪个是真,哪个是假,谁也说不清楚。”
王路华说:“天力克那么大的公司,他们的老总居然是个残疾人?”
何佳说:“我认识一个他们公司的销售,知道一点关于他们的情况。”
向子威说:“如果真是这样,那这个人还真是不简单呢,身残志坚,能做到这一步,看来不是一般的厉害。”
何佳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是啊……我只是没有想到,半路上会杀出来一个程咬金,而且居然会是天力克公司,他们竟然也要来和咱们争夺上海电阻厂。”
唐工说:“来的都是客,上海电阻厂巴不得竞争的对手越多越好呢,竞争者越多,他们就越有面子,收购价格自然也就会水涨船高了。”
上海电阻厂质检科的科长,率领一帮人浩浩荡荡地来到闳清公司。
他们此次来到闳清的目的是,如果将来闳清公司收购了上海电阻厂,要保留他们的原职,不能撤掉他们。
而作为交换,他们则可以帮助闳清公司收购上海电阻厂。
原来,上海电阻厂现在已经全面停产,全体职工一律回家,等候上面进一步的通知。
电阻厂中层以上的领导,每个月暂时可以领到六百元的补助,工人的情况则不得而知。
怪不得他们已经开始慌了。
这个质检科的科长有五十多岁,胖胖的,戴着眼镜,说起话来嗓门非常的大,像是在训斥人一般。
也许是由于在国企里面呆的时间久了的缘故,那种在国企里面长期养成的官腔和做派,已经无法更改了。
下班后,向子威正在往楼下走的时候,看到陆广知拄着拐杖,一步一步正吃力地走上楼来。
当他走到二楼财务部门口的时候,由于没有掌握好平衡,一屁股就坐到了地上,一根拐杖也飞出了好远,顺着楼梯就滚下去了。
下面的人见状,急忙闪开。
正在财务部里的老赵和老阿姨听到声音之后,出来一看,原来是陆广知,于是两个人急忙上前把他搀扶了起来。
王惠则跑下楼去,把那根拐杖捡了上来。
当着大家的面狠狠地摔了这么一跤,陆广知显得极为尴尬。
他顾不得身上的疼痛,接过王惠递过来的拐杖,也不要任何人搀扶,自己一个人拄着拐杖,阴沉着脸走进了财务部的办公室。
他让王惠把何佳叫过来,然后再找一下电器车间的车间主任高树江,要求大家今晚一定要加班加点地把标书给赶制出来。
是在快下班的时候,豫丰环保有限公司才打电话过来,通知闳清公司准备投标的这个消息的。
这次是豫丰环保在广州的一个项目,明天就要开标了。
由于闳清公司现在才接到这个通知,大家都感到很突然,一时有些慌了神儿。
和太原环保设备厂一样,豫丰环保有限公司也只生产电除尘器的本体,而电除尘的其他的配套设备,要向类似于闳清这样的公司招标购买。
老赵说:“老板刚才说了,今晚一定要弄好,否则谁都别想睡觉,不能耽误了明天早上七点半那班从上海到广州的飞机,到时候由我和老钟带着标书去投标。”
其实所谓的投标,只需要把豫丰环保发过来的文件中的有些名称和报价改一下,其他的大部分材料,豫丰环保已经整理好了。
有了豫丰环保的文件作后盾,大家紧张的心情慢慢地缓和了下来,不再像一开始那样,显得有些手忙脚乱了。
王惠在电脑前改,何佳就在旁边看,另外电器车间的车间主任高树江也上来和他们一起加班。
他们几个人一边改着标书,一边还相互开着玩笑,看上去非常的轻松。
反正目前的情况就是,都到这个时候了,眼看着就要开标了,闳清公司对于广州那边的具体情况,还一无所知。
既然这样,他们也就只好两眼一抹黑,稀里糊涂地把豫丰环保的报价直接乘上零点八,也就是说,按照豫丰环保报价的八成算好价格,然后就直接交上去了。
糟糕的是,由于时间太仓促,标书赶制出来之后,居然连公司的公章都忘记盖了。
可是,大家当时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个情况,老钟和老赵就匆匆地带着标书,到上海赶飞机去了。
豫丰环保的销售蔡奇,那天也在广州项目的投标现场。
就是蔡奇首先发现闳清公司的投标文件上,没有加盖公章的。
当时,老钟就在蔡奇的身边,他也不告诉老钟标书上没有公章的事情,而是走到一边,直接打电话给千里之外的陆广知,把这个情况说了一下。
陆广知听了,当时大发脾气。
最后,闳清公司只好又通过传真发过去了一份,这才勉强把问题给解决了。
而老钟和老赵也因为这个严重的疏忽,被陆广知骂了个狗血喷头。
老钟和老赵这次广州之行,中了两个标,一共是一百九十八万。
大家都向他们表示祝贺,说他们这次的辛苦总算没有白费,没想到只是临时抱了个佛脚,居然也能歪打正着地中到了两个标。
老赵给大家泼了盆冷水说:“你们先别高兴得太早了,虽然这次中标了,但这个项目将来赚不赚钱,还不一定呢。”
王路华说:“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老板说了,这次就是赔钱也要做,先打开广州的市场再说。”
老赵一直埋怨蔡奇,说蔡奇为了邀功,让他和老钟狠狠地挨了老板的好一顿骂。
虽然大家一致认为,蔡奇这样做,确实有些不地道,但老赵绘声绘色的描述,让大家还是忍不住想笑。
可是看到他气急败坏的样子,大家最后还是强忍住了,因为在这个节骨眼上,不能再往他的伤口上撒一把盐了。
不过,总的来说,忘记盖公章这件事情,显然已经不是什么小问题了。
老赵不满地说,他和老钟头天晚上一直在公司里陪着大家投标,第二天凌晨又马不停蹄地赶到上海的浦东机场。他们两个累死累活地忙了一天一夜,觉都没有睡好,还要受这种窝囊气。
王路华说,你又不是不知道蔡奇和老板的关系,人家可是每次都要从闳清公司拿回扣的。如果因为你们的粗心大意,这次接不到标,那他不是拿不到回扣了吗?这次之所以在现场没有告诉你们,就是为了给你们一个教训,看你们下次还粗心不粗心。
何佳安慰老赵说:“别生气了,这次就当是给你们提个醒了。”
老赵气冲冲说:“什么叫给我们提个醒?那晚整理标书的时候你也在场,你当时怎么也没发现标书上没有盖章呢。”
何佳不好意思地说:“这件事情我有责任是不假,这个我也不否认。不过你们临走的时候,至少也应该再仔细地检查一遍吧?”
老赵摆了摆手:“好了好了,算我和老钟倒霉。反正公司里的好事儿从来都轮不到我,倒是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儿,哪次都少不了我。”
王路华说:“哦,这么说来,你一直都是咱们公司的劳模了?”
老赵没好气地说:“受气劳模!”
向子威的嘴角不自觉地往下撇了撇。
鉴于上一次山西热电厂事件中老赵所扮演的不光彩的角色,所以对于这一次他在广州的遭遇,向子威连半点儿的同情心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