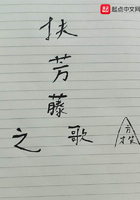从对空山的山顶俯瞰,下嵃城的形状近似于一个半圆形:最外围是厚厚的城墙,从山的一端开始延伸,在下嵃平原上画出一个半圆,然后在山的另一端停止。城墙由整块的旬石堆砌,用荨籽树的树胶进行粘合,石头刀砍无痕,树胶针扎无孔。城墙之上,十二座角楼依次排开,由守城卫兵日夜看守。
城外,目及之处均是沃野,一条碎石铺就的宽阔大道横亘其中,通向视界的尽头。大路两边则是一块块的农田,此时田中的大麦长势正盛,一刻不停的吸收着充足的阳光和水分。
城内是各式各样的建筑,最内层——几乎处于半圆的圆心位置——是金雀国的王宫所在,王宫建立在一座约有一丈高的石台之上,围绕着石台的是一条人工开凿的河流,河流约有五丈宽、一丈深。在石台的中间位置,三座石拱桥相邻而立。从石拱桥上走过,然后穿过石台中开出的圆顶通道,一个上坡,便来到了石台之上。再向前看去便是王城的城门,金雀王宫的建筑群大致可分为五层,由外至内依次居住着卫队、侍官、仆人、王族和国王。
河的另一侧,紧邻王宫的是一片府邸,这里面居住着金雀国的大臣、将军和其他的贵族,这些建筑风格不一,大小各异,但无一例外的奢侈豪华:一丈有余的高大院墙,整块厚重的漆木大门,错落有致的亭台楼院,无不透露着金雀上等人士的奢靡无度。
再向外是十多条繁华的大街,一间间酒馆、花楼、赌场、商店坐落其中,白天的时候,大街上人头攒动、来往的商户顾客络绎不绝;而到了晚上,也并没有完全安静下来,街道里灯火通明,酒馆、花楼、赌场里依旧人来人往。
街的尾端是一片整齐划一的民居,下嵃城内登记在册的居民,每户可以得到一座三间屋子并附带一个小院的独居,代价是在每年须多缴纳一成的税款;民居群落之外,则是一大片空地,空地上零零星星的散布着几百座木棚,这里是无土地农民、破产者和无家可归者的聚集地,他们的背后就是高大的城墙。
天色渐暗。
下嵃城的一个破旧木棚旁边,被母亲绑在树上的江布眼看着太阳落下山去,又开始哀求她把自己放开。
“你不要拿点火的任务来唬我。我已经同火役长讲过了,今天你不用去了。”母亲坐在木棚里,说话的语气极为严厉。
怎么会不严厉呢?今天已经是自己的孩子这个月第三次因为偷东西被人打了。城中糕点店的老板提着他找上门来的时候,他还在偷偷的往自己嘴里塞偷得的米糕。母亲一边道歉一边拿出仅有的几个铜子钱付给糕点店的老板。
母亲极为要强,即便是已经给过了钱,还是强迫江布喝下腐水,使他将肚子里的米糕全部吐了出来。
此时的江布饥肠辘辘的倚靠在树干上,双腿已经几乎没有力气支撑身体。
王城背后的对空山上树立着两个约有七八丈高的云雀雕像,雀身被金色颜料均匀覆盖,雀身中空,里面是一座直通雕像徒头部的旋转楼梯,楼梯的尽头连接着一个小小的平台,平台四周是若干面光滑的镜子,看起来好像是很随意的放置着,但实际上,其摆放的位置和角度都经过精确的计算。每天傍晚的时候,火役长带着江布(或者是其他的人,但大多数时候都是江布),各自身背一桶祁树的树油,从山的另一侧上去,然后顺着旋楼梯登上平台,将树油倒在平台中央位置的巨型油灯里。在太阳消失在地平线的时刻,火役长点燃油灯,灯火的光亮经过四周镜子的不断反射,最终通过眼睛位置的镂空发射出去。
江布朝着王城的方向看去,雕像的光已经开始慢慢的亮了起来,只是与往常略有不同的是,今天发出的光不再是往常的纯净的红色,而是透着一丝淡蓝色的微光。那是因为在一年一度的金雀国祭祀大会之时,灯油里都会加上大量冕石粉,这种粉末燃烧时会发出蓝色的光芒。
不过江布最关心的并不是这些:本来如果今天完成任务,他可以得到出来平常应得的工钱之外的半个铜子,而且城中的祭祀仪式结束后,还能去向祭祀仪官讨要一些吃的。而现在的他除了能哀求母亲尽早将他放开之外,什么都做不了。
“母亲,我知道错了。”
“知道了就老老实实的待着,今天你就不要再想着去城里了。”说完母亲便走进木棚里,把江布一个人丢在院中。
几个孩子跑过来招呼江布一起去城里讨要吃的,看见江布又被绑在树上,便大笑着一起跑走了。
江布怔怔的望着远处明亮的灯火,脑中想象着可能有的肉干、甜糕和糖果,以及他们充满嘴巴的奇妙滋味,想着想着便慢慢的低下头睡着了。
朗月当空。
金沙城的信役此时站在高地之上,极目眺望远处被群山环绕的金雀国都下嵃城。虽然已是深夜,但透过淡淡的蓝色烟雾,依然可以隐约的看见城内纷繁的灯火。下嵃城本就是南方大陆上最繁华的城市,又恰逢金雀族人一年一度祭祀祖先的节日,更使得这座不夜城越发的热闹非凡。
但城内依然沉浸在欢愉之中的金雀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们无比信赖的北境守护者、金雀国最为能征善战的将军武戈已经在醉酒中被塔塔国祭司刺死。和他一起陪葬的还有两个年轻貌美的柯古族舞女。而本以为固若金汤的北境卫城金沙城也被塔塔王索多亲手焚为灰烬。
对危情的敏锐直觉使得信役得以带上密文提前逃出金沙城。经过一整天的躲避式的奔波,他终于看到了下嵃城。
然而此时的他依然面色凝重:他的面前是被银色月光笼罩的下康林地。林地里树木丛生,树冠遮天蔽日,似乎透不过一丝光进去,林子黑漆漆的,看起来让人不禁胆寒。
一旁棕色的马并不知道面前的危险处境,此时正贪婪的嚼食着地上的青草,丝毫没有注意到主人慌张的神情。信役抬头看了看月亮,长长的吐出一口气,之后绑紧背后的包袱,转身上马,沿着坡路下了高地,朝着黑暗的森林狂奔而去。
林地里只有一条羊肠小道可以通过,那是很多年以前猎人部落在此处生活狩猎时留下的,现在已经几乎被两旁的野草吞没了。信役曾经听他的父辈们讲过,当年金雀国的少王文季奉命攻打投降塔塔王族的柯古族猎人部落,最后一场战役便发生在下康林地外的平原地带。猎人部落最后的少王沮寒带领着残存的百余人,终究敌不过如日中天的金雀大军,只好弃城逃进了森林里。年少气盛的文季立功心切,不顾林地里的形势复杂,冲进林地要追杀败王,却不料被沮寒反身伏击而死。
想到这里,信役不禁眉头一紧,他狠命的踢了一下马肚子,棕色的马立刻加快了脚步,箭一般冲进了森林里。
塔塔族小王子子休爬上高地,看着信役孤身一人冲进了林地,便如释重负般长舒一口气。他躺倒在脚下的草地上,嘴里叼上一根草梗,一边看着月亮,一边静静的等待。不一会儿,安静的森林里突然传来了箭镞急促的声响、人的哀嚎和马的嘶鸣。子休坐了起来,看到许多鸟儿从一片树冠中慌乱的飞出,他的表情变得有些得意,那是只有年轻人在少不更事的时候获得一点点小的成功才会表现出来的神情。
子休站起身来,死死的盯着林地的出口。没多久,两个身着黑衣,头戴篷帽的人从林地里穿出,快步来到子休的面前。子休看到其中一人手里拿着包袱,便吐掉嘴里的草梗。然后三人转身消失在高地的另一侧。
过了不一会儿,几只鸟儿盘旋着落回原来的位置。在它们的脚下,信役静静的躺在潮湿冰冷的土地上。他的脖颈中了一箭,已经没有了气息。惊慌的马此时也跑了回来,朝着信役睁着双眼的脸上喷着热气。周围的一切恢复了宁静,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下嵃城的最后一个清晨格外安静。以往在东方刚刚露出一丝红光的时候,城中的人们便开始了自己一天的忙作:上王方榘与金雀国的大臣、将军在王城宫殿里一同商议国家的大小事项;行兵在校场操练或者在城中巡逻;农人扛着锄头去城外的农田耕作;被官府雇佣的破产者在大街上进行清扫和维修。
然而在这最后的早晨里,直到太阳完全升起,整个城中的宫殿、街道,城外的农田里,都空无一人。金雀祖先的祭祀活动消耗了所有人的精力,此时他们也不过刚刚睡去没多久。
江布在饥饿和寒冷中醒来。他拼命的从束缚自己的麻绳中挣脱出来,然后跌跌撞撞的来到大街之上。环视四周,祭祀仪式过后的祭台上空无一物。他不由自主的抬起头,把目光转向了城楼上的祭台。
城楼之上,守护祭台的卫兵喝醉酒之后横七竖八的躺在地上,若不是因为是特殊的日子,恐怕这些人都要被上王发派到西南高原去开垦荒地。他穿过这些卫兵,轻手轻脚的来到角楼里。角楼里满是灰尘,只是中间那张放有祖先雕像的方桌格外干净。果不其然,雕像前面的盘子里放着水果和糕点。
“终于可以痛快的吃上一顿了。”小男孩自言自语道。
正当他想要坐下来慢慢品尝的时候,突然听到远处传来了极其细微的声音,那是自己再熟悉不过的呼喊声。
“江布!”
哦,又是自己的母亲。
江布有些沮丧,他必须得赶紧回去,要是晚了一会儿,恐怕又要被惩罚饿肚子了。但是面对着满桌子的食物,这个面黄肌瘦的小男孩实在是心有不甘,他拿起一个香果放在怀中,可又觉得太过明显,很容易被母亲识破。他无奈的把香果放了回去,只拿着两个拇指大小的甜枣攥在手里跑了出去。
天色已经大亮,而人们依然处于沉睡之中。江布在走下城楼之前,又习惯性的朝着北方看了一眼。那是他的父亲在许多年前奔赴战场的时候离去的方向。自打他记事起,每到空闲或者是饿得发昏的时候,他便趴在小山坡上朝着北方看去。这些年来,父亲从未回来过一次,他却对那片区域的形貌了如指掌。
而今天再次看向那边,他感觉到了一丝异样:在极远处的地平线上,已经没有了本该郁郁葱葱的树木,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片快速移动的黑色斑点。江布揉了揉双眼,确定不是自己因为饥饿而产生的幻觉。而再次望去的时候,他终于看清楚了那黑色斑点究竟是什么。
塔塔人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