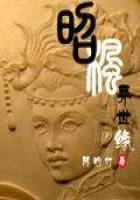第二日一大早,我们三人便收拾好自个儿在花厅集合。外面的天气下着小雨,灰蒙蒙的,就像罩在笼子里一样压抑,蒲灵殊今天脱了爱穿的长衫,换上了一件黑色的风衣,他打着同款色的大伞转身时,头发上的红绳珠子被衬得更加醒目。
“小哑巴,先生这是要带我们去哪儿啊?我怎么觉得气氛怪怪的,有些不舒服。”
花霖拽着我衣袖,把我弄得也有些紧张,因为我明显也感觉出蒲灵殊今天的状态不对。他这两天话很少,不是站在阳台上一动不动的看着外边,就是坐在入定打坐,这样的静默,一天下来,哪怕与他共处一室,能听到两三句话从他嘴里出来,已是幸事。伍锦偶尔会用我和花霖听不懂的哑谜相劝,说他是根傻木头,看不开,直到昨天知道花家的事后,我才明白伍锦为何那样说,因为此刻那人举手投足间,细细看去,全是隐忍的难过和无可奈何的放手。
“没事。”我压了压花霖的手,“先生是不会把你带丢的。”
言罢便领着他跟上蒲灵殊的步伐。
就这样,三把黑色的大伞,一起融进了灰色的雨丝里,再钻进被黑色包裹的汽车匣子里,一起驶向不知名的地方。
开车的是伍锦,蒲灵殊坐在副驾驶闭目养神,我和花霖坐在后座,那小子耳朵里塞着耳机,斜靠着我肩上睡觉。一路上行驶了半个多小时,车子已经离开了郊外,慢慢闯进了盘山公路上,从坐进来的那一刻起都没人说话,一直安安静静的。好想谁都没心思打破这气氛,各自埋在了自己的世界里。
我原本看着车窗上的雨滴出神,不知不觉便把视线慢慢从斜边椅背的缝隙里,移到了蒲灵殊一指宽的侧脸上,这位妖怪先生身上的低气压,都快把他整个人吞没了。
我控制不住的就生出一股冲动,好想此刻把那人拥进怀里,帮他把心里的阴霾挥走,这样,他应该会舒服得许多。
这样想着想着,前面的人突然微微动了动,我不着痕迹的转了目光,落到了模糊不清的反光镜上,那里面影着一辆同样是黑色的轿车在我们后面,但那车牌号……
我熟悉得很。
以前拉来新花苗,于叔让我们去车库里帮忙搬时,都会从这辆车前过,因为那是董事长的车。
我开始大胆的猜测,或许今天这次出门——跟花桥有关。
于是这个猜测,在一个小时后,得到了验证。
不晓得这里是哪座山,也不晓得是哪个没事吃饱了撑的,会在一片暗不见天日的山凹凹里修这么大一座看起来阴气森森的别墅,总之,我从车子停在这里,打开车门下来的那一瞬间,就极度的不舒服,随时有种想要转身逃跑的冲动。
雨水把这周围茂密的林子,都淋得湿漉漉的,水泥路面上除了两道常跑的车轮印,其他地方全被枯叶覆盖着,现在混合着雨水散发在空气中的味道,让我隐隐作呕。
太熟悉了——这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