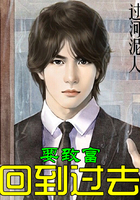沧海桑田千千日,障障百越一日天。福建南平地处武夷山中,林密草深,峦石巍巍,那巅峰峻岭中隐着一条小径,羊肠小径尽头有个庄院,时下有一妇人头挽发髫,身穿长锦,与一小孩儿在那里游戏哩。那小孩儿约莫两三岁年纪,身穿直裰,脖颈上系一银锁,颤巍巍跑过来撞入那妇人怀内,那妇人轻轻一抱,道:“好宝儿,过几日哥哥来看你好不好?”
这时院门呀的一声推开,进来一中年男子,眉目清晰,眼神澄澈,见那妇人怀抱着孩童,喜道:“宝儿,到爹爹这里来。”便张了双臂去接那孩童。那妇人道:“伯远,子修走到哪儿啦?”原来这妇人便是俪如,自从伯远赴任福建后,俩人便接了连理,一年后又有了儿子,乳名唤作“宝儿”。
伯远拿出信函递了过去,俪如拆开来看,只见笔走龙蛇,遒劲有力,认得是子修笔迹。信中言道:
姑妈谨启:
新疆阔别,已逾数载,姑姑大喜,亦未履约,每每念之,常思不肖。幸朝廷天恩,着我赴广州交涉英人之事,遂绕道福建,盼与姑妈重逢。今小侄已过金溪,倘或天公顺意,至南平约略十日路程。万望姑妈保重身体,勿要操劳。此谨奉。
不肖侄子修恭请
俪如阅毕书信,喜道:“子修数年不见,今日迢遥而来,你道我们该如何准备?”伯远道:“你与子修自幼成长,名为姑侄,实似兄妹,今岁围猎山鸡野猪家中不少,我想再需买些武夷山珍给他携带。”俪如听了欣喜,连连称是。
十二日上,日已偏西,伯远忽推门而入,欢喜道:“俪如,你看是谁到了?”便有一男子迎上前来,只见他面容齐整,胡须低平,俪如一眼便认了出来,携了他手,含泪道:“子修,你可是来了。”子修便要作礼,伯远、俪如拦住了,道:“自己家家的,用不得那繁文缛节。”子修见了宝儿,甚是疼爱,陪他东躲西藏,又教他伏高弄低,只是毕竟没有经验,那宝儿却不大睬他。俪如在一旁笑道:“你也该成家啦。”
一语甫出,俪如便知自己失言,自从梁娟在吐鲁番遇险,这些年来给子修提亲的达官显贵又岂在少数,不过一一被他婉言以拒。子修在那沉吟片刻,忽然说道:“不瞒姑妈,说不定年内我便能给你带侄媳妇回来。”矢菊在旁边拾掇碗碟呢,听了吃了一惊,道:“少爷,你可不是给小姐宽心?”子修嗫喏道:“不是,不是。”后面的事却不言语了。
其时已是深秋,才过酉时天便黑尽,俪如忙叫人端了饭食上来,竟是各色山珍野味,又有鲜菌野菜,伯远谦让道:
“南平壤瘠土薄,难得美味,还请子修姑且充饥。”子修听了呵呵笑道:“多年不见,姑父倒是学了欲人客套啦。不过也是,若当日您再心眼活络一些,谈不上总督巡抚,去那江南锦绣地作个府尹却是绰绰有余。”伯远推辞道:“子修说笑了。这南平虽比不得别处繁华,这些年来我旦夕在此,竟也十分喜欢此地的清幽,若得就此终老也是幸事一桩。”
俪如见他俩说得深沉,便过来问询子修:“听闻你在武昌甚为顺利,姑妈可得敬上一杯。”说完便要给子修斟酒,旁边矢菊见了,忙过来接了。子修饮了一杯,道:“姑妈玩笑了。那武昌虽九省通衢,又是洋务重地,但李德隆主政以来,官民多有抱怨,依我之见,多则二十载,少则十几载,定有大事发生。”
俪如恐他酒后乱言,连忙劝道:“这等胡话家里说说也就罢了,到了他处切不可胡说。”子修嗟了一口,道:“我知道的。”俪如便叫矢菊取了他酒杯,当夜安排他住下不提。
第二日上,伯远要去检视水利,子修觉得新奇,便跟了他去。一道上山路崎岖蜿蜒,两人翻过两座山头,伯远手指远处道:“便是那边了。”子修循着他手指方向看去,见那嵯峨矗矗,峰削巍巍,又见那古树参天,乔松凝翠,子修凝眸细看,见那两涧之间横架着一个水车,涧顶飞瀑湍急,撞得那水车吱吱作响翻转不息,两人拔足往前,过了一炷香功夫才到了水车近前。
靠得近了子修才看得明白,原来那水车连着碾车,旁边又建了一座粮仓,工人将那粮食倒入碾车在那舂米呢。伯远道:“自从兴修洋务以来,各省都有了名额,福建八山一水财力微薄,到了这南平兴办洋务就更是举步维艰。幸而这南平山势高耸,水力充盈,便有官员想了这水力代替畜力之法,也好图个洋务之名。不过这一来也有诸多好处,一则农民省了气力,而来有些人家多了收成,只是花费多了些。”
子修道:“兴办洋务花销自然免不了的,姑父还请不要烦忧,过些日子有了收成,那些花销就回来了。”伯远点头抓了一把稻谷,只见那谷粒干扁,用手掂来竟是轻若鸿毛,吃惊问道:“这是何故?”那带头的工人说道:“稻米生长水源最重,犹以上浆时最盛。咱们在这涧中截水开工,下游不少农户少了水源,稻谷故而变得干扁了。”伯远又问:“农户少了收成,怎地不来反映?”那工头道:“他们纵是想来也得知府大人同意不是。再者说了,水车舂米给他们省了多少气力,他们也该忍让一些才是。”
伯远呵呵笑道:“你这工头定是受了官家好处才在这挤兑那些农户吧?”那工头连连摇头,道:“实不瞒大人,我等辛苦劳作一年,统共也收入不了二十两银子。”伯远道:“嘿,你这口气还忒大,二十两银子已够一五口之家一年用度了不是?”那工头知道再往下编排更是没趣,自顾自的干活去了。预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