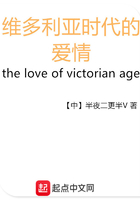“我记得,我当然记得,我在门缝里看到过,阿耶阿娘他们紧紧捂住我的嘴,让我喊叫不出来。”
“可是我还有眼睛,我看到他们在杀人,好残暴,好凶狠,就像恶魔一样。”
“我忘不掉,真的忘不掉,永远也忘不掉了,呜呜呜!”
小女孩的哭声不绝于耳,使得众人都在叹息。
即便有的人想上前安慰一二,也怕惹上那么一个累赘。
一个孤苦伶仃的小女孩,谁摊上该谁倒霉。
在这种世道,自己都养不活,又何苦去招惹是非呢?
李伯禽在人群中,自然也目睹这一切,他叹息一声,看来古代的日子更为艰苦,流寇猖獗,竟动辄做出这种杀人屠村的事,简直丧尽天良。
一个原本美好的家庭就此破灭,一个宁静祥和的村落就此成了一个荒村。
乱世之中,苦难深重。
良久,风停了。
雪也不下了。
小女孩一直哭到再也没有眼泪可以掉下,哭到眼睛酸痛苦涩。
不过心中还有一口闷气在支撑着她,支撑着她想做该做的事,想说该说的话:“我见过,我阿耶给他们送过东西,那是我偷偷地跟着他才发现的,他们要我阿耶每个月送东西给他们,才许诺保护我们这个村子。”
傅奇眼眸一亮,看来果然是一群贼寇,勒索百姓这种事情除了贼寇,没人能干得出来。
这下子,他也就不用再大海捞针了。
他不会安慰人,更何况面前还是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所以说话自然生硬无比。
傅奇看着小女孩,道:“那么你可知道那群贼寇有多少人?”
小女孩抬头望去,没来由地觉得自己应该相信这一群人。
这些人,是大人们口中常常提起的应该敬畏尊重的大唐子弟兵么?
她沉默着,想了一会儿:“大概有六七十人,我听阿耶说过。”
傅奇呼出一口气,六七十人也不算少了,在魏州地界上,这么一大群流寇藏匿于山野之中,无异于无声之箭,危害无穷。
若是今天屠了一个村落,明日又屠了一个村落,弄得魏州人心惶惶,他决然不允许。
何况,现在北地还有一个安禄山,犯上作乱,竟私自集结军队,意欲谋反之心,无人不知。
那个人的名声他自然听过,如雷贯耳,大名鼎鼎,以一介胡人身份得天子厚待,权势熏天。
魏州即将面临这种未知的大敌,指不定哪天安禄山就挥军南下了,内部绝不能存在蚀柱之蠹。
傅奇手托下颔,想了许久,看向李伯禽所在的方向,道:“这群贼寇只有六七十人,现在我给你们一个机会,那是成为正规军的机会,这也是属于你们流民的任务,必须遵从,不得违抗。”
“我要你们这一百三十七人去捣毁贼窝,灭杀贼寇,我想,这并不过分吧?”
傅奇的话一出,顿时引起一片哗然。
那些被认定为流民身份的人看向傅奇的目光尽是不满。
开玩笑,他们手无寸铁,如何去对抗那群杀人如麻的贼寇?
这哪是任务,分明是让他们去送死。
看到流民们的目光,傅奇也不在意,他只等待一个答案,也只需要一个答案。
有人哀怨道:“敢问将军为何要如此针对我们?我们手无寸铁,如何去对抗他们?”
“是啊,还要不要人活了?”
“拳脚难敌刀剑,这是最浅显的道理。”
“不去,我坚决不去,今天即便是死在这里,也不会送上门去让人家砍成七块八段,死无全尸。”
那些正常身份的征兵或摇头叹息,或幸灾乐祸,或怜悯感叹,流民就是流民,在哪里都会有不平等待遇。
区区流民想要平等待遇?此刻看来纯属是在做梦。
傅奇的脸色陡然变得冷漠,声音阴沉如寒渊之冰:“你们没得选择。”
适才还在愤怒出声的人顿时全部噤声,他们怕傅奇一个命令就将他们就地灭杀。
他们是流民,常年奔波,天下无家,来去不定。
总有人求生于市井里,抑或求死于山河间。
这些年来,从来看到的尽是别人嫌弃厌恶的目光,以至于他们都有些自卑局促,甚至都不敢勇于反抗。
看到这群人的表现,傅奇脸上显现出满意的神色。
他首先要清理的蛀虫,就先从流民开始。
他正要下命令,一道声音却不合时宜的响起:“将军,我想问个问题。”
傅奇拧紧眉头,道:“怎么又是你?先前在官道之上,我容许你耽误一时半刻,此刻,你又想做什么?”
这个流民,似乎并没有把他放在眼里。
说话的自然是李伯禽,他如果再不发声,恐怕今日过后,去往魏州的征兵,就只剩两千八百六十三人了。
李伯禽缓缓走出,看着傅奇,不卑不亢道:“将军,我若是用刀剑砍在你身上,你是否依旧能够安然无虞?”
刚说完这句话,便有一正规士兵喝骂一声:“大胆,竟敢对将军如此说话。”
傅奇微微抬手,这个动作让那名正规兵士立刻闭嘴不言,他轻声道:“肉体之身,安能与刀剑利器对抗?这不算是问题。”
李伯禽目光如炬,却自有一股争锋相对的气势:“那么,拳脚难敌刀剑,也是再正常不过的道理。将军既然派出这个任务,就应该明白若是没有兵器,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人,进入茫茫密林之中,就再也没有出来的机会。”
“试问,如何返来回复将军呢?”
“试问,公平何在?”
“试问,既然流民的命不是命,何苦太宗陛下要以天下人皆为臣民?道天下族皆一族呢?”
傅奇怔然片刻,脸上露出异色,被问得哑口无言。
“流民就是流民,若是在其他地方,或许会受重视,可是在魏州,本就没有公平,你们流民,如同星星之火一般,也想与那天间皓月争辉?量力而行是为智,不自量力是为蠢!”傅奇直言不讳道。
李伯禽略微恼怒,没想到在古代阶级之差竟然如此严重,他一朝陷入阴谋诡计之中,沦为流民,也就失去了话语权。
所有陷害他的人,他一个都不会放过。
怪不得世间有万万人,却都趋之若鹜地往那朝堂之上行去,哪怕那座桥下堆满了枯骨残躯。
独木桥下面到底摔死了多少人?没有人会去在乎。
独木桥的彼岸,无论站着多少人,都会受到世间万民的仰望。
高不可攀么?
独木桥的彼岸真的高不可攀么?
朝堂之上,真的不可奢望么?
流民,不可以有话语权么?
今日,他要定了。
他的身子站得很直,气势如虹:“星星之火,却也足以燎原。”
傅奇脸色微黑,看来此人要跟他作对到底,不终止不罢休了。
可是他并不是嗜杀之人,仅仅是天生看不起流民而已。
流民的糟糕印象盘桓在他心里,已有整整十五年,挥之不去。
记得十五年前,他刚刚参军的时候,正为自己成为一名真正的唐兵而骄傲,而自豪,而意气风发,少年张扬。
反观那些同时期的流民,逃窜,无知,卑微,羸弱......
如今眼前这个年轻人,倒是令他生起了浓烈的好奇之心。
傅奇狂笑一声,道:“报上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