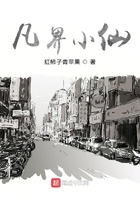彼时乃是仲春,宫道之内春风飘拂,鸟语花香,宫道将各宫切开,两侧高墙彷佛隔着一个世界,但鸟鸣声却彼此串联,各宫妃嫔养的各色鸟儿被挂在屋檐之下,于鸟笼之中嘤嘤作鸣,一齐唤来十分动听,婉转不绝,清脆悦耳。
鸟鸣不绝,花香亦是不绝。宫女走在四处宫道上,不用深嗅,仅仅浅浅呼吸,花香便扑入鼻子,花香盈盈,那是因为皇后早已在立春那日便命内府与丛芳阁送各色花给各宫嫔妃作各宫装点之用了。
现在是仲春,花已绽放开来,香气扑蓬。皇后还觉不够秀美热闹,又命宫女往各宫送了好些花卉。
如今宫内香风盈盈,四处暖融,令人行走其中也觉得浑身舒适,特别是日头虽好,却不觉得热,风也是不热不冷的,吹在身上恰恰合适,令人颇为爽快。
皇帝身边的大太监傅知寒却觉得身上面上跟裹了一层暖乎乎的蜘蛛网般难受,抬起头看到云层之上的太阳,展眸便是湛蓝的青天,看到这青天便忽然想起来多年前自己发下的誓言。
多年之前,大太监傅知寒还不是大太监,而是太子身边的一个年轻侍监,在一次回家探亲之中,听说了亲弟弟傅知凉到处养女人,将他寄给家里的钱挥霍一空,盛怒之下,他竟然失手杀死了弟弟。
之后的每一天,傅知凉都会出现在他的梦里,午夜梦回,他都能听到傅知凉的喊声,傅知凉折磨着他。看到床铺他就会想起傅知凉,睡觉对他来说仿佛酷刑一般。
他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他发誓,他以后再也不会杀人了,再也不会。
没想到,今日陛下又要他去杀人,陛下的意思是了结了圣棋馆的梅初语梅大人。
可他却不能也不敢再杀人了。
“师傅,您怎么在这儿站着啊,怎么不去西殿坐着?”他的徒弟小夏子捧着碗酸梅叶茶,走过来,低眉顺眼地对傅太监笑道。
这些小太监八岁便进宫,在宫内摸爬滚打了多年,却连总管的边都没摸着,唯一能让自己再往权势之梯登上一步的便是皇帝身边的大太监傅知寒。
所以像他这样渴望权势的小太监,早早地便拜了傅知寒为师傅希望有朝一日,能承师傅的恩,成为皇帝身边的红人,或者能从傅知寒身边知道一些皇帝的息怒,以讨好皇帝。
看到小夏子,傅知寒忽然计上心来,伸手搭在了小夏子肩头,和蔼笑道:“小夏子啊,你伺候师傅也有好几年了。这些年,你在陛下身边干的都是换衣拿裳之类的可有可无的活计,师傅也很想提拔你,可就是缺个由头!”
说着,傅知寒丛小夏子手里拿过茶盏,低头喝了口茶,润了润嗓子,又抬头看着小夏子,笑道:“小夏子啊,师傅给你一个差事,是陛下的吩咐,你若干得好,必然得陛下青眼,从此平步青云,再无忧虑。你若干得不好,那就是杀头的罪,纵陛下能饶你性命,师傅我也有手段叫你难活!”
小夏子把头一抬,看着傅知寒和蔼的脸色,知道师傅既然发话,想推脱也推脱不得,何况,师傅既说了自己这些年来少一个被提携的由头,要是这事办得好,不难成为陛下信重的人,乃一口应承:“师傅,是什么事,小夏子一定尽心去办。”
“嗯。”傅知寒拖长嗓音哼了哼,道:“圣棋馆的梅初语梅大人得罪了陛下,陛下的意思是要他死。可是,殷贵妃不是正怀着胎么!陛下不想见血,见血不是好兆头,怕冲了贵妃的胎。所以要让梅大人死,不流血的死。”
“知道了吗?”傅知寒说着伸手在小夏子脑袋上一拍,将茶盏送进小夏子手里,又笑道:“也不难。去太医院找陆归唐大人开副药,让人上吐下泻的药。就梅大人那半老的枯朽身子,上吐下泻一个时辰,就能脱水而亡。”
“师傅,怎不开一副安睡散,听说容泮贵嫔就是邵贵妃用安睡散害死的,一副安睡散下去,能睡三天,三天之后就死了!”小夏子不解地看着傅知寒,傅知寒脸上挂着的笑像是刻上去的一般,傅知寒笑道:“是陛下的意思,安睡散三日才见效,可是梅初语图谋不轨,陛下一刻也容不下他!”
说着,眼里带着笑,看着小夏子,道:“师傅把法子交给了你,敢不敢做,就看你的了。”
小夏子眼珠子一转,点头道:“小夏子明白。”说着,便将茶盏放在了廊上,然后匆匆往太医院方向跑去。
欢存殿内,一片幽香,因无事,皇后只穿了一袭家常的玉色衣裳,粉面着妆,娇俏之中自有端庄气度,头上挽着一个简单的螺堆髻,孤单的髻上只簪着一枝鸾衔宝珠钗,钗上鸾形金坠上垂下三根流苏小珠坠,更衬得皇后气度娴静,端坐在软榻上,手内捧着内府新进的春秋茶细细品着。
身后两名长眉细眼的鹅蛋脸侍女在为她捶背捏肩。
“内府进的春秋茶细细品起来也无甚意思了。往年春天都喝这种茶,都喝腻了。”皇后开口笑说道。
她手托茶碗,左指指尖套着三枚二寸长的璨点玉珠细密状点缀银护甲套,右手却一无所饰,只有食指指根戴着一枚金丝戒指。
皇后声音温婉动听,如她动人的肢体与柔美的面部轮廓一样,给人柔和的感觉。
说着,将手中的茶盏移放在软榻边的荷叶形金面方桌上,左手端着茶盏,戴着护甲套的三根手指微弯,三枚护甲套恰到好处地聚拢在一处,将茶盏稳稳护着,那微弯的三根手指,与微翘的三根护甲套,如同三片弯起的玉兰花瓣,十分柔美好看。
素仪听皇后提起品茶来,立刻知皇后心意,乃微笑道:“说起来,这内府里的泡茶好手也算是黔驴技穷了,远远不及婉仪殿的素贵人泡茶技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