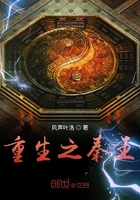郁牧川、尚文诏与街坊友邻们推杯换盏,敬过一圈酒后,席上的客人也换了一茬。
各家妇人、孩童填饱肚子后次第下桌,从自家搬出来马札、小床,就地坐下拉闲散闷,后边的男人们这才相率入席,补上空位坐下吃喝。
尚文诏不许文卿、文姝俩人饮酒,兄妹俩给在座的邻居们见完礼,便坐回桌边埋头大快朵颐。
尚文诏回到主家这桌,同师兄一起给王得地和本坊各火铺的铺丁们一一敬过酒,混个脸熟,算是结识了众人。
王得地今日不知何故酒性大发,他不等打更就叫铺丁伙计们提前闭住了坊门,待伙计们回来,王得地吆喝众人,拉住郁牧川、尚文诏和黄全财几人划拳罚酒,兴致颇高。
几轮过去,座上就数郁牧川输的次数最多,喝的也最多。纵他郁牧川平日自诩酒量不错,在众人轮番围攻下,一时也渐不能支,脸上一会泛青,一会泛红,最后端的连话也说不顺溜了。
众人饮酒嬉闹时,尚文卿趁着郁牧川和尚文诏不注意,避开小妹视线,揣上一把炒花生,独自溜进院里,偷偷喝了一碗烧酒......
戌时初,暮鼓大作,一百单八响鼓声后,郁牧川和尚文诏家的小院前只留了不多几桌客人还在饮酒。
“尚兄弟,尚兄弟。”
“嗯?”
尚文诏感觉有人在戳自己胳膊,他回头一看,正是黄全财。
“黄兄,何事?”
黄全财抬手指了指街口,凑到尚文诏耳边道:
“尚兄弟,你瞧,瞧最外边那桌。”
尚文诏有些摸不着头脑,“那桌如何了?”
黄全财蹙起眉头:“老弟,我可瞧了好一会儿,那两人不是咱们坊中的住户,我不认得他们是谁!”
尚文诏狐疑:“黄兄不认得?”
黄全财不住点头,他道:“我看像是来蹭吃蹭喝的。这二位坐在那里少说有半个时辰了,嘿你说这厮,不然咱去给他们撵走?”
尚文诏打个饱嗝,拍着黄全财的肩膀道:“黄兄,何必,今日来了的都是客,你且坐着,待我去看看二位朋友。”
尚文诏从桌上抽身,抱起一坛未开过的烧酒,抓了几只小碗,径往黄全财指点的那桌而去。
“两位兄台,今日的饭菜如何,可算称心可口?”
尚文诏将怀中的坛子摆到桌上,对两人作个揖,随后坐到二人对面,打量起两个混吃混喝的家伙。
尚文诏粗看一眼,桌上两人一老一少,上首的青年四肢纤细,形貌清瘦,头上戴着一顶精致的苏样鎏金小帽,身穿缀了云纹的青色罗衫,外边还套着棉绒比甲,脚踩一双白边官人靴,一身富贵打扮,也不知是哪个豪奢绅衿之家子弟。
公子身边坐着的则是位健硕魁梧的悍仆,那悍仆的衣装简朴干练,面容粗犷,蓄着短胡须,脸上密密布了长短不一的可怖疤痕,宽厚的脑门下面,一对煞气十足的大圆眸正紧紧锁定在尚文诏身上。
“你就是主人家啊,你家饭菜还算可口,我喜欢!”
答话的正是上首那位清瘦公子,这人不止身材消瘦,嗓音也十分细腻。
悍仆垂头提醒道:“咿,小......少爷莫与生人多说。”
尚文诏看那悍仆举止怪异,也不理他,拱拱手对那贵公子道:“公子过誉了,都是些家常小菜而已。”
上首那公子回看尚文诏一眼,露齿一笑,仿佛听进了悍仆的话,也没再与尚文诏搭话,他自顾自地抓来一只皮酥肉嫩的鸡腿,埋下头继续狼吞虎咽。
尚文诏见这主仆二人神神秘秘,坐了半天也没再言语,他识趣的不去问,缓缓斟上三碗酒,给对面两人各推过去一碗。
少顷,那公子仿佛酒足饭饱,他停箸坐稳,不知从哪里拈出来一张素白的手绢,三两下将嘴角的油渍抹干净,又侧过身与自家悍仆耳语了一阵。
那悍仆代主人低沉道:
“我家小......少爷说,多谢主家款待。”
公子又凑近悍仆耳边嘀咕了几句,悍仆应声点点头,对公子叽里咕噜低声念叨了一通。
尚文诏侧耳细听,悍仆说的最后一句仿佛是——“的确是流水席,不过小人也不知主家为何办。”
公子说罢,一摆首,悍仆便往桌上拍了个沉甸甸的大银锭。
悍仆道:“这是我家少爷与你的赏钱,主家收下吧。”
尚文诏笑眯眯的观察着面前的公子,他那一对本来就不大的眼睛渐渐眯成了一条缝——对面公子身上的衣衫松垮垮的,较其清瘦娇弱的身材,明显要大上一圈。
尚文诏捏捏鼻子,再细看两眼,这公子皮肤白皙,腰肢甚细,他视线往上一挪动,公子的脖颈上竟没有喉结!
“这又是何苦来?”尚文诏在肚里叨了一句,他心道:
“怪不得,只怕这位公子是刚从闺阁里偷偷溜出来的吧......天底下的纨绔子弟们,哪个不是自小就飞鹰走马、纨绔浪荡,吃喝嫖赌样样精通,等闲小家小户摆个大棚流水席,哪里能叫豪奢世家子弟们瞧上眼?”
尚文诏看穿了眼前这位公子乃是女扮男装,心里兴起了逗一逗这富家小姐的意思,他问那假小子道:
“兄台,这银锭又是何意?某今日摆酒不过是贺一贺乔迁之喜,二位既然来了,便不必客气,敝姓尚,名文诏,敢问兄台尊姓大名?”
那女公子听尚文诏喊他兄台,刚要开口自报家门,蓦的意识到自己不便开口讲话,硬生生将嘴边的话吞下肚去,她凑近悍仆耳边,嘟囔几句,悍仆便又替主人说话了。
“我家少爷,咳,我家少爷近日里口舌生疮,喉头发涩,一出声嗓子就痛痒难耐,不便讲话,家少爷免贵姓唐,名讳嘛,少爷道,额,相逢何必曾相识,若日后有缘聚首,那时再互通姓名也无妨。”
尚文诏忍住笑意,绷着脸道:“唐少爷,口舌生了疮,那明显是五脏六腑失调,肝胃上虚火炽盛,这位大哥,我说这便是你的不是了,你家少爷都病成这副鬼样子了,你还敢叫他吃烧鸡,你是想害你家少爷喉咙溃疡失声吗?”
尚文诏自然不懂医术,什么肝火胃火失声都是瞎诌的。
假小子闻言,又捂住嘴噗嗤一笑,她身旁那悍仆有些坐不住了,悍仆怒道:“嘚,你这贼小子,怎么说话的,竟敢......”
话说到一半,那假公子掐住悍仆胳膊一拧,悍仆吃痛之际,明白了主子的意思,登时收了声。
假公子照旧耳语,悍仆气鼓鼓的道:“这位,嗯,尚贤弟,我家问,你家这葱末烧鸭是如何烧制成的?”
尚文诏心中暗暗发噱,“这小姐也忒没见识”。
今日流水席上,整桌的菜都是黄全财请来的李婶带来的厨班烹制,他又哪里晓得如何烧制?
尚文诏一拍桌子,来回扫视二人一阵,装模作样的道:
“不瞒二位,这葱末烧鸭的制法,乃我师门不传之秘,此秘方嘛,系我师尊南山厨王十载呕心沥血钻研出来的,唉,小子实在不敢擅露天机,将这秘方传出大众,若坏了师门规矩,小弟怕是要被逐出师门的,二位谅解则个。”
“噗哈哈......”
那假小子捧腹而笑,再也端不住了。
“狗屁!你胡说八道!”悍仆拍桌子瞪眼。
假小子见悍仆发作,眉头蹙起,似有嗔意,狠狠剜了悍仆一眼,悍仆仿佛也意识到了自己失态,在主子怨厉的目光下,如哈巴狗一般再次收住了威势。
“过瘾。”
尚文诏摇头晃脑,暗暗得意之时,悍仆又发话了:
“我家少爷问你,愿不愿意来我家府上做事,进火房月钱十两银子。”
“火房就给月钱十两?果然是豪富人家。”
尚文诏婉拒道:“幸得公子看得起,小子乃一山间野人,放纵惯了,怕是做不得火房中的营生。”
假小子锲而不舍,又对家仆耳语几句,家仆道:
“哼,不识抬举,我家少爷道,既然尚兄不愿泄露秘方,那就请尚兄弟明日再照今日这例,做两例一模一样的烧鸭,明日正午时,送到棋盘街齐贤酒楼的牌幌底下。”
“好嘛,还真把我当厨子了,这小姐家的厨子就没做过烧鸭?看来李婶这厨班的手艺是不错的。”
尚文诏忍俊不禁,在心中暗道。
悍仆说完,不等尚文诏答复,径自起身走到了尚文诏身边,他给尚文诏露出一块铜质腰牌的一角,尚文诏看见腰牌,登时惊得动也不动。
铜牌子上赫然镌着两列——親軍羽林衛鎮撫司掌緝事校尉,懸帶此牌百戶錢。
“天子亲军......羽林卫的镇抚司......钱百户......”尚文诏喉头发涩,不住干咽。
那悍仆凑近尚文诏,狠狠道:“小子,有胆逞口舌之利,今日之事,老子看在少爷的份上,不同你计较,明日莫给老子耍花样,照我家少爷吩咐,准时送来烧鸭,不然有你好看的。”
悍仆说完,返回到假小子身边道:“少爷,咱们回吧,小人已经给那火夫说清楚了。”
假小子点点头,眉睫一忽闪,又扔下一块大银锭,起身随那悍仆一齐消失在了夜色中。
“掌印指挥使家的小姐......娘的,祸事了。”
尚文诏自掌一记大嘴巴子,呆愣了好一会儿,他将桌上那两个大银锭揣进怀里,返回到小院里。
戌时末,每夜在街面上四处巡回的更夫来到了崇北坊外报时,坊内杯盘狼藉,宾主尽欢,尚文卿搀扶着喝到不省人事的郁牧川回屋休息,尚文姝与厨班伙计一同归整着餐具,大伙兴尽而散,个个面带笑容,整个院子里独独尚文诏愁眉苦脸。
尚文诏扒拉出银袋,塞给李婶一两,问了李婶今日的荤菜都是哪几位大厨烹出的,请李婶留下那几名厨师。
李婶走后,尚文诏给留下的两位大厨每人发了五两巨款,请两位大厨赶在明日隅中时,每人烧两例与今日一模一样的葱末烧鸭出来——万一意外横生,哪位厨子明日没法做菜,他也总是留了后备的......
约好了取鸭肉的时间,尚文诏送走厨班诸人,他感觉酒劲上头,简单沐洗了下身子便回屋歇息了。
翌日鸡鸣未至,郁牧川还沉在梦乡中打鼾,尚文诏就摸黑起了床,收拾停当出门时,文姝也起了,她打着哈欠问:
“大哥,这么早你去哪里?”
尚文诏行色匆匆道:“卖烧鸭换钱,大哥走了,后晌回来,等郁哥醒了,告诉他,我后晌回不来,就别去应举了,让他带上你和文卿回江陵。”
文姝点点头表示听清了,目送尚文诏离开院子,她准备去烫水洗漱,她蓦的一愣,仿佛品出了尚文诏的话不大对劲,文姝追出院子,正想再问大哥几句,却见尚文诏早走得没影儿了。
从小院出来,尚文诏直奔外坊早市,买了四只肥嘟嘟的大胖鸭子,随后将四只鸭子分别送到了昨日那两位大厨家中。
送罢食材,尚文诏便一直在大厨家中待着,焦急地等着烧鸭出锅......
......
正午,尚文诏提着两只盖了数层羊绒与棉麻的竹篮子,准时出现在棋盘街的齐贤酒楼店幌下面。
“嘻嘻,贤弟,你这么听话,我好高兴!”
尚文诏循声望去,说话的不是昨日那假小子又是谁?
“小子不敢迟来,兄台,请点验烧鸭!”
尚文诏毕恭毕敬道。
“喏,贤弟,这里是一两银子,赏给你!”
尚文诏抬头一看,唐姓假小子今日变了一身打扮,昨日她身上那件云纹罗衫换成了一件青边点黛白褂,头上那顶苏样小帽也换成了方巾。
那悍仆亦如约而至。
悍仆接过烧鸭,掀开遮盖在篮上的棉麻,忽左忽右嗅来嗅去,还不时动手从烧鸭边角上揪下几片肉来亲尝,很是细致地检查了一番。
“还怕下毒?老兄也是够心细的。”
细察一阵后,那悍仆对假小子道:“少爷,咱们这几日太过招摇,早晚......”
“不听不听我不听!”
“哎哟,小姐莫嫌小人麻烦,小人也难办的很!”
悍仆阖住嘴巴,他自知说漏了嘴,向下首的尚文诏瞧一眼——只见那尚文诏耷拉着脑袋,傻呵呵地踢着脚边石子,边踢边傻笑,丝毫不敢近前半步,恨不得离他主仆二人八丈远。
悍仆满意的点点头,心道这小子懂事,便是给他听到了,谅他也不敢胡咧咧,于是继续劝自己小姐道:
“老爷不日便回京,小姐,咱们还是早些回府吧,莫叫大公子担心,若叫老爷知道了大公子没管束好...呸,小人该死,若叫老爷知道了您私自出府,大公子和老爷定要责罚小人啊!”
情急之下,唐小姐也忘了顾及仪态,她嘟囔着道:“七叔,你是不是不疼人家了?说,你是不是同我大兄勾结到一起了?咱们这才出来几天,人家还没玩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