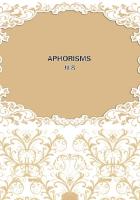收好玉佩,告别小猫,沈云简离开蓝溪谷,进入闹市。两日不入闹市,竟有些不习惯。许久没有进食,早已是饥肠辘辘。便找到一家面馆,打算先来碗阳春面果腹一番。
可就在自己坐在店里慢慢吃面之时,一个男人匆匆跑进店里,拽起他的左臂就要往回拉,显得十分着急:“哎呀殿下,你刚吃了不是吗,咱们赶紧赶路吧!”
这沈云简不知所措,一看,是位官郎,便问:“什么殿下?相公,您找错人了。”
官郎打量他全身,有些犹豫:“只是换件衣服却不改容貌,这不像是殿下的作风。”
此时,官郎注意到店门口有人,转头看去,不由得吃惊了:门口的曲裾青年,才是他找到殿下。最惊人的是,这个襕衫青年,与昀昕长得简直一模一样!
“植轩,别丢人现眼了,走。”昀昕一摆头,随即离去。官郎瞅了沈云简一眼,随后离开面馆。
刚刚那一幕,沈云简也愣住了:天底下,居然能遇到和自己同一面庞的人!
回过神来,沈云简匆忙跑到昀昕的面前拦住他。“打扰一下,敢问尊姓大名?”
昀昕浅浅一笑。“刘姓,名昀。”
沈云简低头思索片刻,再次抬头时,却找不到二人了。他四下张望,“哎?刚才的两位,怎么这就说没就没了?”
过了些许时日,昀昕与罗茗快马加鞭,在益都县博山驻站歇脚。此时,正是连绵夜雨,二人照例在旅店过夜。
“益都临近济南府,我想很快就能回去了。眼看冬至就要来临,济南府多温泉,冬日较温暖,也适合过冬。”罗茗倒是很兴奋。
“我自是不惧冷热。若是孤身一人,早就飞去了。可现在顾及你,所以得陪同前往。”昀昕却是冷淡的模样,毫不激动,“我们应晚些时候再去济南府。”
“为何?”罗茗顿感疑惑不解。
“我不想碰到那个和我有着相同面孔的男子。”昀昕干咽了一口,“我同样也不想遇到宋惠那个家伙。”
“那天遇到的那个男子是什么人?”
“那个人是谁不重要。不过他和我同样的面孔绝对不是偶然。他是柳源的学生,而且还有一个对录纳部来讲重要的作用。”
罗茗追问:“那宋惠又是何人?”
“之前我们见到的,那个自称天官大冢宰的男人。虽然摸不透他的底,但之前也与他打过交道。别看那人冷漠,可心如海底针,明杀暗害过不少人,还是小心为妙。”
罗茗想继续问什么,却又欲言又止,只得拱手作揖,“详情不便多问,那植轩先入寝了,殿下自便。”
罗茗一人宽衣解带,侧身入眠。耳畔无他声,昀昕顿时思潮起伏,想起来自己与杜冶宋惠等人的初次见面。
杜冶并不是一个常人,他应当是史册上死过一次的人物。而救过他的人是谁,又为了什么私心救他,自己却不知为何。或许是当初的晖,也或许是宋惠。
想到杜冶时,总能莫名联系到如今的柳源。他俩,或许有什么共同之处。
第一次知晓杜冶,是五百多年前的事。
那时候,刚经历仕途失意的年轻人杜冶,归乡返途中,途经济州,在人声鼎沸的街巷漫无目的走着。这时,周围的百姓像是看到了什么恶霸,匆忙朝他的反方向跑去。
他被蹭到了肩膀和大腿,原本魂不守舍的他猛地清醒过来,站在原地看前方发生了什么。一个红袍垂耳幞头郎官,像醉酒般拨开众人冲在他面前。
杜冶上下打量着这奇异的公服,小声嘀咕:“这莫非是父亲说的……录君?”
然而来者不善,红袍郎张开右手,手里凝聚出一支蘸墨的毛笔,他握紧毛笔朝半空划一道笔顺,墨迹划过消失,顿时杜冶被隔空打飞,摔落在无人的平地上。
浑身剧痛的杜冶不知自己招谁惹谁,为何要攻击自己,艰难起身后想要询问,哪知还没来得及开口,就看到那人凭空画出了个“水”字,随后自己脚下四周出现一滩黑水,自己跌落其中,眼看就要被淹没。
眼看就要冤死在其中的杜冶,被一只手硬是从黑水中拽了出来,那潭水随之消失。
杜冶尚未道谢,就看到一个赤襦黑裳的年轻男子,背对着他站在身前,面向面前的红袍郎。
红袍郎轻蔑一笑:“晖君,你管的似乎有些多了!这可不是你管辖的神官!”
“哦,是吗?很快他就是了。”晖的右手里变出一支相同毛笔。红袍郎见状划出一个“井”字,晖也随之挥出一笔。“井”字回弹,红袍郎被掀飞,半空中受到“井”字笔画的四处攻击,跌落在地。
“你这小小神君,还是没认清自己的定位啊。”晖冷嘲热讽着,低头把弄手里的笔。“昀昕手下管辖的神官,原来是些表文内武,只懂残害的道貌岸然的家伙。”
身后的杜冶慢慢起身,作揖答谢:“谢相公救命之恩。”
“晖,给我等着,昀昕殿下会来收拾你的!”红袍郎气急败坏的大喊,狼狈逃窜。
杜冶追问道:“那真的是录君?为什么行事像个恶棍?”
“是昀昕眼光不济,选错了市井之人。”晖说着,转过身来看着他。“不若来我这里,做我麾下的录史神官如何?”
“这……罢了,我只想像普通人一样活着。”还没说完,身体便像被控制的傀儡一般绷直僵硬了。
晖漫不经心地掏掏耳朵。“在下刚才没听清,可劳烦您再说一次?”
“我愿意做您的录史神官。”杜冶平和地回答道。
晖仰天狂笑。
后来这件事传到昀昕耳朵里。昀昕知道那绝对不是录君做的,定是晖自导自演的把戏。杜冶是两方都看上的人,而晖用这种卑劣的手段夺得,实属令他作呕。
不知为何,多年前昀昕这段尚且清晰的记忆,不知为何变得模糊不清,连救杜冶的人是谁都无法记清。难道是修史者抹去了谁的历史?可修史者是谁呢……
遇到宋惠,想来也是好几年前的事了,那时候,徐泊与柳源,还是济南府录纳部的两位神君,同样也是两大主考官。只不过,他们临近退休,境况也窘困。
自从雁神书信那件事后,徐泊就寝食难安。他觉得,自己会有生命危险。不仅是自己,他想,柳源也是。
他私下与他在录纳部的轩阁中会面,和他交谈了一些事情。
“徐公,你真的要自请削除神官籍?”听到徐泊的话,昀昕不禁惊讶无比。多少人向往的荣耀,而就这样,想将它抛却。
“我身体老矣,不能为圣上效命了。希望,殿下可以上报神皇,应允此事。”
昀昕当然明白,这只是借口。徐泊随柳源在双派之间夹缝生存,现在,自己赶紧离开,或许还能好好活着。虽行事问心无愧,但每天依旧心惊胆战。老了,向往安逸了。
“那你的友人柳公可知此事?”
“尚且不知。只怕知晓,他会想法子斥回我上疏,把我留住的。”
昀昕想拒绝此事,却内心纠结,难以开口。“你知道,你和柳源,现在是多重要的角色,你们掌握着两派的一些秘密,你觉得,能脱身?在我这边,我还能保你平安。你若是被害,我可救你不得。徐公,慎行。”
徐泊作揖回敬:“谢殿下叮嘱。只是心意已决,是生是死,全由自身承担。”
昀昕一声长叹,以示惋惜。“随我走吧。”他徐徐起身,离开小轩。
哪想殿外站着位不速之客。
二人正准备回殿,却看到台阶之前,一位红袍金色祥云纹的男人背对他们。昀昕警觉起来,伸臂示意右侧的徐泊停下脚步。男人转过身,昀昕察觉到他胸前秀有金织团蟒纹。
徐泊大惊失色,颤抖着手指向此人:“宋,宋叔仁!你,你怎会来此……”
“宋叔仁是何人?”昀昕把头转向徐泊。
“天官,大冢宰……宋惠!”
宋惠冷笑一声:“徐公,你以为你和柳公,还逃得了吗?”
昀昕上前一步,挡在徐泊前面,“喂,宋叔仁,徐公可是对我等很重要的人,有我在此,你还妄想伤他不成?”
“殿下,是这样吗?”宋惠嘴角上扬,他甩甩衣袖,身后的徐泊凭空被掀飞,只听一阵惨叫,他跌落至昀昕的左手边。
“不对你动武怕是不行了。”昀昕冷笑一声,腰间自动系上一条蹀躞带。随即身上燃起幽火,幽火消失,身上穿着黑色的贴里服与罩甲,头配唐巾,腰间斜挂一把剑。
宋惠不屑地低声“哼”了一声,踱步迈向跌落在地的徐泊。昀昕眉头一皱,欲瞬移至徐泊面前,却被一道无形的屏障弹开。起身再战时,却发现脚下出现了五行青木阵,困住自己动弹不得。
宋惠停下脚步,得意地看着他,“殿下,你应该记得,你最初是附身在大汉皇子之上。大汉是崇黄色,是因为五行中,黄土克黑水,而秦崇黑。青木克黄土,故此,殿下你被我控制住了。”
昀昕还在挣扎:“怎么……我可是神明,你能困我多久?”
“不需要多久。”宋惠保持冷漠的面容,转向仰坐于地上的徐泊。手无缚鸡之力的徐泊惊慌失措,身上的余痛感还未消失,难以站起,根本无力反抗,只得连连后退。宋惠步步紧逼。
“究竟,要我怎样,才能留下我这条老命……”徐泊有气无力地发问,他几乎已经是放弃活着的希望了。
宋惠抓起他的衣领,冰冷的眼神直勾勾地盯住他。“可惜,我不能让你活着。还是神官之躯的你,现在无比脆弱。徐公想除籍,抱歉,没有机会了。”
说着,宋惠身上的红袍变成银袍。随之,他从左腰的蹀躞带上抽出剑鞘。
徐泊知道,自己马上就会消散殆尽,不禁悲从中来,可悲的是自己还没料理后事,不知自己的家人要如何,亦不知柳源得知此事会如何……
杀戮——五行白金!
剑刃刺穿了他的胸膛。他的素衣被染的一片血红。恍惚中,他隐约听到宋惠对他说:“老家伙,你知道的太多了,还不老实。带着你的秘密,下黄泉吧。”
他被踢翻在地,伏在地上。他的身体渐渐化为一缕青烟,随风而逝。
待宋惠回首时,昀昕才挣脱阵法控制。昀昕气呼呼地痛喊:“敢在我面前杀人,胆子不小啊!下面,就轮到柳源了吗?”
“柳源毕竟是我前辈,未尝不可留一命。可若是不肯老实,那就别怪我们残忍了。”
“现在还是想想自己怎么全身而退吧!”昀昕大吼着,掏出十八神君之难君印,顷刻间乌云密布,雷电交加,巨雷劈向宋惠,四面产生一堆黑烟。
就在昀昕自以为解决此人之时,黑烟散去,却是一条四趾蟒,盘绕其身,保护着他。宋惠完好无损,神态也依旧波澜不惊。
“你竟然有蟒护体!”昀昕惊叹。
“我只是遵六官总令的来访者。”宋惠说罢,身体化为金光隐去。
柳源最终还是知道了这件事。
丧失了友人,悲痛的他,只得一人在殿中借酒消愁,却不想只是愁更愁。醉醺之时,他满面潮红,摇摆不定地站起,走到墙角一侧的书架,疯狂拍打着,骂着:“你这个……老东西,怎,怎么,不陪我……继续论史了,了呢……你,你的医世志,去,去哪儿了……”
纵使昏迷,他还是明白,徐泊真的永远消失了。他用尽力气,从那书架上翻出一只笔。那是他们曾经录史时用过的。
内心的酸涩与无奈交织,他苦笑道:
“录史官,留我一个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