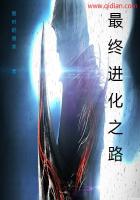青月容镇日无事,便在宫中习文练武,她深知自己如今虽被圈养,但文武之技不能荒废。只是翊坤宫中终日刀光剑影,教宫人们极不习惯。
一日,青月容正在院中练剑,祝桐芙忽然快步走过来道:“你快去看看罢,你那宝贝二皇子又被他父皇打了。”
青月容将冰玉剑收到鞘中,问道:“景仁宫又央人来传信了?”祝桐芙低声道:“是我安插在景仁宫的耳目偷偷给我报的信。”
青月容自幼受母亲青水涟教导,身为人君者,须得对天下之事耳听六路,眼观八方,万事万物尽在掌握,却又要做到少说、无为,这样的君主才会既令臣下敬重爱戴,又不至于被臣下当成昏聩之君随意戏耍。青月容想前朝后宫皆是一般,因此和亲来白陆国后,便拿出大量银钱,教祝桐芙去各宫中安插眼线,方便自己掌握白陆国后宫的情况。如今,这眼线总算派上了用场。
青月容准备提剑去景仁宫,却被祝桐芙拦住了:“你去就去罢,拿着剑做甚?”“我去宰了打易儿的那两个内监。”祝桐芙撇撇嘴道:“你这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次数也太频繁了些罢。”
青月容听她话音不对,转头看向她,含笑道:“怎么?你吃醋了?”祝桐芙道:“我才不会吃他一个小屁孩的醋!我只是提醒你,他是白陆国的男人,你就算再怎么宠他爱他他也不会跟你回国,嫁给你。”
青月容被她说得也有些不好意思:“你说甚么呢?我对他可从没有那个意思。”“问题是你对他也太好了些,很难不让人想歪。”“对他好怎么了?我对你也很好啊。”“这么说在你心里他跟我一样重要了?”青月容笑着道:“还说你没吃醋?酸味都飘出八里外了。”
祝桐芙一把按住了青月容握剑的手,岔开话题道:“你真不用带着剑去,行刑的内监早就走了。你想想,白老儿在的时候,宫人哪敢擅自出来报信呢?”
青月容与祝桐芙来到景仁宫白流易的寝殿。白流易一见青月容来了,赶忙故意不停呼痛,跟青月容撒娇。青月容一边亲自为他上药疗伤,一边心疼地问道:“你父皇为甚么又要打你?”
白流易噘着小嘴道:“他忽然要来考较我跟哥哥的学问,我没答出,他便将我一顿毒打。”
青月容一听是这个缘由,故意板着脸道:“要我说你这次便是该打,谁教你平时不用功来着?要我说,你父皇还打得轻了。”白流易见青月容不替自己说话,小脸气得鼓鼓的,白流金在一旁看着好笑,不禁“噗嗤”笑出声来。他这一笑让白流易更为生气了:“你也笑我!我还不是为了你挨打。父皇原本先考的是你,我见你答不出,才故意抢着答,故意说得驴唇不对马嘴,惹怒了父皇,挨了他一顿好打。我若不这般,怕是你也要似我这般趴在床上了。”
青月容听后,忆起他当初舍命为祝桐芙顶罪的事,心想,易儿这孩子平时看着倔强,可他为对他好的人付出,却总是不计代价。
青月容心中虽心疼白流易,嘴上却依旧道:“你们兄弟俩也太不刻苦了些。”
“才不是呢!”白流易的小嘴撅的更高了:“分明是那张太傅不肯好好教我们!”
“易儿!”白流金在一旁训斥道:“不可与母后顶嘴!”
白流易闻言委屈地撇了撇小嘴,青月容轻轻拍拍他的头道:“无妨。”又转过头问白流金:“他说的可真?”白流金道:“张太傅……总讲些十分高深晦涩、儿臣听不懂的话,儿臣们也曾问过他,他却斥骂儿臣们说我们不够用功,方才听不懂他说的,是以儿臣们也不敢再问。只是他讲的课,儿臣们越发听不懂了。”
青月容问道:“你们和三皇子都是张太傅一人在教?”“不是,三皇弟是刘太傅教。”
白流易插口道:“张太傅和宰相王郭关系甚好,肯定是嘉贵妃故意教他不好好教我们。”
青月容沉吟道:“皇子太傅都是宰相王郭的人,这嘉贵妃,真是要霸天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