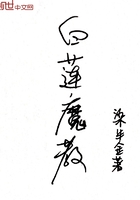面对肆无忌惮的江湖道门,大燕将屠刀首先砍向佛宗。
夏日炎炎似火烧,天下佛寺齐折腰。大燕二十万灭教铁蹄踏破一个又一个寺院,驱逐僧侣数万之众,经书佛法燃烧的焰火,遍及大燕个州道府。
官道之上,一列列披戴枷锁的僧侣,在军差的押送下,向西驱逐,稍有拖沓便有鞭棍加身。佛宗立世数百年,从未面临过今日的苦难。
千佛万众朝西去,天下无人颂佛经。佛经寺院付一炬,尘世无处是空门。
数万僧侣齐叩首,面朝佛土口无禅。佛渡世人,又有谁来渡佛。
西土凌寒地,无处不是料峭的岩石,山峰覆盖皑皑白雪,一年四季不化,这里是佛宗的发源地,隔离尘世,保留下最纯粹的佛法教义。
菩提伽那,天下佛宗出于此,古佛坐化地,每一天都迎来朝圣者?他们历经千难万险,走过无尽雪山来见真佛,古往今来,这条朝圣路埋葬了无数信众。
菩提伽那,这座堪比一城之巨的寺院,迎来了大量衣衫褴褛的僧众,他们被一路驱逐,踏入苦寒西土找寻佛宗最后的净土。这一路,成千上万人倒下去,葬身在无垠的雪山中,幸运活下的僧侣在今日得见净土。
在这一众僧侣之中,一个枯瘦的小和尚,怀里抱着禅师临终赠与自己的佛珠,面相菩提伽那五体投地,口中梵音不断,稚嫩的口音回响在净土。“无世无我,花开如来,一朝得见真佛时,今日方知我是我。”
小和尚沿着陡峭的台阶,一步步攀登向上,菩提伽那响起万千佛语梵音,一扇扇门禁打开,一步一钟声。这一刻,阳光撕裂白云,白雪覆盖的庙宇顿时散发耀眼的金光,小和尚口诵心间自生的如来真经,一路宝相庄严,沿路僧侣口诵佛陀跪拜下来。
“未曾生我谁是我?未曾生我本无我。生我之时我是谁?生我之时迷是我。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菩提伽那十万僧众齐叩首,三世如来归来时,大雄宝殿再无空,真佛已经从红尘归来,我佛不灭,佛宗当盛,佛法不空,真佛往生。
大燕时隔二十年再次展现一统天下的实力,虽然世道混乱,大燕依旧是尘世间最强大的屠刀,没有人能够扶其眉须。当世三大宗教的佛宗被赶回西土,数百年地繁盛发展,全部成空。
经书付之一炬,佛陀金身砸碎一地。寺中荒草掩空门,世人不诵菩提声。
杀鸡儆猴,大燕用事实证明,国力依旧强盛,朝廷政令通达天下,再无质疑反对的声音,大燕国迎来建国以来的第二春。
燕历二十六年,政通人和,农商皆富足有余,大燕顺利推行食货法,收效巨大。左相公赵甑因推行食货法为世人称赞,富商甲天下的江南道,为铭记左相公的恩德,于太平湖畔立生祠竖长生排位。
京都汇聚天下八成财富,今年由盛。一辆辆装满财货的马车通宵达旦运进京都,喂饱了大燕朝堂,喂饱了官宦名门,大燕一年的赋税比得上往常数年之和。
在一片丰收喜悦中,大燕兵马司频频调动,不知不觉间将三十万雄兵调往东海之滨,在京都第一片秋叶落地之时,大燕三十万军队,对肆虐已久的东海道海贼发起冲锋。
在半年围剿海贼的战争中,一位白袍小将脱颖而出,一杆白银抢在乱军之中七进七出,无人可挡一合之力,李牧的声名出现在燕国上层的眼中。
军道世家的后裔李牧,加封白马校尉,大燕继唐念奴这位年轻的剑道宗师之后,又出现一位年轻的枪王。多位将军联名上表,称赞其有唐王年少之风,实为大燕可造之才。
大燕这一年用屠刀逼退世间佛徒,平定内患,加之丰厚的赋税,俨然有了一丝盛世景象。
太庙学宫,唐念奴安坐在儒首的面前,二人已经争执已久。
儒道以仁治世,兵家则是乱世而起,杀伐镇世,乱世用重典还是仁义安天下,这是亘古难辨的话题。
唐念奴在学宫近一年光景,每日里除了饱读藏书,再无琐事。今日是儒首第一次和他大谈仁爱治世,将兵家之事贬的一文不值。
千百年来碗里羮,怨声如海恨难平。欲知世上刀兵劫,但听屠门夜半声。
武以军乱世,儒以文误国。二者生来就是在矛盾中寻求统一,平衡之道就是治国之道。
儒首面红耳赤,八十多年的养气功夫破于今日。近乎嘶吼的给唐念奴灌输儒家仁义。唐念奴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平日里的儒首是一个威仪稳重的儒生,今日里,言语无不透露着一丝绝望。
儒首平复久矣再问道:“唐念奴,你如何看待当今燕国?”
“表面粉饰太平,内里霍乱掩藏。”
“是你这样看,还是你家的女诸葛这样认为?但倒是看的明白。汝可听过九索占卜法?”
“儒道独家的占仆之术,闻名天下。”
“九索占卜,向天九问其索。一个人一生只可有九次占卜的机会,吾一生为燕帝占卜过三次,为你占卜过三次,为儒道占卜过三次,昨夜是我最后一次占卜,占卜儒道未来?”
“福祸自有天意,儒首又何必纠结。”
儒首叹息道:“吾三岁习字,五岁温书,活到今日九十有六,生死早已知晓,学而无涯,到了今天我依旧是儒道的一个小学生而已,生平之志不过儒道二字。”
儒首寻来一柄戒尺,接着说:“生死有感,我自知追寻前贤的时候要到了,依旧是忍不住为儒道占卜了这最后一次。可惜,我预见到儒道凋敝,天下无儒的场景,一如今日之佛宗。世间无佛,世间无儒啊。”
唐念奴摇头:“儒道之于燕国,如水之于鱼,何来灾祸?”
“凡国立者,无不盛世起,乱世终。燕国立国二十几年,从未有出现朝气蓬勃的太平盛世,只懂以杀止乱之道,不思开民教育之本,亡国之道矣。待到民不畏死,再以死惧之的时候,就是燕国国灭。”
唐念奴低头沉思,儒首所言非虚,燕国立国至今,没有一年停止兵事,这是极不正常的。
儒首接着说:“儒家当今的一切都是庙堂赐予的,凋亡之日一如燕国寿命一般,不远矣。”
“儒首今日所言,若是传于天下,儒道定灭于明朝。”
“人之将死,其言何究。不去论师生之谊,你也算得半个儒生,今日送你三戒,汝自好自为之。跪下,伸出掌心。”
儒首手中的戒尺轻轻排在唐念奴的肩头,让其情不自禁跪向墙上的仁字。
“念奴儿,今日之后,你与儒家再无瓜葛,与我亦无瓜葛。汝的道在西天,汝的命在脚下。切记,切记。痴儿,只望儒道灭顶灾祸到来时,庇护一二便可,吾这一生所学都是你的了。”
戒尺三打掌心,钻心的剧痛让唐念奴面色苍白,胸中闷热难耐,喘不出一丝气,在脑袋一片轰鸣中晕了过去。
燕历二十六年十月十日,土星贯日,当代儒道魁首于太庙中寿终正寝,天下儒生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师,燕国失去了文坛泰斗。
百万儒生齐下泪,这是儒家盛极而衰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