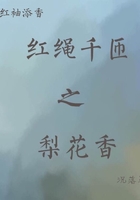二人绕着朱雀街走了一大圈,方才来到一座简陋的石屋前。青碧的石砖因磨蚀而隐隐泛灰,门前的石阶已然破碎开来,散落在地上,半布青苔,狼藉一片。石屋的木门斑斑驳驳,颜色深浅不一。
但走近了,却能感到大门处磅礴的灵力,大概是一层又一层的结界,为了护着里面那个昏迷不清的青年。
陆嗣挥手去了结界,推开门引着桑榆进去。
石屋的内里如外表一样简陋,那名重伤的青年此时躺在一张退了漆的木床上,但身下垫着的,身上盖着的确是上好的火绒织就的锦。
燚羽火绒,取开春火绒兽身上最细软的新毛,纺成最细的线,再织成最软的布料,是最坏绣娘眼睛的手艺。却因为出奇柔软而成为燚羽最珍惜的布料。
陆嗣高大的身躯往石屋中一站,石屋的空间便顿时更局促了一些。但他脸上毫无窘迫之色,只躬身引了桑榆到床边站定。他搬过一张椅子,又细致地用袖子拂了拂,请桑榆坐了。
“有劳公子。”
那躺着的男子脸上已有青灰之色,呼吸几不可闻。桑榆没有再等,冰极寒丝一闪便卷上了他的手腕,她静坐一旁,细细地探脉。
探脉的时间似是过得极慢,桑榆一脸淡然,静坐如老僧入定,反观陆嗣额上却见了细细密密的汗。
又过去一刻钟,桑榆收回了手,温声道:“要医治的话,要将他挪到晚晴楼。”
石屋过于简陋,若是手术,难免会增加感染的危险。
陆嗣一愣,半天才找回了自己的声音:“公子是说,真的能治?”
桑榆起身看向他:“我以为,在琳琅阁我便说清楚了,能治,只是有危险,我也不能确保说便能治愈,不过总要勉力一试的。”
陆嗣的眼睛忽地红了一下:“我以为……我以为……”
虽然他从未想过放弃,但希望越来越渺茫,身体疲惫之余,心中难免觉得一片死灰。而桑榆的一句话,却忽地在那片死灰之地埋入了一点星火,烫得他心口发疼,一时间完全不知道心下是什么情绪,只觉得百味杂陈。
“流光绯羽可还在?”桑榆见他神色恍惚,便开口问道。
陆嗣倏地回过神来,忙点头,手中便出现了一个水晶盒子,正是那日在琳琅阁拍卖的盒子,上头还带着醒目的千机锁。
桑榆的眸中闪过深思,储物戒、千机锁、流光飞羽均是珍稀之物,寻常人见都未见过,更遑论据为己有。而陆嗣就这般轻飘飘地拿了出来,他究竟是什么身份?
眼下也无法探明,只能先救治了陆风,将流光绯羽拿到手再说。
“走吧。”
桑榆往屋外踱步而去,陆嗣小心翼翼地用火绒将陆风的身体裹好,抱着他跟在桑榆的身后走出石屋,二人便往晚晴楼而去。
进了晚晴楼,桑榆便一路往寄桑居而去。
陆嗣越跟着走,心下就越是震撼。
“公子住在西楼?”
桑榆点点头,“要医治他,寄桑居的东西更齐全一些。”
陆嗣似懂非懂地眨眨眼,他自然不是问这个。
他想问的是,晚晴楼的西楼不是素来不对外开放的吗?为什么公子这么随意地就进来了?且一路走来,晚晴楼的管事经过都对公子毕恭毕敬的。
联系着先前沈烨的态度,陆嗣感到自己悟了。
眼前的小公子实在神秘,他来之前也多方打听过,并没有打探到什么像样的消息,如果他便是晚晴楼背后的主人,那一切就都说得通了。
少年深沉,而医术高深,一身清冷的气度逼人,怎么看都不像是寻常人。
他自然不会傻到开口去问,在世上行走,每个人总有自己不愿为人所知的秘密。他此刻有求于人,更要小心翼翼。
桑榆带着陆嗣进了寄桑居的客房,先将陆风安顿了。
“你先帮他沐浴,衣物都需要换掉,我吩咐人进来帮你,好了之后来喊我。”
陆嗣毕恭毕敬地听着她的吩咐,点头应是。
桑榆再进屋的时候,陆风已经被收拾得干干净净,睡在一张不太宽的软榻上。
陆嗣已经被请了出去。红衣先行搬了长桌放在软榻的边上,将桑榆惯用的工具用酒泡了,按顺序摆好,又端了热水放了几块干净的棉布,便安静立在一旁等候吩咐。
每到为人医治之时,桑榆看上去总是跟往常不太一样。她的眼眸亮如半夜的星辰,熠熠生辉。
她净了手,走向陆风,有条不紊地动作起来。
陆嗣一直候在前院里,不敢靠得太近。他知道医者在医治病人的时候,最忌讳打扰。但他也不敢离得太远,自桑榆关上了门,他的一颗心便七上八下,无论如何都安定不下来。
前院的阳光有些烈,他就这样傻乎乎地站在烈日里,皮肤被晒得黑红,满头大汗。
傍晚时分桑榆从屋里出来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这样的场景。
她不由失笑:“你若再站下去,兴许中了暑,还要我来医治。”
陆嗣此刻有些头昏脑胀,看着桑榆轻松的神色,心中一动,但依旧是放心不下,便扯着干哑的嗓子问道:“陆风如何了?”
桑榆神色淡淡:“不如何,眼下还算稳定,能否痊愈还要看接下来的治疗。”
陆嗣闻言眼眸亮了亮:“有救?”
桑榆闻言了看了他一眼:“自然。倒是你,积劳过重,肝火虚燥,再不去休息马上便要倒下了。”
陆嗣长舒一口气,心下一口气松了,脚步就有些不稳地晃了晃。
“旁边的客房便给你做休息用吧。”
语罢,桑榆带着红衣往主院而去,昨夜一夜未眠,今日又为着陆风的伤势忙活了一天,着实疲惫。
陆嗣看着两人的背影许久,方才咧嘴一笑,他先是去看了一下陆风,见他脉搏较之先前有力了许多,心下踏实,便真的去客房休息了。
所以,当燚羽皇的赏赐圣旨到晚晴楼的时候,沈烨只能请刚回来的千面去接旨。
等到千面晃晃悠悠到了前厅,才发现来送圣旨的人居然是喻墨。
喻墨见是他,笑容温和地道:“想不到还能当面跟阁主道谢,看来这个圣旨送得倒不冤。”
千面也是一笑:“二皇子想要见的恐怕不是本阁主吧。”
被戳穿的喻墨也不尴尬,大方地承认道:“来之前便也想到,她怕是不愿见我的,只是我却不能不来。”
见不见是她的选择,来不来却是他的诚意。
“主子确实不需要你们的感谢。”
喻墨对他的无礼也没有恼怒之色,他失笑道:“阁主还真是一点也不客气。”
他拿出一块红色的火焰形状的薄玉递给千面,说道:“这是火羽令,护国公主的令牌,宫中军中皆可行走,可以调动赤羽卫,见之如见父王。”
千面没有伸手去接,微微挑眉道:“殿下是觉得我身为属下,可以为我的主子做决定?”
喻墨摇摇头,他递出去的姿态坚决,一双修长的手衬得手中的玉荧荧如火。
“我只知道,这块令牌只是保护她的一种手段。她无须做什么,护国公主的名头也可以不必理会,只是多了支军队保护,何乐而不为?”
千面闻言眉目顿时冷了下来:“哦?无须做什么?殿下以为,雪氏一族的血并不算什么?”
喻墨自知失言:“抱歉,我并无此意。只是希望她收下这块令牌。”
千面冷嗤道:“让主子收下令牌,好给你们不安的良知找一个自我欺骗的借口?”
喻墨抿着唇,端肃地道:“是不是自我欺骗重要吗?只要这块令牌有朝一日能护住她半分,便是有意义的,不是吗?”
千面冷哼一声。
他就是看不惯燚羽皇室道貌岸然找借口的样子罢了,如今喻墨的话说到这个份上,倒是顺耳多了。
喻墨见他面色缓和了一些,便将火羽令放在一旁的桌案上。
“总归是我父王的一片心意,若是她实在不喜,毁了也无妨。”语罢头也不回扬长而去。
千面见他走得潇洒,撇撇嘴咕哝道:“还真是滑不溜手啊。”
他收起了火羽令,哼着不着调的小曲便往主院里去了。
陆风毕竟伤势过重,桑榆每日来给他施针治疗,一连十日才堪堪苏醒。
长久的昏迷让陆风有些恍惚,他睁开眼睛,好半晌才将眼神聚焦到陆嗣的脸上。
“大哥?”
这低哑又有些听不清的叫声却让陆嗣喜不自禁。他激动地欺身到床沿上,将脑袋凑近了,拍了拍陆风的脸:“小风,可能看得清大哥我?”
陆风被陆嗣突如其来的动作惊了一下,一时气没喘匀便急急咳了两下。惊得陆嗣几乎是弹了起来:“你怎么样,哪里不舒服?”
陆风被他奇怪的举动逗笑了:“大哥,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一惊一乍了?”
陆嗣不好意思地摸着后脑勺,抱怨道:“你小子差点吓死大哥,你可知你已经躺了两月有余了,我请了多少炼药师来给你治病,都说你没救了。若不是公子,你此刻怕是再也见不到大哥我了。快来谢谢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