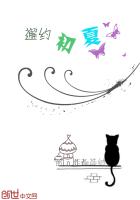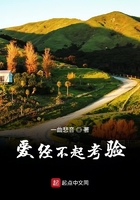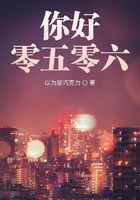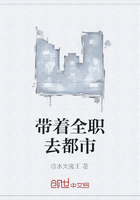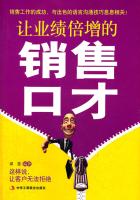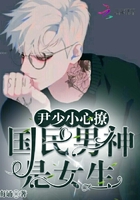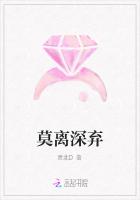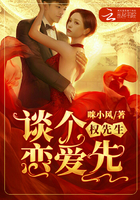老街“田家巷”深处有一家年头已久的新华书店,书店大门外面的牌匾上、黑色的油漆已经脱落,门前的石头台阶被过往的行人踏得光滑而圆润,泛着幽暗的光泽,仿佛告诉人们:它们已上了岁数。
这家书店外地人很难找到,因为它店面不大,藏书也不丰富,光顾的客人不是很多。但是因为喜欢这条叫“田家巷”的老街,我和赵敏每到周日,隔三差五地会从学校乘公交车来到这里,看看书、转转街,再随便吃点什么小吃,一待就是一整天。
书店里的几个营业员几乎都认识我和赵敏了,每次看见我们来热情地打着招呼,知道我们是穷学生后,明白有些“大部头”的书根本买不起,在我俩爱不释手地长时间翻看时,只是善意地提醒我们不要把书页弄褶皱,但从来不给我们脸色看。
在这条老街上,我们经常会遇见一些美院前来写生的学生们,他们中有画水粉的、有画油画的,有时看见画得好的同学,我们会忍不住驻足在画架前观看一会儿。有两个总是在一起写生的男生,装扮极富“艺术气息”,每次我和赵敏来“田家巷”溜达,几乎都能碰见他俩,时间一长已经脸熟了,再遇见彼此友善地笑笑,只是从来没有说过话。
这家不大的书店坐落在“田家巷”的中后部,被老街两旁林立的老屋藏的十分很隐蔽,没来过的人很不容易找到它,唯一的标识是在门口的不远处有棵高大的棕榈树,树下有个穿着皮围裙的修鞋老人;狭窄的老街两旁是些老门老户的住家,房子老墙的外围、下面的水泥都已经没有规格地脱落了,显得斑驳陆离,墙根长满了郁郁葱葱的青苔,从门前经过时,能闻到房屋散发出来的潮湿气味儿;有些居民把临街老屋改装成小杂货店和报亭、电话亭,兼卖些日用品针头线脑的小本生意人;有个穿着一身蓝底白花、头上戴着同样花色头巾的老阿姨正在窗前专心致志地织布,织布机发出有节奏的声响,显得老街更加地静谧;街道两旁的门前零星地摆放了一些自行车、花盆和各种杂物,有两个上了年纪的老婆婆瘪着嘴,坐在自家门前的竹椅上,手里还拿紧紧握住一只拐杖,好像随时要站起来的样子。她们眼睛里什么内容也没有,只是目光散淡地执着地看着过往的行人。
每次看到这些脸上布满皱纹、手如枯树皮的老人,赵敏就会拽紧我的胳膊,问我相同的话:“安雪,你怕死吗?”
我答:“我不怕死,我怕老。”
赵敏认同地点点头,说:“是呀,人老真可怕!想想有一天咱们也会变成这样,这也太吓人了吧!”
是啊!二十三岁在我心里就是一道年龄大关,它离我们已经不远了,难道我们就要步入即将老去的行列了吗?
低着头,我正在胡思乱想中,只听见赵敏低声说:“嘿,看前面,快看呀……”
我抬头往远处一看,看见韩武和施向华正迎面向我们走来,我想进到哪个小店回避已经来不及。
初六那天发生的事情,过后我只是简单地和赵敏描述了事情的经过,她很为我鸣不平,觉得他俩做事“太差劲”,后悔那天没有陪我一起去。
看我想躲,她不解地问:“你跑啥?你又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我有些紧张地说:“不是跑,我只是觉得太别扭了。”
韩武已经看见我和赵敏,目光游离地看了我一眼,感觉他走也不是停也不是,假装四处张望着什么。施向华还没有发现我们,手里拿着包吃的,边吃边和韩武兴致勃勃地说些什么。我们离得越来越近,施向华终于看见我们,故意亲昵地把手里的东西往韩武的嘴里塞,韩武尴尬地转过头,拒绝施向华送过来的食物。
施向华撒娇地说:“吃嘛,可好吃了!”说完像刚发现我和赵敏似的,一只手拽着韩武的胳膊,微笑着和我们打招呼:“你们也来逛街呀!”
我十分不自然地说:“是呀!”
赵敏目光灼灼地直视两人,什么话也没有说。韩武窘迫地冲我们点点头,逃也似地快步逃离“现场”。
这是从初六那天起,距我离开韩武家已过去整整四个月,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
有时想想,仅仅因为他的“介入”,就让我和施向华的关系跌入冰点,把我们小学五年和高中三年的友谊化为灰烬,我觉得挺不值得的。我很想找个机会和施向华好好聊聊,推心置腹地和她说:你完全不用这么紧张,我一点儿都没有打算和你“抢”韩武的意思。我们俩的关系这么僵,韩武心里会怎么想我们,他会认为我和你的同学情谊有多么不堪一击!
其实,我更想表达的含义是,我不想让韩武内心有沾沾自喜的优越感,好像自己有多么抢手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