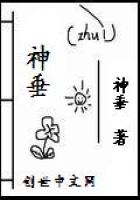我一直以为贺续文和周美芝一样,他俩都是在我们班“借读”两年后,提前回老家去了。虽然,当时因为贺续文的不辞而别我还有些小小的不开心,但想到他是如此的害羞和木讷,我也没再多“记恨”他,再说,他是没有和我们班任何一个人告别就走了。
当我几乎快要忘记他时,班里忽然传出一个小道消息,说:贺续文得精神病了!精神病?这怎么可能?!他能在两年的时间内,英语从只会二十六个字母到一跃成为班里的中上水平,精神病哪里会有这样的高智商!
在我记忆中,精神病患者应该是像大浩妈妈那样,整天只顾涂脂抹粉地打扮自己,不知道打理家务也从来不管孩子,天天在那毫无缘由地傻笑,有时走路还会旁若无人地自言自语。
当然,贺续文有时也会“自言自语”,可人家那里是在默读英语课文啊!
这是我们班第二次传“谣言”,记得第一次传“谣言”是在高二下半学期,有同学说我们这一届有个女同学从楼上掉下去了。有人说她是故意跳楼自杀;有人说她是擦玻璃不小心掉下去的;还有人说她是被家人从楼上推下去的。我们无从考究哪个版本是真实的,总而言之,她掉下来后没有摔死而是被送进了医院,后来有人说她下肢摔瘫痪了,要与轮椅终生为伴。
那么她为什么要跳楼自杀呢?有同学神秘地说,有一个搞“艺术”的人哄骗她拍裸照被人发现了,她深感无脸见人于是就跳楼了。
罗亚西和施向华向我描述了半天这名女同学的长相,还说有一次我们在路上碰到过,她当时还对我们说了什么话,她俩竭尽全力帮助我回忆,我也丝毫也回想不起来这名女同学的模样......
后来,有关贺续文的“谣言”也传的越来越有鼻子有眼的,说是他自己回家和父亲说:班里有位女同学看上他了,上课不仅老回头看他,还冲他摆手、冲他笑,上自习课时还专门扭过身来和他共用一个课桌......
他父亲觉得儿子有些不大对劲儿,专门跑到学校找慕容老师核实情况。
我心里有些暗暗吃惊,慕容老师嘱咐过我的关于罗亚西和贺续文的“秘密”,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一个人,包括罗亚西本人。有时,我为了不想让罗亚西再转过身来在我课桌上写作业时,真想告诉她班里因此而有人传她的闲话。可是想到慕容老师的再三叮嘱,说这是仅限于我和他两人之间的秘密,就忍住了。
答应过老师的话我一定要做到守口如瓶。
我没有外传的话,慕容老师更不会告诉其他同学,可是,同学们议论的这些内容分明就是老师当时找我核实的内容呀,是谁泄露了这个“秘密”的呢?
有关贺续文得“精神病”的事,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我冥冥中有一种不太好的感觉,心里面七上八下的很不安。我想问问慕容老师,又不敢;我观察观察罗亚西的神态,完全是一种毫不知情的样子,她还和原来一样没有任何的反常。
我下定决心,一定找班里的同学私下了解一下这个事情,我想到了男班长韩武。我和韩武不仅小学就是同学,又同是学生会的干部,平时接触自然比其他同学多了一些,心理上感觉他比其他同学要可靠。
周六下午放学,我喊住了正准备回家的韩武,拿着书包走到他的座位上,看看班里其他同学都逐渐走光了,才焦急地问他:“同学们传贺续文得病的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啊?”
韩武吃惊地看着我说:“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啊?全年级同学都传开了!你和罗亚西那么好,她没有告诉你吗?”
我着急地替罗亚西鸣不平道:“罗亚西告诉我什么?她自己还根本什么都不知道呢!”
韩武赶紧解释:“我不是这个意思,这事儿根本不怪人家罗亚西,我回家问过我爸,我爸说他这个病叫‘花痴’。”
“什么‘花痴’不‘花痴’的,”我又问:“你们是怎么知道这个事情的?”
韩武答:“六班有个同学和贺续文他爸是同事,他爸请假送贺续文回老家时和单位领导讲了,他们同事都知道这事,还号召大家给贺续文家捐款治病呢!”
我担心地问:“那贺续文是回老家看病了还是在这里?”
韩武摇摇头,说:“具体不太清楚,反正他休学了,高三是上不了了。”
我心里很不好受,贺续文这么刻苦读书,不就是为了明年的最后“一跳”,十一年的寒窗,是他们这些农村贫困家庭的孩子跳出“农门”的唯一出路啊!
我去过周美芝家,可以想象出来贺续文家的日子不会比周美芝家能好到哪里?平时和他说话我总是小心翼翼,生怕伤了他脆弱的自尊心,和我们这些城市孩子相比,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太不容易了!起码我们还从来没有面临过“饥饿”和“失学”的危机,我们平时里受的那些小委屈,在他们这里根本不足挂齿,和他们比起来我们的那些小痛小痒的又算得了什么呢?
施向华问我这个事情要不要告诉罗亚西,我说:“还是不要说了吧!贺续文已经这样了,再告诉她也没什么意义,省得她有什么心理负担。”
施向华担心地说:“现在全班同学几乎都知道这个事了,如果她是从别的同学、没有深浅的谈话中得知这个消息,这样对她才不好呢!我们是她的好朋友,应该婉转地先告诉她这个事情,省得她听到别人的议论时没有任何的思想准备。”
我觉得施向华的话十分有道理,于是决定这两天找个机会我们俩和她好好聊一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