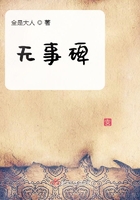此处是魏起军帐,魏起不愿随士卒军伍受苦,找了个借口在容城住下,这房军帐,每日有人打扫,实则空了许久。
鲜于辅以刘和为主,又敬重季先生,进入营帐以后,不敢于两人并立,在稍远处站住。
季先生只粗略看了一周,见营帐简陋,内部却是极大,暗道鲜于辅地方选的也不错,收回目光,自顾道:“世子,你我皆手无缚鸡之力,我知以往时候,想要做一些事儿,总会被身体缚住手足,你为天子伴读,一向养尊处优,即是要兴兵,不知世子心志如何。”
“家父之仇,不能释怀,若是不亲手刃公孙瓒,刘和枉为人子!”
季先生深以为许,点头示以赞同,道:“你为天子使臣,又有父仇,两相所选,甚合我心意。我且问你,吕布带走魏起两千骑兵,你心中如何做想?”
“先生!”刘和蹙眉,面有难色,见季先生只是笑而不语,只好坦然心思,道:“我虽不精兵事,也知道骑兵难以训练,所来容城,亦是为了魏起一部骑兵,如今想来,先生说的极对,魏起心有旁意,便是归附于我,也不会尽心尽力。”
听到刘和回应,季先生也不接过,又问道:“若是战时,遇敌你当如何自处?”
刘和想起前时刘策叮嘱之事,极为凝重,缓了缓心思,道:“我力不能战,一切皆听从随行将军所言,前几日,刘策曾与我约定,入容城时,我不能对他策议有指点,此时能安然与鲜于辅合并,全赖刘策一路照应,今后,刘和会学习战事,也不会自作主张,刘策鲜于辅尽是熟知兵士的将才,我会听从他们建议,不会在兵事上胡言乱语。”
“倘若被包围,不能力敌,你又如何?”
“刘和不会后退,与士卒共进退,同生死!”
“待到杀了公孙瓒,你可愿自领幽州刺史?”
“这.....季先生,我虽为天子伴读,本朝却从未有过子继父职的道理,若是幽州刺史,还需天子下令,我才能自领。”
“于士族寒门,刘公子又有何做想?”
“我不常行走大汉疆域,也知十三州,不论是治理,还是策令,尽要依赖世家才能推行,袁绍,公孙瓒,乃至朝堂官员,多是出自世家,先帝曾于我父亲说过,世家于大汉,虽可安民,却如人身上之疾癣,盛世时囤积财物,荒年时,又不吝民间疾苦,父亲因先帝诏,去往幽州,光施恩,减赋税,又安抚外族,才让百姓能活,于世家,父亲多有压制,未见成效时,就.....”
“唔!”季先生眯着眼睛,眉头紧锁,似有疑虑。
刘和见季先生一动不动,还以为说错了什么,犹豫着喊了一声:“先生….”
季先生扬手止住刘和,轻声道:“先不要说话,让我想一想。”
季先生转过身,再左右踱步,时而仰起头,时而伸出手指盘算,口中不知所谓的说着些话语,似乎对这件事极为看重,又似乎遇到了难以决断的当口。
刘和固然着急,看向鲜于辅,鲜于辅也是茫然,向刘和摇了摇头。
又过了十息的时间,季先生才转过身来,额头沁出细汗,气色看起来有些疲惫,只是目光却深沉如水,其中又有隐然的咄咄逼人之势。
“世子,先帝给你刘刺史诏书拔乱世家,可否与我一看。”
甫一出声,刘和听到季先生嗓音微有沙哑,与方才全然不同,询问有多有急促,不及细想,随即应道:“先生,诏书上未提及世家之事,这些策令,是先帝与父亲私话,我听父亲说起才知晓。”
“是我问的鲁莽了。”季先生先是摇了摇头,消瘦枯黄的脸上增添了一抹落寞,缓缓道:“原来如此,当日刘刺史于我以礼相待,与我探讨时政,还当是刘刺史性情如此,错过这番机缘,我还尚不自知。”
季先生唏嘘了一阵,再长长吐出一口浊气,直走到刘和身旁,似宽慰刘和,“我大抵已知世子心属,请恕季某直言,世子仁心,在如今时机,多有不适,若是要杀公孙瓒而后快,世子还需要多做些改变才好。”
听季先生说的郑重,刘和也绷直了身体,认真聆听。
“先生,此话怎讲…..”
“也不欺瞒世子,我所问的五个问题,世子所答,前四个,皆不合我心意。”
季先生说的直白,等若刘和所思所想,全盘被季先生否定,刘和脸上顿时红的有些发烫,还是咬紧牙关,恭声道:“先生是刘和长辈,刘和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先生只管提点就是。”
“我与你说这些,就是要给你讲旁的道理,既如此,就从方才我提的问题开始,告知我不苟同世子之处,世子可愿听我浅薄之论?”
“愿听先生高见。”
季先生身体孱弱,这时松了心神,才感到双腿有些酸涩,毫不客气的坐在一张椅子上,又指着身旁另一张,“世子,你来坐下,我们慢慢说起。”
刘和依言坐下,而鲜于辅却站在刘和身后,不愿入座。
季先生也无暇与鲜于辅客套,凝神想了片刻,把脑中想说言语略作斟酌。
“世子且听好了,吕布带走魏起两千骑兵,你自言骑兵珍贵,难以迅速成型,既是原本属于你的东西,不管是魏起,还是吕布,若有心成为雄主,手中之物,不分贵贱,又岂容旁人随意取走。”
“先生!魏起,他似乎也不想随同我,而且,那是魏起的骑兵,多半只听魏起一人号令。”
季先生轻哼了一声,语气也变得有些深然,道:“魏起不随同,杀了他便是!你起兵事,所求只是兵马,谁人敢挡你,便与公孙瓒同罪,既是如此,魏起杀了又何妨!统领之下,又有千骑长,百骑长,此类人是幽州官身,幽州以幽州牧为最,你以刘刺史名义,许以重赏,谁人敢有不服?若是不服,也可杀之!”
“先生,这......我......我记下了!”
“第二事,一军之主,不能自乱,属下之人,说的是在他立场所见,随行将军,也是一叶障目,他们作战建议,汇报你处,你自行定夺即可,统领之人,要决断所有大事,如此,于今后应做什么,如何去做,提前布下手段,才能了然于胸,战而不殆,尝云,意而不断,断而不决,此乃兵家大忌。”
“是!先生!刘和知晓了。”
“第三事,倘若你被敌包围,首先所思乃是保全性命,逃出生天,再回头计较,岂不问勾践卧薪尝胆,忍辱负重,终一举灭吴,连命都没有了,还谈什么复仇,与士卒同死,这等蠢事,又不是不死不休,世子怎能去做!”
“先生....这与家父教我,有所不同。”
“所以,你父亲刘虞,才会以十万大军,进攻公孙瓒,被公孙瓒一千军马所败,你可知,当日为了分散你父亲兵马,公孙瓒烧了多少房屋,毁了多少百姓,公孙瓒所做为人不耻,又祸害百姓,然而对一军来说,却是合格的统帅!刘和,若是你不能做到,趁早绝了复仇心思!”
“先生!我......我定然努力去做得!”
“第四事,如今天子被董卓余党李催、郭汜、张济、樊稠把持,哪还有什么天子诏令,不过是四贼假托天子名号而已,你是天家血脉,父亲又是幽州牧,先帝任你父为太尉,盘踞幽州,便是想朝堂不稳之时,能为外援,倘若你领幽州牧,当今天子,怕是欢喜还来不及,怎会怪罪与你。”
季先生之言,只如春雷绽响于夜,所见唯有一道光亮,恍若大吕黄钟,在刘和忠君事君的墨守成规馄饨处劈开一个崭新的天地,刘和陡然发现,原来这世间,还有如此模样。
或许,世间本来就该当如此模样。
刘和呆坐在椅子上,神情登时恍惚,忽而从座椅上站起,向季先生在揖三次,方才直起身。
“多谢先生,若不是先生今日教我,刘和至今仍不知天子苦难,事出何因。”
季先生望着刘和,似有顿悟,隐有笑意道:“哦?世子有所悟,也是好事,可否说与我听听?”
“元光年,司马相如为西南夷事,上书武帝,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今之大汉,十三州频有乱起,实在于兵权被外戚把持,公董卓袁术袁绍公孙瓒之属,手下都有私兵,我若是再循规蹈矩,怕是连大汉最后一丝希望,都要断绝在我手中。”
刘和眼神中透着一往无前的坚定,握住季先生手臂,继而道:“先生,杀了公孙瓒,我自领幽州牧,假以时日,积蓄力量,再自领辽东,青州,季先生,你要助我!”
“好!”
季先生站起身赞了一声,而后弯身双手揖道:“因怕牵连家人,以假名游历,取自季氏,君子三戒,少年戒色,中年戒斗,老年戒得。故名季戒,我本是颍川寒门,名戏忠,字志才,方才不知世子心志,有所隐瞒,若是世子不嫌弃,戏忠愿在世子麾下谋一个闲职。”
先前戏忠推拖要回颍川,连季戒假名都没告诉刘和,自是没打算在刘和处多呆,此时告知真名,又愿在刘和麾下任职,其实等若是真心投靠了刘和。
这让刘和如何不惊慌。
刘和扶起戏忠,欣喜的声音都有些发颤。
“季先生….哦,不,戏先生,快请起!能得戏先生相助,实是刘和之幸,是大汉之幸。”
一旁,鲜于辅简直有些瞠目结舌,戏忠说的什么雄主,为天子外援,鲜于辅听不太明白,只是,自领刺史郡牧,盘踞一地,这分明私自割据汉域,等若是自立为王!
这戏忠如此心思,几乎同于谋逆!
倘若刘和真的领了辽东,幽州,青州,这.....,这听起来好像也挺不错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