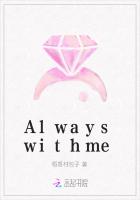燕国刚经历了一场变故,酒肆中本就没有多少人,加之李儒刻意腾挪,二楼中倒是颇为清净。
在座的这些人,都算是与刘策交情匪浅,又有协力破了燕国之围,眼下公孙瓒已死,先前为了掩人耳目做的弥彰,也无需再藏掖着,于是刘策将如何去涿郡,如何引诱公孙瓒,到交战徐荣事,与众人尽数说过。
虽然公孙瓒的死讯,让几人觉得惊愕,然则听了其中详尽关节,才发觉竟然有一波三折的跌宕起伏,除了戏忠不属武人,太史慈,张郃,阎柔,听过后心中未免有些异样感慨。
阎柔倏然站起身来,一脚踏在半边椅子上,面色有些红润,举着杯盏,大声道:“主将!我阎柔,这辈子就服你,哈哈!你杀公孙瓒杀的痛快,我与太史慈,还有这位张郃兄弟,杀邹丹也杀的很爽快!其它的话,我就不多说了,我来敬主将一杯!”
“阎柔说的对,仲业能在短短时日,将黑山张燕,公孙瓒一举平定,实则为幽州百姓,谋了安平之所,我太史慈平生所求,上敬于天,下敬于地,心中无愧,他日仲业若要再辽西纵横,太史慈定当随你同进退!”
太史慈亦是举起了杯盏,侧着身躯望着刘策,虽然不如阎柔那边形色于面,也能感知其胸中激昂。
再向张郃拱举,继而道:“我与俊义,虽是初次见面,那日,俊义在城中夹击邹丹,这等果决眼力,太史慈佩服。”
在刘策详述时,已与阎柔,太史慈喝过几杯,若是与太史慈不相熟之人,听到太史慈这番言语,只会觉得太史慈是直爽好友的汉子,可是刘策与太史慈极熟,于太史慈的态度中,却是感知到太史慈的莫名离意。
这等言辞,分明是在与刘策道别。
此时,不知为何,戏忠也抬起手,笑道:“燕国之围,全依赖诸位,戏某谢过诸位!来,戏某敬诸位一杯!”
几人端着杯盏,一饮而尽。
阎柔霍然坐下,眼瞅着窗外,再转过头,哼然道:“主将,我听说,燕国这里,有许多不开眼的东西,还想为邹丹内应,依我说,如今田畴不在,择日不如撞日,稍后我与主将去将这些东西,再杀过一回。”
刘策已从张郃口中,得知了当日燕国内部隐患,对于这些摇摆不定,始终以自己家族利益为上,又相互抱团传统的门户,刘策也有了怒意,倘若真的让他们得手,经营了半年之久的燕国,恐怕是另一番局面。
卧榻之处,自无容他人鼾睡的理由。
已经有些酒意入头,刘策转过身,向戏忠问道:“戏先生,以为如何?”
“嗯?”
戏忠沉吟道:“仲业先前说,少主不日就会归来,我觉得,这等事儿,还是要等少主回来,在做定论。如今公孙瓒已死,这些人怕是想左右摇摆,也再无可选余地。”
刘策心中有些抑郁,不过亦是没有驳回戏忠。
“这….如此也好!张将军,此次辛苦张将军了,刘策在此谢过张将军!”
这番饮席,不知什么时候结束,到了刘策清醒时,已是第二日的清晨。
走到屋外,举头的阳光有所刺眼。
刘策打过水来,尚未洗漱完,便听到身后院门打开。
平日进出刘策屋院的,多是麾下士卒,还有刘冲,小黑,刘策顺眼望过去,看到竟是戏忠快步的走来,刘策口中尚有含水,只做点了点头,打着手势让戏忠暂且稍等。
等到清洗了颜面,刘策着着小衣,看到戏忠便是坐在院中石椅上,眯着眼睛晒着日头,多有几分悠闲。
刘策执礼道:“戏先生!”
听闻刘策呼喊,戏忠睁开眼睛,没有与刘策寒暄,第一句便是沉声道:“刘策,刘仲业,以后,你万万不可再饮酒!”
“先生?这….”
直呼名姓,这俨然是长者对后辈的态度,不过,戏忠比刘策大了一旬,刘策也一直将戏忠视为长辈,对于戏忠持着严意语气,刘策一时间有些摸不清戏忠的来意了。
刘策试探问道:“先生,可是昨日我酒后做了什么错事儿?”
戏忠与刘策对望了片刻,目光始终坚定,其中又有别样意味,让刘策看的有些心虚,终而底下了头,此时听到戏忠缓缓说这。
“我一直与公孙瓒有来往,当日在容城时,我与你说,我北上是为了寻继命药物,其实我还有别的目的,我已见过公孙瓒,叮嘱他聚拢兵力,将幽州的战线拉长,与袁绍对峙,随后公孙瓒执意猛进,接连败退,最终才依着我给他说过的,占据了城池与颜良对峙!”
“之所以公孙瓒会去寻辽东公孙度,与公孙度联军,也是我与公孙瓒私信说起,这次公孙瓒倒没有顾忌脸面,再做什么荒诞儿戏事。”
“前几日,你去涿郡掩人耳目时候,我又派遣人送给公孙瓒一封书信,将燕国的兵力,还有你去涿郡的意图,尽数告知了公孙瓒,所以,公孙瓒才会悍然出兵!”
刘策心中秉动,早就抬起了头,只是戏忠目光依旧决然,分毫不与退让。
便是无需多问,刘策也从戏忠眼中,看到了戏忠给出了肯定答复。
此时,刘策原本还有些沉荡的脑中,早已清醒许多。
回记起往事,一幕幕,一朝朝,对应戏忠所说,那些不经意间的事情,相互印证,让刘策有种豁然明悟的欣意。
怪不得,戏忠会只身一人出现在容城,依着时辰来算,可不正是公孙瓒连连败退时候?
还有从容城离去时,戏忠对刘策说,要让刘策提防公孙瓒的援军,甚至极为肯定这援军是辽东的公孙度!
至于前些时候,刘策一只疑惑不解的,公孙瓒为什么会出兵燕国,这是刘策也不能十足确定的事情,可是刘策与戏忠说起时,戏忠竟是没有盘算公孙瓒不来的后续事,以戏忠的智谋,万事会有后备手段,怎会露出如此的破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