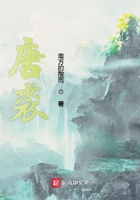岔道的尽头处是一个山脚下,洛水绕着青山而过。洛水旁停泊着一艘小渔船,一个身披蓑衣戴着青色斗笠的汉子临江垂钓。汉子旁边放着一个酒壶,一手拿着钓竿,一手拿着酒壶,仰天痛饮,何等惬意。
一阵风拂过,江中的草标有了动静,汉子连忙放下酒壶,猛地将钓竿一提,却是什么也没有。汉子不禁哑然失笑,高声唱道:“浪骤风急草标动,蓦然提起饵全无。鱼儿,鱼儿,你不要开我的玩笑。”
这是一幅充满诗情画意的景象,青山绿水,渔舟闲人,对酒高歌,垂钓日月。
南宫云绣抿嘴一笑,“鱼儿早被你的酒气给熏跑了。”
汉子一闻人声,立刻脱掉蓑衣,摘掉斗笠,扔下酒壶,竟然是令羽杰。他跳下船,奔前几步,朝南宫父女俩抱拳道:“郡王,郡主。”
南宫霸眼睛一亮,一掌拍在令羽杰肩膀上,哈哈大笑,“原来是令兄弟,许久不见,令兄弟还是这么洒脱。”
令羽杰眼睛一热,握住了南宫霸的手。两只手紧紧相握,一时热血澎湃,“郡王风采更不减当年。”
“令兄弟,你这个称呼我真不爱听。况且我早已被革除爵位,成了乡野草民,更是个通缉犯,论身份地位远不如你了。当年我满门罹难,若不是兄弟冒死报信,我和云儿岂能逃出洛城。当时我们不就结拜成兄弟了吗!怎么,时隔几年,兄弟就不认我这个大哥。”南宫霸向南宫云绣一招手,“过来云儿,拜见你令叔叔。”
南宫云绣也收起玩闹的样子,庄重地福了一福,“令叔叔。”
“不敢。”令羽杰连忙扶住南宫云绣,“云绣都长这么大了,大哥,时间真是如白驹过隙。当年小弟是受皇后娘娘和太子殿下所托,给大哥报信。太子殿下支走了后街的廷卫,才使大哥安然脱身。”
“兄弟对太子真乃忠心耿耿。你不用多说,我心中记得这份恩情,不然我也不会千里迢迢赶来赴太子的约会。”
“殿下在对面草庐中等候。”令羽杰一伸手,“大哥,请上船。”
渔船横渡洛水,对面也是一座青山,只是更荒僻而已。三人弃船登岸,令羽杰在前领路,转过一个山脚,只见一个精致的草庐隐于树木丛中,一条清澈的小溪蜿蜒而下,直流入洛水。
南宫业仍端坐在轮椅上,面前摆着一张小的方桌,方桌上有一个红泥小火炉,炉中燃着木炭,炉上是一个铜制的茶壶,空气中飘散着一股淡雅的茶香。
见到三人,南宫业面露微笑,招呼道:“郡王,郡主,请坐。这是此山中的云雾茶,用的是旁边的这条溪水。我不惯饮酒,只能以粗茶相待,千万别嫌怠慢。令侍卫,你也坐下同饮一杯。”
在东月国皇室中,南宫霸的辈分极高,他是南宫纯的堂叔,比南宫业高两辈。南宫霸也不行礼,大咧咧地一坐。
南宫业拿下茶壶,分别往三人杯中斟茶,解释道:“我对茶道还有几分研究,这茶火候正好,三位尝尝此茶如何。”
南宫云绣端起茶杯,只觉一丝清香从鼻尖直入肺腑,令人神清气爽。轻啜一口,齿颊生香,回味无穷,不禁赞赏道:“果是好茶。”
南宫霸面前的茶杯一动未动,他甚至看都没看一眼,南宫业不觉有几分尴尬,自嘲般地道:“郡王,我知道父皇以前对你……”
南宫霸忽然一摆手,“你放心,南宫纯是南宫纯,你是你,大丈夫恩怨分明,我绝不会混为一谈。说吧,你千里传信,究竟有什么事?”
南宫业不禁对南宫霸肃然起敬,正色道:“东月国如今风雨飘摇,父皇又不太理朝政,内忧外患,搞的民不聊生。田明涛独揽朝政,培植私党,野心昭然若揭。玉莞红娇宠后宫,穷奢极欲,善于蛊惑人心。我虽为太子,但除了朝中几个无权无势的老臣,势单力薄,无法与此二人抗衡。我希望郡王看在同根同宗的份上,协助我一二,铲除这朝中的毒瘤与祸水,还东月国一片清明世界。”
话说的冠冕堂皇,南宫霸心中却暗暗冷笑,这南宫业看似文雅,其实也是争权夺利之辈。他担心太子之位即将不保,准备先下手为强。自己虽离开东月国数年,但威信仍在,南宫业就想利用这点威信,帮他组成另一股很大的势力,与其他两人相抗衡。
这时令羽杰也在一旁附和道:“大哥,殿下求贤若渴,万望大哥成全。”
南宫霸轻叹一声:“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曾答应另外一个人,帮助他完成一件大事。目下并非自由之身,实在有负兄弟。”
南宫业神色一变,把求助的目光望向了令羽杰,他早已知道南宫霸和令羽杰有结拜之谊,这次特意孤身只带令羽杰一人前来,就是希望用这种兄弟情义打动南宫霸。令羽杰当然明白南宫业的意思,他对南宫霸一向敬佩,南宫霸既然有难言之隐,岂能强人所难!但南宫业之意又不得不遵,一时情义两难,只得劝告道:“大哥……”
“兄弟不用多说了。”南宫霸看到了令羽杰的痛苦,霍地站起来,朝南宫业微微抱拳,“太子相召,我父女不辞辛劳,不畏艰险,千里迢迢而来,看重的是信诺二字。现在我早已答应他人,我一生光明磊落,岂肯做背信之事!我有一言奉告太子,田明涛已发现我的踪迹,目下只怕已派出大批手下搜寻。为了太子的安全着想,还是尽早离开此地。”说着一拉南宫云绣,径直往江边走去。
令羽杰慌忙站起来,高声叫道:“大哥,我送你。”
走了一段路,南宫霸握住令羽杰的双手,轻声道:“兄弟在洛水之旁做个渔夫,是何等逍遥自在,何苦卷入这争权夺利之中。我观太子此人,虽谦恭有礼,但心机深沉,将来只怕也不是能同富贵之人。兄弟,你不用送了,我父女划船自去,那船我会毁去,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兄弟,多保重!”
“大哥,一路珍重。”令羽杰热泪盈眶,望着南宫霸的背影,竟有一种洛水萧萧之感。此一别,或许再无相见之日。他转回头,草庐中的南宫业面色苍白,可那双眼睛闪烁不定。
皇宫别院的一间寝室内,玉莞红神情落寞地坐在梳妆台前,对着铜镜顾影自怜。寝室内装饰豪华,白玉床,金凤帐,琉璃珠,配着一个正淡淡春愁的绝代佳人,真是一幅绝美的图画。
女人再美,也不过是那时令的鲜花,有多少时间供人赏心悦目。等到春尽秋来,繁花落幕,还不是什么也没留下。玉莞红不仅貌美,还是个很聪明的女人,她现在虽然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可时光终会流逝,到了人老珠黄的那一天,她也会像那些无数打入冷宫的妃嫔一样,所以权势比留住容貌更重要,她必须为自己的未来打算。
玉莞红像是忆起了什么,在梳妆台的抽屉里一阵翻找,里面有一个镂刻着精致花纹的铜匣。打开铜匣,珠光闪耀,全是些价值连城各式各样的宝珠。她却看都没看一眼,小心翼翼地拿着一支金钗,往匣口处轻轻一点,下面竟还有一个隔层。隔层内放着一块红绸丝,上面是一朵极为普通的珠花,是那平常女子常用的装饰品。
玉莞红用纤纤玉指捏着这朵珠花,娇面上忽然浮现出一种幸福的微笑。这朵珠花曾经是她唯一的精神寄托,是她少女时期孕育的一个绮丽美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