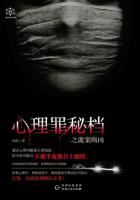唐黛回到帐篷里已经很久了,她晚上没吃东西,躺在榻上也一直都没睡着,裕王进来时她却装睡。
他脱了外衣钻进被子里,伸手将唐黛拖出来压在身下,他身上还带着未散的血腥味,却明显很亢奋,抵在唐黛双腿间的火热巨物仿佛在跳动一样。
唐黛却不想在这个时候应酬他,她微偏了头,拒绝他的吻。裕王爷欲/火烧得极旺,也不在意她的抗拒,就下手去剥她的衣服。二人拉扯时,何馨掀布帘进来。
她跪到榻上,自后揽了裕王的腰,娇声唤:“王爷,您又在使坏了。袋子今天累了,您就放她休息一会嘛。”
裕王终于松开身下的唐黛,回身抱了何馨压在床上:“那本王就先战你三百回合!”
杀戮让他兴奋,他连要了何馨两次,直到最后,身经百战的何馨都忍不住求饶了。唐黛滚在榻的一边,裹了被子装死。裕王云雨暂收后将她也抱了过来,再靠到怀里。夜里,他的声音格外清晰:“杀是你们让杀的,现在本王真杀了,你又不高兴了。”
他低头,唇在唐黛额际烫了一烫:“或许你觉得这样残忍,但是袋子,这是战争,如果输的是我和皇兄,我们的下场不会比这更好。是,穿越者是人,是命,难道大荥王朝的百姓就不是人,命就不是命了?”他以手轻触唐黛脸颊:“所以袋子,其实正义与邪恶只是人们主观赋予的光环罢了,从来都没有什么对和错,不管死去的,还是活下来的。所以,你不必介怀。”
“你明明可以给他们一条生路!”唐黛第一次如此直接地反驳他:“说着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你就无罪了么?如果不是大荥对穿越者的压迫,穿越者会起义吗?!他们会死吗?你们只是一群茹毛饮血的怪物,根本就没有人性。”
“啪”地一声,裕王在她头顶敲了个爆粟子,刚泄过火,他不易动怒,只懒洋洋地道:“这条律令没有定下来之前,穿越者就开始不停地起义了。那时候大荥连年用兵,内忧外患,先皇也是被迫立的这些规矩。”他自觉下手重了,摸摸唐黛的头:“你们总说古人如何如何,但是袋子,不管穿越者人数再多,掌握着再怎么先进的……科技,你们是叫科技吧?穿越者永远都不可能战胜大荥。知道为什么吗?”
唐黛不答,他索性自言自语:“因为你们永远都不可能热爱这个朝代,永远都不可能热爱大荥的每一个百姓、每一寸土地。无家无国,单凭一腔热血的军队,不能成事。你们总笑我们傻,动不动就尸横遍野,血流满地,可是唐黛,如果没有这些人的马革裹尸、沙场埋骨,会有现在的长安?会有现在的太平?如果让你们这些穿越者去这样牺牲,你们会肯吗?所以,我们不可能让穿越者动摇大荥政权,就算是杀尽所有穿越者,在所不惜。”
他拍拍唐黛:“好了,现在不管本王怎么解释,你也听不进去。但是唐黛,至始至终,本王不觉得这有什么错。只是立场不同,多说无用。睡吧。”
唐黛趴在他胸前,声音里带着疲惫的沉寂:“裕王爷,唐黛想求你一件事,请王爷成全。”
裕王揽着她腰的手紧了紧:“说吧。你求本王的事,本王几时拒绝过吗?”
唐黛叹气,半晌方道:“或许王爷您才是真正的高瞻远瞩吧,但是这些见解,唐黛永远不能苟同。唐黛见识粗陋、目光浅薄,只希望以后能够安安稳稳,以度余生。所以……所以秋猎之后,请王爷准许小民离开。”
山间的秋意真的甚浓了,风卷着落叶拂过帐篷,其声暗哑。
裕王拥着她的手僵了一僵,声音却分不出喜怒:“你想去哪?”
帐中灯火黯淡,他看不清她的表情,只觉得那语声带了一丝嘲讽:“王爷命我们亲手杀了黎桥,我们自然是不可能和太平天国再扯上半点关系了。若是已经不可能投敌,小民去哪里,又有什么关系?”
“你啊。”裕王抱了她,顺着她的长发:“有时候本王喜欢你够聪明,有时候本王又恨不得把你打傻喽。这时候你若出去,太平天国的人肯定会杀了你。”他轻笑:“若是你在围猎场倒戈,死在本王手上,多少也还算壮烈,这出去死在太平天国余孽手上,两面不是人,何苦来着。”
唐黛不想就这么被说服,这就跟辞职一样,往往很难开口,但是若是开了口没结果,下次又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若王爷当真替小民着想……小民想请王爷替小民指婚。”
裕王一怔,果然,这才是你的目的么……他声音依然无波无澜:“指婚……你想嫁给谁啊?”
唐黛不应,他便换了问题:“你和本王同榻已久,他不介意?”
“小民……小民没有问过他。”
“你问过他之后前来告诉本王。”
唐黛穷追不舍:“王爷您是答应了?”
裕王突然起身,开始穿衣:“你求本王的事,本王一直在答应,从不曾拒绝。”
他拂袖而去,并没有说他去哪里。这帐中的两个女子都曾与他颠鸾倒凤,但谁关心他去哪里?
榻上的何馨语带嘲讽:“你觉得他真的会放你离开?”
“我不知道。”唐黛仰躺在榻上:“可是这样的日子,我一天也过不下去了。成与不成,总是要试一试。”
“虽然我并不愿意你离开,但是我也希望他能够守信。”她侧身伸手拍拍唐黛的肩。
帐中骤然安静,外面传来兵士们低声的说笑,篝火燃出哔剥的声响,长夜犹漫。
秋猎结束之后,是十月中旬了。
唐黛回到浮云小筑时发现迟容初竟然还在,她有些不敢面对她。不管什么理由,杀夫亦是血海深仇。她挽着何馨的胳膊走过朱漆雕祥云、珍禽的走廊转阁,迟容初一直跟着。她脸上的脂粉打得极厚,遮去了眼角眉梢的痕迹,唐黛只能从她的目光看出内中的沉郁。
唐黛吩咐家人打水,迟容初也跟着忙去了。唐黛颇有些担心:“何馨,你说如果你是她,你会怎么对付亲手杀死你丈夫的人?”
何馨也在望着迟容初退下的方向出神:“如果我化悲痛为力量,那么也许现在我会跟着太平天国残余的势力转移,以待时机,东山再起。如果我儿女情长,失去他我活不下去,我会留下来,舍我残生,拼个鱼死网破。”
她回眸看唐黛,神色凝重:“她应该不会硬来,现在开始,小心饮食果品,一旦发现任何异常,叫你的暗卫救命吧。”
唐黛却没有心思管这些,她洗完澡便去找寒锋,一别十几天,她居然有些想他。这感觉很奇怪,她和裕王一睡三年,但他去哪她从来不想,和这寒锋真正相处并不久,心里却总是记挂着。
那时候寒锋在后园浇灌花草,闻声赶出来时唐黛坐在前厅相候。他也不顾下人在场,当下便拖了唐黛,一路进了书房。唐黛能感觉他握着自己左手的力度,她突然觉得安心了很多。
寒锋关了房门,突然返身紧紧地抱住了唐黛,唐黛身上有着沐浴之后留下来的浅浅花香,他在她颈间嗅了一阵,才放开手。良久他轻咳一声,掩饰自己刚才的唐突:“和谁一起出去,游玩了这么久?”
唐黛第一次进他的书房,这里完全不同于浮云小筑,随便一个玉人骑马的摆件便是从西汉时期流传下来的珍物。香樟木的书架保持着原木的颜色,偶尔的切面可以看见深色的年轮。完全不同于唐黛看完便丢的习惯,寒锋的每一本书都保存得极好。
大凡写手都有这么一个毛病——爱书。就算是其实根本就称不上文人,却也不妨碍他们对于文字的热爱。
唐黛信手抽了本,好死不死竟然是含珠的,此时看到这本书,她心中有些讶异:“我以为你就看些《菜根谭》之类呢。”
寒锋微笑着帮她把书放回去:“我们五个人出的每一本书,这书架上都有。”
他没有再说下去,五个人的书都还在,可惜五个人已经……
唐黛这才突然想起:“是了,瑞慈该是要出嫁了吧?”
“嗯,喜帖应该已经快到浮云小筑了。”寒锋再握了她的手,搓了搓拢进自己怀里:“袋子,我们呢?”
唐黛抬头看他,他的气息纯净甘冽、他的目光真挚而热烈,唐黛觉得接下来的话有些苦涩:“寒锋,如果……如果……”她咬牙,闭了眼睛把话一口气说完:“如果我在你之前,有过别的男人,你介意吗?”
书房里静默了一阵,唐黛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怎么期待。
如果你不是我唯一的男人,你还愿意做我最后的一个男人吗寒锋?我竟然忽略了,在你们的时代,视名节、门风重于生命,那些三贞九烈的牌坊分解出来,有多少是爱?
“袋子……”寒锋的手心在出汗,他的声音像钝器滑过砂纸,字字艰难:“我考虑一下好吗?我……或许我只是需要一个时间去接受……”他努力地寻找着措词。
唐黛微笑着抽回自己的手,他已经很努力的紧握,掌中却只余下指尖划过的隐痛。
“哈哈,寒锋,我只是开玩笑罢了。”唐黛努力笑着替自己解围:“你们本就是书香世家,真嫁你们家还不把我给沉塘了啊?”
她一步一步缓缓后退,笑容灿若春花:“我唐黛好不容易得空穿越这么一回,才不会这么轻易地去死呢。”她转身去开书房的门,寒锋自背后抱住她:“袋子,别这样,别这样,你让我想想,我只是太突然了,我一时……”
“嘘——”唐黛笑着挣脱他的双臂,她的神色带了一点俏皮:“不用再说了,我明白了寒大。”
她笑着迈出房门,寒锋哑声唤她,她回头,浅笑依旧,只是容颜如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