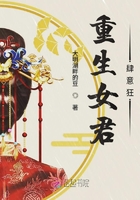他的身体一僵,顿住了,但并没有甩开我。
我小心翼翼把头轻轻的靠在他肩背上,说:“纪言泽,是不是,连你也不要我了?”
他的脊背笔直,他转过头,看着我,眼睛里是两簇明暗往返的幽深冥火:“你义无反顾从楼上跳下去,又不惜撕开自己尚未愈合的伤疤,你不是对我避如洪水猛兽恨不得我在你面前消失殆尽吗。何子颜,我是真正决定了一别两宽再不相见的,现在,你又自己横冲直撞闯过来。你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又把我当成什么?”
我抬起头,抓着他的衣角袖口,确认眼眶泛起的酸涩足够使自己泪眼朦胧:“纪言泽,全世界的人都百般不喜欢我挨着你。你妈妈,我妈妈。。。站在你身旁的未婚妻,更比我优秀闪耀一万倍。我确实不该再打扰你。可我真的好难受,头也痛心也痛,或者明天我就要难受得死掉了罢。我什么都没有了,全天下我是孤零零一个人,我什么都不想再顾虑,我只是想顺着自己的心意一次,就这么一次。如果让你觉得厌弃了,我现在就走,远远走开就是。”
松开他的衣角,我拿手抹着脸上的泪花,抽泣着缓缓转身离开。他长手一伸,已经紧紧抱住我:“这是你自己找回来的。你要走,前几天尚有机会,可现在,你又对我说出这样话语。。。你应该清楚,我再不会容忍你像以前那样荒唐胡闹。你要来,可以允许你,但不能随随便便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你懂不懂?”
我望着他。他的手环着我的腰,他的脸庞沐着窗落背驰进来的瑰色晨曦,褪去了平素的肃森冷峻,笼起的全是淡淡的柔软怜惜。不管为何,他对我,是尚存着三分情分的,我稍微放下心来,一抽一搭点头:“纪言泽,我一点也不喜欢伦敦。雾气蒙蒙,永远都是那样阴沉沉。不像新港,太阳像镶着金边一般明媚,连冬天都那么暖和。你带我吃的乌鱼子很好吃,你在潜海底时装大鲨鱼吓唬我,在阳明山上,你给我摘木槿花。。。不管去什么地方,我总是想,如果你在我身边,那就好了。纪言泽,我好想你,以后不管谁赶我走,只要你没开口,我都再不会离开了。。”
拉扯着记忆说起来,我突然一阵恍惚,其实他有阵子,对我实在也是极具耐心且温和的。只是他毕竟大少爷脾气,又那样喜怒不定难于揣测,或者说,我那时尚没有心思去揣测他,终究是免不了各自不痛快惹他发起脾气。
而他已经把我搂得越来越紧,他的肩膀在微微颤抖:“谁敢赶你走?子颜,你什么都不知道,我才是想你。你不会知道,我有多想你。。”他轻轻抚我散在肩上的头发:“伯母的事,你一定要想开一点。子颜,你受苦了,不要哭,以后会有我。我一直都在。”
我呜咽着,紧紧抱着他,如溺水的人抱住汪洋大海中唯一的浮木,心头终于坠下沉甸甸踏实的安全感。他拿起手,小心翼翼擦拭我脸上的泪珠,像是捧着最易碎的瑰宝琼玉,微而终于埋下头,从我的眼睛,轻轻滑落亲吻到我的嘴唇。长长的睫毛柔软的卷垂下来,溢出的全是温柔与怜惜。
真好,他对我尚有留恋或者可怜,不管如何,有就好,那怕只有三分,我也要用这三分,来翻起风云。他将是我的盔甲,我的倚靠,我的武器。
噌亮的落地玻璃窗外,楼下的工人帮佣来来往往在准备鲜花流灯金盏银匙,我想起纪言恺说的,晚上将有舞会。
在树林里,刚刚死了一个人,而这家人,若无其事在准备晚上的宴会。
凭我有限的欧美法系常识,不足以了解他们将会上几次堂,疏通几个人。想来纪言恺也不会在乎:没有什么事是纪家要做尚做不到的,杀个人又何妨,他罩得住。自然有人为他奔走出入法庭,他还是逍遥自在地做他的政客富贾,谋他的权势赚他的钱财。他不会亏待琼斯,不会亏待任何为他做事的人。
这就是纪家人。我将要交手为敌的,纪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