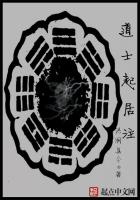公子请留步(朵岚)
韩颠国位于西蜀之地,民风淳朴,乡景富饶,百姓安居,皇室崇尚德政,历朝历代都以文治国为方针,外交和睦,与边陲邻国的关系也向来安好。
然,德宗皇帝十三年冬季,一向太平的韩颠国出了一件大事儿。
德宗皇帝六十华诞,宫里大摆宴席宴请宾客,宫中五品以上官员全部进宫为德宗皇帝贺寿。席间,德宗皇帝最为宠幸的妃子梁妃突然暴病,腹痛如刀绞,德宗大惊,百官慌乱,太监急急传来太医普连为梁妃诊治。
“回皇上,梁妃乃是喜脉,待臣开两付安胎的补药给梁妃娘娘食用以养身子。”普连放下梁妃的手退到一旁,开方子。
“爱妃!爱妃!朕有龙子了。”德宗皇帝欣喜若狂。
“皇上!臣妾终于有了皇上的骨肉了。”梁妃听闻自己有了喜脉不禁热泪盈眶,幻想着母凭子贵早日扶为正宫娘娘。
“皇上,安胎药已经开好了,请许公公开药吧!”普连开好安胎药将药单交予皇上审视。
德宗皇帝草草看了一眼后交给身后的太监许公公,吩咐其开药。
德宗皇帝是十三年冬,梁妃有孕的三个月满,葵水破裂,小产而死,德宗大怒,朝中太医全部受到牵连,只因后来查出梁妃服用的安胎要里面竟然有藏红花——-堕胎药的成分。同年十一月,梁妃大殡之后,德宗问罪太医院,十三个太医除了当时在祁阳王府为王妃治病的太医李谦外,其余一律发配边疆,世代不得为医。
第一章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公元722年,德宗皇帝去世,其二子井研继位,号天元。
天元8年,韩颠适逢百年罕见的大雨,大雨连续下了十余天,整个韩颠国土之内无一处幸免
放眼望去,到处是一片狼藉。
天元十一年,井研帝花费四年时间从整国力,拨银修建了韩颠历史上最大的一条人工疏导
道景天河,整条河道贯穿全国各各郡县,最终汇******。
天元十一年夏天,景天河道下游的北陵郡突遭瘟疫,痢疾横行,整个韩颠陷入前所未有的恐慌之中,北陵附近的郡县严禁门户城池,严禁人口疏散,北陵被完全隔离。
井研帝坐卧濮阳城里忧心国事,朝下臣子却无人能想出控制瘟疫的办法,朝中太医有半数被派往北陵,可惜,数月过去,北陵的瘟疫依旧无法控制,派出的太医如同肉包子打狗般一去不回。
“桂枝一钱芍药二分生姜三钱大枣12颗甘草一钱熬一次两餐之间喝一日三次。”濮阳城里的一家医馆前围了一群人,人群之中摆着一张桌子一张椅子,椅子上好端端的端坐一人,此人眉清目秀,气宇轩昂,倒是有一般人所没有的飘逸之姿。
“你去医馆取药吧!”温润的嗓音从他口里倾泄出来,感情是医者看诊呢!只是,为何要围有如此多的人呢?好似全城的医馆都倒闭了一样,所有人都挤到了这个小小的摊位前。
然,放眼望去,整条街上的医馆不知凡几,却都是门可罗雀,真是叫人猜想不通。
“下一位。”男子温润的嗓音再起,后面的人向前走了两步,伸出手腕递到他面前。
男子微微一笑,伸出修长的手指为他把脉,“这位大哥,你得的是痢疾,没什么大碍,回家多吃几颗大蒜就好了。”
“好好!谢谢蒲芹大夫。”男子道了谢匆匆走出人群。
“蒲芹大夫你为我看看。”
“蒲芹大夫你为我看看。”
人声鼎沸,拥挤的人群争先恐后的要蒲芹把脉,一时间平日里冷清的大街上热闹非凡。
“蒲芹,你这里可真是热闹呀!”人潮散去,天色已暗,蒲芹身后的医馆里大步懒散的走出一人。
蒲芹回头瞧了来人一眼,转而开始收拾桌子上的诊包和散落的几根银针。
“你的医术这样神通,何不效力国家呢?去某个太医院的官职也是不错的。”公孙雨玩笑道,绕到蒲芹的身前帮他扛起地上的桌子,另一只手拎着椅子往医馆里走。
“我志不在此,能医天下人,造福万民百姓足矣,皇室之人事不敢苟同。”蒲芹轻轻摇头,跟在公孙雨后面进了医馆。
“那你就甘心蹲在我这小小的医馆?”寻了一处空地,公孙雨放下桌椅。
“有何不可呢?”蒲芹笑道:“你不也是身怀绝艺,才高八斗的才子么?怎么不去考取个功名,绕或是承袭伯父的衣钵去当个万人敬仰的大将军呢?何苦窝在这个地方开个小小的医馆呢。”
公孙雨愕然,随即哈哈大笑,一把搂过蒲芹的肩膀状似亲昵的道:“呵呵!知我者蒲芹也,也罢,既然你我都无志于功名,那么就这么一生碌碌无为也未尝不是好事儿。”
蒲芹挑眉拨开公孙雨打在肩上的大手,转身面对他,“公孙,三日后我便要离开濮阳城了。”
“离开濮阳城么?你要到何处去呀!是不是嫌弃我给你的工钱少呀,你大可说嘛,我给你长就是了。”公孙雨道,大手却不知羞耻的再次爬向蒲芹的肩膀。
“误会了,如今北陵郡瘟疫横行,朝中无法可想,我要去北陵瞧一瞧,或许可以找到控制瘟疫的办法。”
“你不要命了么?朝中的太医去了多少,全都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的,你要逞什么能呢?”公孙雨气得不轻,目光凶恶的看着一脸淡然的蒲芹。
这家伙,永远一幅天下大任为己任的良善鬼脸,当真忘了自家老头是怎么死的么?什么样的浑水都要趟一趟。
“正因为如此我才要去的,行医者的本职便是救人与病苦之中,我当仁不让。”蒲芹一脸的坚决。
“蒲芹,你在这里行医不是一样救人与病苦么?”公孙雨咆哮,俊逸的脸气得扭曲一团,恨不得撬开蒲芹的脑袋看看里面到底装着啥东西?
“不一样的,北陵的百姓更需要我。”
“不一样?哪里不一样?”
“公孙,我去意已决,你就不要横加阻拦了,三日后我定要启程的。”蒲芹轻叹一声,转身出了医馆。
“喂!你等等,等等。”公孙雨急急的追出医馆,可哪里见得蒲芹的身影呀!
“妈的!你就是要去送死么?好吧!老子也不拦你了,死翘翘也活该,我是不会给你收尸的。”公孙雨朝着空空无人的大街上咆哮,大手一挥,身边的巨大石狮子被打得粉碎。
北陵郡。
紧闭的城门阻隔了去路,回首,那个曾经生长十八年的家已经如破败的扁舟被世人弃之不理。
“龚子琪,你还有什么可瞧的?还不快点上车。”刺耳的女声入耳,龚子琪回首,二姐已然坐在自家的马车上朝她招手,身后是二姐夫、大姐、大姐夫以及爹爹和两个姨娘。
“子琪,你发什么呆,要是让人看到我们爹爹带着全家弃城而逃可是杀头的大事儿呀!”大姐也是不耐烦的喊道,爹爹更是一脸铁青的看着龚子琪。
“我!”我想留下来,吐到嘴边的话却是没有勇气说出来,龚子琪缓缓的朝着马车的方向走去。
风吹过,卷起黄土地上的沙尘,不知是迷了眼睛还是怎样,眼泪顺着颊边刷刷落下。
北陵的百姓,街角的大叔大婶,龚子琪当真是寸步难行,再回首,紧闭的城门边是无数堆砌的死尸,那些城里得瘟疫而死的百姓死后连一块净土都没有,爹爹可还记得这些呢?一个郡县的官员竟然在百姓最困难的时候携带家眷逃走,可笑呀!可笑呀!
眼前浮现出大火熊熊燃烧的一幕,身着兵服的男人们将一具具腐烂的尸体抬到城外,然后在某个人的一声令下燃起漫天的大火,瞬时间,腐败的恶臭气体弥漫整个北陵。哭喊声不断,地狱的牛鬼蛇神怕是也要为之动容吧!只是,为何不见有神人来帮助这芸芸众生呢?当真要看着百姓生灵涂炭么?
“子琪,你快点呀!”二姐的声音再次传来,龚子琪抬头,却觉得车上的人怎生如此的陌生呢?那个爱民如子的爹爹的脸怎生如此的扭曲呢?
脚下的步伐再也无法迈出,泪眼婆娑的看着远处的马车。
“爹爹!女儿不走了,女儿留下,与这北陵成一起陨灭吧!”说罢,龚子琪转身朝着来时的路狂奔,将马车远远的抛在身后。
“子琪!”
“子琪!”
“子琪你回来呀!”众人见一向老实不善言辞的子琪竟然跑回了北陵皆不由一愣,随即有志一同的看向身后的老爷,谁也没有做声。
是追还是弃?谁都知道,若是此时回去不仅无法再出来,恐怕连性命也不保了。
众人各怀心事的看着老爷,等着一个能给大家活路的决定。
“不用追了,随她去吧!”老爷子一声令下,马车滚滚向前,身后的黄沙尘埃就留给能人吧!
高高的城门上挂着木制的牌匾,门洞两边是无数的散发着恶臭的尸体,有的已经开始腐烂,有驱虫在上面蠕动。
“这便是北陵么?”抬头望着仅仅合着的破败城门,蒲芹微微挑起眉头,紧走两步来到城门下。
“你是何人?”沙哑的声音从脚边传来,蒲芹微微惊吓的退后一步,低头循着声音的来源一看。城门左下角坐着一个人,由于光线太暗,蒲芹没有看清此人的面目,听声音倒是一个女子。
“你也是城里的人么?”蒲芹缓缓的走进,弯身蹲在那人的身前。
“嗯!我是北陵的人。”龚子琪抬起头看着昏暗中靠过来的头颅,鼻端传来一阵淡淡的药草香气,“你是大夫么?”
蒲芹微微一愣,而后想到自己身后背着的一箩筐药草便笑了,“是,我是濮阳城里来的大夫,来北陵治瘟疫的。”
看不清彼此的脸,两双茫然的眸子在黑暗中交会。
“是宫里的太医么?”龚子琪又问。
“不是,城里的大夫。”蒲芹答道,伸出手探向她的手臂。
“你干嘛?”龚子琪不悦的躲开他的手,一脸愤然的瞪着他。
“你莫要生气,我是想瞧瞧你是否已经染上瘟疫。”蒲芹诚恳的道,想来这人被关在城外也是因为染上了瘟疫,所以他想要先瞧瞧,即使无法根治也定要寻出一个保命的方子。
“我没有染病,只是正好出行,回来时天色以晚,城门紧闭,要等到明日早晨方可进城。”龚子琪道,抬手指了指满天的星子,此时,怕是爹爹他们已经到了其他的郡县了吧!也罢,她生来便不是个受人喜爱的女子,长相其貌不扬,又力大如牛,莫不是让人当怪物看待,只有死去的娘亲是真的爱惜她的。
“是么?”蒲芹像似不信般的站起身子来到城门边抬手用力推动城门,果然,紧闭的城门纹丝不动。
“我问你,你的医术如何?”龚子琪道,伸手拉了拉他的袍子。
蒲芹顺势又蹲到龚子琪的身前,“医术平平。”
“哦!那先生便不用进去了,回去吧!”
“为何呢?”蒲芹轻笑,顺势席地而坐,凑到她跟前。
“你自觉和皇宫里的太医有可比之处么?”龚子琪微微的挪动了一下身子,避开他的欺进。
蒲芹摇头。
“我说,宫里从瘟疫之始便派遣数名太医,可是没有一个可以控制瘟疫的,倒是有几个已经染上瘟疫死了。”说着,龚子琪抬手指着城门遍上的尸堆道:“瞧见没,就是在这里被大火烧掉了,死了死了当真是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连尸体都没有留下,与这漫天漫地的黄土做伴了。”
本意是要吓走这个声称医术平平的大夫,没想到蒲芹却轻笑道:“跟宫里的太医无法比,倒是民间的疾病却不见得是宫里的太医能全部了解的,在下自认走过很多地方,怀揣着救人的心态来这北陵,如今怎能还没进城就反身离去呢?”
“先生若是本着救人的心态,那我便不在劝阻先生,明日你我一同进城吧!”龚子琪无奈的道。
“好哇!你我一同进城也算有个照应。”蒲芹愉快的答,抬手将身后背着的药篓子卸下来摆在脚边。
淡淡的药草气息传来,龚子琪狐疑的瞧着蒲芹的药篓子,“里面可有见愁、手参、毛鸡、毛茛、毛姜、升麻、升登 丹砂、丹皮、丹参、乌茜、乌韭、乌药、乌头、乌桕、乌梅、方海、六曲、文元、文蛤、仁杞 双花、双皮、水花、水萍、水韭、水莽、水蛭、巴豆、玉桂。”
龚子琪一口气说出十几种药材,一旁的蒲芹如同被雷劈中般的愕然,没想到单单凭借着一些药草的香气这女子就能辨别出里面的药材,莫不是也是个大夫么?
“你也是大夫么?”蒲芹惊喜的问,大有他乡遇故知的欣喜之感。
“不是。”
“那为何……”
蒲芹的话还没有说完便被龚子琪打断,凉凉的道:“这些个药材不仅仅是我,北陵城里的每个活人都能闻出来。”
蒲芹愣了,不知道要说点什么?
“宫里来的太医每天给城里百姓调理的药都是这些东西,每天闻,每天喝,想不记住也难。”
蒲芹羞愧的红了脸,好在光线昏暗对方什么也看不见。
“对了,先生大名呢?”龚子琪瞧蒲芹不说话便问道。
“蒲芹。”
“蒲芹么?”龚子琪噗噗笑出声来,“你爹肯定也是一个大夫,不然怎么给你起了一个药材的名字呢?”
“不!我爹不是大夫。”蒲芹突然反映强烈的抓起龚子琪的手朝她吼去,好像她说了什么大逆不道的话一样。
“喂!你怎么了?不是就不是,你激动什么?”龚子琪一把挥开他的手。
“诶呦!”蒲芹虽不及防的被推翻在地,一脸惊愕的看着黑暗中的人影。
“你,你怎么?”这女人好大的力气呀!只是那么轻轻的一挥自己便摔倒在地。
“怎么?力气大不行么?谁叫你先抓我手的。”龚子琪羞怒的吼道,她也不愿生出这样大的力气呀!一个女子有如牛的力气,倒是有哪个男人敢娶她呢?
“我没有说你力气大不行,只是!”
“只是什么?”龚子琪栖身向前,伸出拳头在他鼻端晃晃。
蒲芹感觉到鼻端的威胁,心念一转,吐到嘴边责斥的话硬生生咽了回去,识趣的抱着药篓子退到离龚子琪稍微远一点的距离。
一阵冷风袭来,蒲芹微微打了个冷战。
“呐!给你!”一件披风从天而降正好落在蒲芹的头顶。
“什么?”蒲芹手忙脚乱的抓下头上的东西,拿到面前仔细一看,原来是一件披风。
“穿上吧!外地人来北陵都不适应本地的极大的昼夜温差。”龚子琪凉凉的道,身子更往城门角窝去,整个人缩成一个球。
蒲芹抱着带有她身上暖暖温度的披风,心口无意间划过一抹暖流,淡淡的,却足以慰籍心灵某处的缺口。
寒风冷冽的吹着,破空而入,闯进城门洞拍打着城门沙沙作响。
耳边响起平稳的呼吸声,浅浅的伴着细微的鼾声。
“姑娘,你睡了么?”蒲芹轻轻的问,小心翼翼的靠近龚子琪。
没有回应,除了风吹城门的沙沙声就是他的回音。缓缓的摸索到龚子琪近前,蒲芹抖开手里的披风将两人罩在一起,然后伸手抱住她卷缩在一起的身子。
她的脊背靠着他的胸膛,蒲芹可以清晰的感觉到她浅浅的呼吸和心跳声。
“龚子琪。”呐呐如蚊声,本该熟睡的人儿却是异常的清醒。
“啊!”蒲芹微愣,没想到她根本没有睡熟,俊脸一阵潮红,揽在她肩上的手不知所措的僵硬着。
“我叫龚子琪。”龚子琪又道,声音依旧很小。
“对不起!”蒲芹知晓自己这样的行径必然会坏了一个姑娘的清白,可是冷风刺骨,两人都心知肚明,若是没有这披风避寒,两个人谁也不会活着看到天明的太阳。
龚子琪不语,身子却僵硬的紧绷着靠在他怀里。
他们,一个是要救百姓与苦病的大夫,一个是要替爹爹赎罪的女子,他们当真谁也死不得。
天上的星子默默的看着,相依的两个人谁也不语,就那么静静的靠在城门脚一直坐到天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