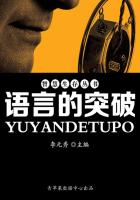玻璃洋葱/文
八年还是十年以前,江浙通往闽南的铁路被洪水淹没,我和两个同学坐着长途车去厦门。那时我们都没见过什么世 面,看到厦门市区路边种着成排硕果累累的芒果树也会原叫个不停。那个季节炎热、干燥、多风。不知从哪里听来的传闻, 从鼓浪屿搭晚上十点以后的船回市区就可以免船费,于是我们在港仔后看完日落便抱着“逛死街头”的决心在岛上夜游。 窄路上下起伏,天上有星,路旁有花。老旧的殖民建筑墙体青灰,黑影幢幢,废弃的门廊,毁损的木窗,如怪兽张开巨口, 伺机在黑夜中吞噬猎物。夏夜还有萤火虫,疏疏落落点亮鸡山路上横七竖八的石碑,再细看,不是石碑,分明是一大片 番仔墓。不怕死的开始讲鬼故事,胆小的便跑起来,一行人追逐而去,迷路时遥遥望见暗夜里那座西班牙哥特式教堂雪 白的单沖楼,简直有种神祇的意味。这是第一次为这些房子着迷,敬畏又倾倒。
四年后,又去厦门,那个季节阴冷、潮湿、多雨。BRT (Bus Rapid Transit,快速公交系统)通车,去集美只要40分沖, 却没有兴趣再故地重游。鼓浪屿开始到处出现“鱼丸” “馅饼” “海蛎煎”,家家户户看起来都差不多,吃起来也没两样。 那些怪兽般的房子似乎一大半都被驯服,墙体典型的青灰色被更符合潮流的油漆覆盖,变成小资的旅馆、西化的咖啡店、 婚纱摄影的外景地。时髦青年坐在庭院里无懈可击的遮阳伞下,用刀叉吃着意大利面,人手一份鼓浪屿手绘地图,消费 一种叫做“文艺”的情调。
我随身携带一台28毫米的傻瓜相机,凭本能拍下一些建筑的样子,试图恢复四年前它们在我记忆里的样子,后来发 现基本是一种徒劳的行为。本地的医院与学校为了旅游业发展已迁至岛外,鹿礁路的博爱医院变成一座空壳,鼓新路和 内厝澳的大部分旧宅都被早就生锈的铁锁锁上,在高墙外窥看,只能看到一地落叶,青苔蔓延在花岗岩废墟上。黄昏时, 我像我讨厌的游客一样,于码头迅速撤离,手里拎着多盒馅饼和肉干的特产。
第二天,我搬去了华侨新村。
阴雨时期的公园西路和斗西路,洋紫荊被雨一打漫天撒落,帽衫一抖嘭一声飞出一兜花瓣。
相对于民国时期的鼓浪屿豪宅别墅,这些建于20世纪60年代,供华侨居住的房屋更为低调实用。没有古希腊廊柱, 7K泥透雕,云墙假山,多的是清水红砖外墙与坡面屋顶。住了二楼的小屋子,大比例的木框窗,推开窗,迎面是一棵巨 大的龙眼树。下雨无法外出就在客厅看书,被楼面铺设的地砖吸引,仅仅是简单的几何图案的重组和拼凑,却可以变化 出这样繁复惊艳的造型。以为是旅店的特色装饰,打听后才知道这些被称做水泥花砖的地砖是当年驰名南洋各地的“南 洲花砖厂”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专为厦门、漳州两地的华侨新村建设生产,总产量只有435万块。而如今,这种梦幻般的地砖因为工艺复杂,加之大量步骤需要手工操作,已经绝迹于国内市场。
傍晚,在中山公园散步。肥嘟嘟的小孩端庄地坐在动物形状的电动车里痴笑,榕树下的老人喝荼聊天拉胡琴,琴声 在雨天纷纷扬扬,总有欲说还休的况味。也许只要这些人还在,厦门的本来面目就不至于彻底失去。穿过这座公园是老 城区百家村,我想看看那年看过的漆线雕,邻居说因为城区改造,工匠搬走已经很久。幸运的是,记忆深处一扇木质的 鹦哥绿百叶窗还未被毁去,虽然,那幢老楼也已经搬空,大厦将倾,不忍卒读。
不知为什么,非常想在无人的海边放天灯,潜意识又预感城市整修的下一步迟早会轮到曾厝垵,于是在去年,在背 囊里装了十个天灯,住到这个曾经几无游人的海边小村。
村口的大榕树和戏台还在,福海宫也在,保生大帝和妈祖似乎总是用那种以不变应万变的眼神面对这些年的一切。 这里闽南建筑的典型番仔楼已经很难分辨出原来的建筑结构。短短几年,由于此处到海边的直线距离之短,建筑大部分 被翻新重建,为全面开发为海滨度假村落作准备。半真半假的pizza屋,糖精和奶粉勾兑出的奶荼,铺天盖地的烧烤铺…… 任何海滨游乐场所似乎总由这些拙劣的元素组成,最重要的——人和自然间亲密无间的距离,却被认为并没有那么重要。 曾厝垵和大海只隔着一条马路,五分沖的步行距离,越过那些闪烁俗气霓虹灯光的海鲜酒楼和星级宾馆,是夜晚九点的 无人栈道。走下去,鞋子里开始渗进沙子。远处是一对形迹可疑的情侣,不去管他们,从包里拿出白色绉纸的灯,组装、 点火,只消等待燃料充分燃烧就可以松手。海风很大,朋友不断喊着:“我放手咯! ” “我真的放了噢! ”纸灯脆弱,但 竟然出乎意料顺利地乘风而去,沿着海面纵深的方向越飘越远,越升越高,我们屏息看着温润却有力的灯火在靛蓝色的海面拖出一条闪电般的橘黄色倒影,直到一切消失在天际。若干年后,这里不知又会开出几家酒楼几处旅馆,从马路直 接走到大海也许只能变成地方志中的一种描述。
最后一天,又回到鼓浪屿。不死心地去了笔山公园,天知道为什么我那么喜欢这个不合时宜的地方,也许只是因为 这里还能隐约看到一些童年的形状和色彩。果然,已经拆得面目全非。这个曾经的儿童乐园废弃多年,像一个落魄的隐 者一样藏身于巨大的榕树和竹林中,沉重的木质积木上“大坏蛋”的字样仍未退色,熊猫脸的跷跷扳还能玩上一阵,大 象滑梯却已经摇摇欲坠。走进那个不知能骗几岁小孩的迷宫,里面很臭,迷宫的中心有一团狗屎。它和很多古老的东西 一样,一旦不被时代需要,就面临彻底被销毁的境地。现代社会讲的是效益,是投入和产出的量化,是同无用的“回忆” 与“美好” 一刀两断的决绝心。
回来的路上看到报纸说厦门最老的市集“八市”已经被拆除。曾经,那里是每次去厦门必定造访的地方,为了充满 市井美学的古老物什,为了大批光怪陆离的深海鱼类,为了道路两旁古朴典雅的闽南骑楼,为了偶然路过竹树礼拜堂还 能听到牧师布道……坚持传统通常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但每次面对传统与发展的选择时,人类却倾向于权衡他们能从 中臝得什么,而不去思考他们将失去什么。每一年,城市与城市都在变得越来越像,所谓的特点不过是为了迎合游客而 臆造的场景,最终,世界大同,我们只是在一个戏仿彼此,或者说戏仿同一拙劣标准的巨大迷宫中生活。歧途之后,无 限接近迷宫中心,却发现不过是那么一团不尽如人意的狗屎——城市化的骗局,令人窒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