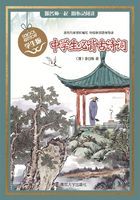三、创作目的:致力于国民摆脱奴役走向人的境界
“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这个艰巨的历史使命首先是由鲁迅自己承担起来的。“‘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是一件极伟大的要紧的事,也是一件极困苦艰难的事。”自“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起,鲁迅始终将改造国民劣根性与再造现代公民作为自己文化实践的根本任务。在他的全部文学创作中,凸显着巨大而鲜明的“人”的主题。
在长期的文化反思和创作实践中,鲁迅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进行了意义和价值的再认识。中国文化不但存在于纸质的有形的“编年”、“鉴略”等史书中,更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深层的心理结构中。“作为文化大师级的作家,对中国现代社会的演变与中国国民性格的模式曾经作过本世纪思想史上最为深刻的透视和反思,这些透视与反思的结果甚至包括困惑都体现在他的文学创作中,构成了鲁迅小说与散文创作中一些不断重复出现并且相互联系的主题现象。”他的冷静叙述与客观呈现引起我们严肃的思考;他在对中国的人生有着毁灭性破坏的文化传统的批判中,包含着对民族新文化构建的理想;他的文学创作实践是与他的“立人”总目标紧密相关的,他的创作力图在遏制人性弱点的同时,重塑中国人的现代品格。因此,他的文学具有一种艺术审美化的“人学”品质。这使鲁迅的文学创作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文明进程中显示了不可低估的力量和价值。有学者预言:“如果说鲁迅的社会批判带有更多的时代性,那么鲁迅的文化批判带有更多的超越性。只要中国继续迈向现代化,鲁迅的文化批判,鲁迅为中国传统文化诊出的病症,在21世纪的中国就仍然具有极大的价值。”只要中国人还没有达到“人”的高度,鲁迅的思想和文学就将一直存在下去。
第三节 语文课程的终极目标:“立言”以“立人”
一、“语言”:从工具符号转向人类存在始源
古有“三立”之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所谓“立德”,即做人首要是以身立德,为人楷模;所谓“立功”,即建功立业,垂范后世;“立言”一说,有著书立说、撰写文章、提出主张等多种解释,历来为人所重视。如孔颖达所疏:“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其身既没,其言尚存。”可见,“立言”不但与人生俱在,而且还会流传后世,产生历史影响。语言与人的密切关系,以及优秀语言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可见一斑。在此,我们借“立言”一说,用来泛指一切语言活动,特指以语言为媒介最终通过培养语言能力以达到“立人”宗旨的语文教育。
回顾20世纪,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语文课程的工具属性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这除了“文以载道”的民族文化传统和实用工具理性之外,苏联斯大林语言观的影响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化因素。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一书中,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语言学的理论基础上,对当时语言学的重大问题,如语言与社会、语言不是一种上层建筑、语言是全民的、语言没有阶级性、基本词汇和语法结构是语言的基础等问题都进行了系统的论述。斯大林关于语言的论述,不仅对苏联本国,而且由于特定的历史因素,对中国的普通语言学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最深的莫过于“语言是交际工具”的观点。“语言是工具,人们要靠它来互相交际,交流思想,达到相互了解。语言从产生时就是为了适应交际的需要,产生以后一直作为人们交际的手段来使用。一旦某种语言不再作为交际工具来使用了,就意味着这种语言的消亡。所谓用语言进行交际,具体说来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说话人要运用语言这个工具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另一方面听话人是通过这个工具来理解对方的表达。说语言是工具,指的就是它作为交际工具,使人们能够互相了解并调整他们在人类活动的一切范围中的共同工作。”20世纪80年代末期,在语言本体论思潮中,人们在与同时期西方语言理论发展相比较时发现,“我们所使用的语言——汉语,尽管具有悠久的历史,但严格来说,它并没有因此而产生在哲学和本体意义上的语言学理论”,“‘语言’在我们这里只能为‘用’而很难为‘体’,也就是说,我们还很难把‘语言’上升到哲学层面上去理解,而只会将其拉到‘工具’,最多只是‘材料’的位置上去使用”。
在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工具性”始终是语文学科的基本属性。所谓“工具性”的概念主要有两个义项:一是政治思想教育;二是语言知识和应用能力。1963年《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在“语文的重要性和语文教学的目的”中指出:“语文是学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各种工作的基本工具。”1978年3月,教育部制定颁布了《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行草案)》,强调语文的基础工具性,重视思想教育。新时期以来,对语文学科的性质进行了认真的探索和讨论,形成了“工具性”、“人文性”、“素质论”、“语感论”等不同观点,但“工具性”观点始终占据统领地位。“语文是人们的交际工具,是‘学习和工作的基础工具’,因此工具性是语文学科的本质属性。语文课的任务就是进行语言知识教学,培养理解和运用语言的能力,即听说读写能力,课文只是一个例子。有人甚至主张语文课就是传授语文知识的课。”2000年版《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验修订版)》有意淡化了“工具性”,加强了“人文性”。至此,语文教育理念才开始有了新的转变。
1987年出现的“语言本体论”思潮,是中国人对语言独立地位的确认和认识上的觉醒。“语言本体论不仅把语言看作文学作品的形式构成要素,而且把语言看作人类的本体、世界的本体,使之从‘器’的层次完全上升到了‘道’的层次,从而成了真正哲学意义上的本体论。”它的哲学基础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海德格尔认为,在人的原始状态下,人的存在和语言是同一的。人的思维不是对纯粹客观外界的逻辑反映,而是存在通过人来呈现或显露。“语言就是说‘话’,‘话’即思中之‘在’。‘在’就‘住’在‘话’里,是‘在’有话要说,才由语言把‘话’说出来,换言之,是人从‘在’那里听到了这些‘话’,然后才说出来。所以实际上不是人在说‘话’,而是‘话’在通过人来说。语言不是人的工具,人倒是语言的工具。”语言是人的存在之家。这样,海德格尔就在“本源性”的意义上对语言作出了解释。受海德格尔哲学启发,我国文艺批评理论界对语言的认识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人有语言,表明人与世界的关系得到了确证;语言将人与一般动物划出了一条永久的分界线;语言成了人类生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的一种生存方式,是人类的一种存在。这样,语言不再只是认识人和世界的认识论工具了,而且还具有突出的生存本体的意义。”也有学者将文学的诗性语言和普通语言区分开来,认为文学“是人的一种语言的存在,确切地说是诗性语言的存在”。它“不是作为研究人、表现人的材料、手段或工具,它本身就是人的语言方式的存在,是人的不可或缺的、有意义的生存方式。
正是在这里,作为人的一种有意义的存在方式的诗性语言与作为工具的普通语言之间构成了质的区别”。
“语言本体论”对于语文教育带来的深刻启示在于:对文学作品的解读,不能够仅仅停留于外在的语言形式层面的认识上,而应该去研究一个作家为什么“这样说”,而不是“那样说”,即从作家的言说与他的生存根基的关系去解读作品。这样不仅有助于读者加深对文学作品本身的理解,而且通过对文学作品与人的存在关系的深度阐释,反过来理解人和认识人自身,求索人的生存意义,关注人与世界的相互关系,产生改造世界和美化人本身的审美愿望,从而在语言实践中建构人自身,将语文课程本身还原到本体的地位。
二、人文性:无可摆脱的课程属性与人本承载
由于受“文以载道”传统和长期的政治影响,我国当代语文教育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工具理性色彩十分浓厚。教育理念的落后除了对语文教育本身的发展形成阻碍之外,对于受教育者——“人”的全面发展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更大。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和改革深化带来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形成,以及全球一体化趋势的出现,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问题被提到一个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世纪之交展开的语文教育大讨论,使人清醒地看到由于文学教育失误给人文素质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在1998年由《北京文学》为论坛的讨论中,人们更多地看到语文教育中“人的缺失”:“我们的阐释体系往往能把经典作品讲偏、讲歪,讲得味同嚼蜡,刻板无趣,仿佛全世界所有的作品都可以用反对封建主义、批评资产阶级、同情人民大众诸如此类的大词来概括,再加上阶级局限、消极面,就万事大吉、天衣无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