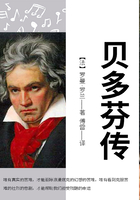受访者基本情况
性别:男
年龄:46岁
籍贯:江西
婚姻状况:已婚
文化程度:高中
打工时间:1987年至今
打工地点:浙江宁波
打工类型:小包工头
天,开始阴沉下来,预示着一场大雨即将倾盆而下。
我站在冷清的十字路口,不知往哪里去寻找合适的访谈对象。来自丽水的卖烧饼的大叔沉默寡言,不愿多说什么;来自福建的卖水饺的叔叔虽然热情,但我挖掘不出什么特别的故事(这时真为自己的访谈水平感到惭愧),而他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你去采访别人吧,他们比我辛苦多了,我至少是自由的”。于是不到十分钟,我离开了饺子店。要找到一个合适的访谈对象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大部分的民工不愿意在一个陌生人面前诉说自己的故事。更多的时候他们选择保持沉默,因为那样更有安全感。
继续搜寻目标。
我来到一个建筑工地上,沿途堆着石块沙砾,还有不少用细竹竿架起的晾衣用的架子,上面挂了些衣服、毛巾。河边几个赤着上身的工人在乘凉聊天,更多的人躲在屋子里。工人们就住在这些已造好的屋子里,他们用很多木板隔起来充当门窗,但还是留着很大的空隙,白炽灯的灯光就大块大块地打在外面的墙上。幸好现在是四月天,要是再早点,冷风嗖嗖地直往屋里灌,这么艰苦的居住条件怎么让人受得了呢?
终于找到了建筑工地的老板,一个中年奉化人。说明来意后,他用奉化方言说道:“其实比起以前,现在的农民工都不怎么辛苦的。有住处,有规定的休息时间。何况在浙江,农民工的条件自然会好很多……”他热情地给我介绍了一个江西的建筑工人。
这是一间10平方米左右的临时小房子。一张四围用木板围成的床,一张陈旧的四方桌,左边是一排矮矮的木桌,上面放着煤气灶等简单的厨房用具和一些零碎的东西,墙上挂着安全帽,一盏白炽灯悬在房顶的中央。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台手掌大小的袖珍电视机。一个胖胖的中年妇女一边收拾屋子,一边瞄几眼电视。看样子,这家人比一般建筑工人条件稍好。走进小屋,老板和屋里的人打招呼,准备休息的男主人公从床上起来。
窗外一道明晃晃的闪电划过,雷声响起,终于下起雨来。我也开始了我的访谈。
眼前的叔叔名叫陈和德,今年46岁,是江西人。矮小的个子,黑得发亮的皮肤,粗糙的双手,一看就知道从事的是常在阳光下暴晒的职业。他的妻子和他是同乡,今年37岁,有点发胖,嘴角挂着淡淡的笑容,让人感觉很亲切。
叔叔,能随便说说您的打工历程吗?
我高中毕业后就在老家江西开始了打工生涯。当时做的是木工,主要是做家具,但是收入很少。
那大概是怎样的收入呢?
在家乡每天1.8元,而在外面每天可以拿3元的工资。
哦,确实差挺多的。那后来呢?
三年后(即1987年),我到福建做建筑工地上的木工。1988年,在老家结婚。后来妻子就留在家中带两个儿子上学,我自己在外面打工挣钱。
五年后,我到了宁波。我先后在明楼小区、三八市场、段塘等地方做建筑工人。去年才来到这个建筑工地,妻子也跟我一起来了。
那阿姨有工作吗?
没有。她就是来给我烧饭的。我大儿子也在这儿,他现在在厂里做机床工人,前两年在温州打工。我小儿子现在16岁了,留在老家跟他大伯伯一起,在上初中。
我很想把孩子接到这儿来上学,考高中,再读大学。可是像我这样,是不可能的。一个,我们居无定所,这里工程完了就得换地方,孩子跟着转校很不方便;第二个,孩子成绩不好,不争气,考不上高中的。(叔叔摇了摇头,似乎有点儿无奈和失落)
嗯,老是要转校确实不方便。其实只要他自己能认真学习,肯定可以上大学的。叔叔,听说您现在是包工头?
哈哈(似乎笑得有点儿难为情),不算啦,只是个小包工头,不像他们那样的。我只管木工活,这里有二十多栋房子的木工活归我管(叔叔说这句话时似乎有点自豪)。我的工资是按月算的,大概每月3000元。一家人每年大概有3万元的收入,扣去日常开支的话,有1万多元的剩余。比起老家的工资来,当然是好了点。但是不稳定啊,如果没有活干了,那就什么收入也没有了。
工作不稳定是不是您最担心的?
(叔叔点了点头)
那叔叔,您能不能谈谈您的家人呢?
我的家人啊……(叔叔想了想,谈论这个话题时一直很平静)父母已经不在了,我们五兄弟,我是第四个儿子。大哥在老家做木工,二哥、小弟在老家开杂货店。小弟去年离开老家跟我一起出来做木工了,收入不好嘛。三哥在老家种田。几个兄弟的生活嘛,马马虎虎。
在这二十多年的打工生涯中,您有没有感觉特别艰辛的日子?
有啊!(叔叔显得有点激动,停顿了一下,似乎在理清思路)从江西到福建,然后到浙江,打工当然是很辛苦的。在2002年,当时我也是在奉化打工,因为太累了,心脏出现了毛病。当时我根本不能工作,只能整天躺在床上休息。后来到奉化的人民医院检查,医生说是心脏的主动脉瓣和二尖瓣关闭不全,必须要动手术。我就又到宁波一家心脏方面比较好的医院复查。医生也说是心脏的主动脉瓣和二尖瓣关闭不全,要动手术。我就住院,动手术。从6月到10月,总共花费了8万多元。这8万多元全从自己的腰包掏出来的,根本没地方去报销,补贴也没有的。当时我的积蓄只有两三万。没有办法,就向亲戚、朋友借,总算付清了医疗费。但是很麻烦的,现在必须天天吃药,而且也不能过度劳累。当时,我还回老家去休养,因为根本不能工作。那个在老家的两年时间啊,真是不可想象!(叔叔无奈地摇摇头感慨道,在一旁的阿姨也忍不住补充道:“那两年可辛苦哩。”看样子那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两年时间是他们心中永远难以抹去的艰辛记忆)
当时,我的两个儿子还在上学,政府也没有给我什么补贴,孩子的学费都是向兄弟借的。我们一家人花钱很省的。妻子种水稻,我干不了重活,就扛着根竹棍到街上卖冰糖葫芦,是自己做的。我们家就靠这点钱过日子的。
当时吃的都是自己种的蔬菜,很少有肉的。不过村里的大队倒是给了点补贴,每年50元。(我诧异了一下,接着我们几个人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我想,在贫穷的乡村大队又能有多少钱呢?医疗补贴若无政府出面,根本就不可能给需要者满意的结果。在外地风雨飘摇打工十多年,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钱,就因为大病一场,全都打了水漂,这个滋味谁碰到了都不好受)
有没有让你特别高兴的事?或者是特别感动的?
(马上摇头)打工苦啊,还有什么可以高兴的事。从来没碰到过,从来没有。(叔叔一直不停地摇头)
不一定是大事啊,一些小事也会让人感觉很开心的。比如和老乡聚在一起时……
没有。打工辛苦死了,哪有什么可以高兴的事。每天就是工作、吃饭。
晚上心情好了,出去走走,到附近看看电视,散散步;心情不好了,就睡觉,工作了一整天很累的,怎么会有快乐的事发生呢?打工苦啊!(叔叔表露出不满的情绪)每天工作10个小时,早上六点钟就起床了,十一点吃中饭,十二点上班,下午五点下班。到了冬天中午十一点半就要上班了,因为天暗得早,中午是没有休息时间的。
食堂又赚我们的钱,卖的菜贵啊!他们(指食堂的人)每月已经有600元的工资的,还要赚我们的钱……
那这儿的老板人还不错吧?
(叔叔没有回答,只是低下了头,似乎不愿意多说什么)
那有没有碰到过什么特别委屈的事情呢?
委屈的事情太多了!(叔叔笑着道,脸上的表情仿佛告诉我,这个问题无疑有着肯定的答案,无需用疑问句)
2001年在台州,有一次是休息时间,大家都在屋子里休息,但小包工头要大家去工作。大家不肯,他就把床铺都掀翻掉了。我非常生气,就把小包工头推倒在地上,结果两个人就打了起来。后来老板过来,我们要老板评理,当然是小包工头错了。他(小包工头)后来再也没有强制大家在休息时间去工作。我们赢了!
还有一次也是在台州。老板有一个亲戚在工地上开了个小店,卖的酒很贵,比外面的贵2元。我很爱喝酒,就从外面一箱一箱地买酒。老板的亲戚不高兴了,一定要我在工地上买酒。我当然不答应,老板亲戚就把我的酒瓶砸碎了。我很生气,就跟那个人打了起来。(叔叔在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的笑容收敛了,似乎回到了当时的情景中,眼神中露出几许愤怒,不停摆动的双手也显示了他内心的压抑与激动)老板亲戚说要赶我走,我才不怕,走就走。但是老板很看重我的,后来就留下来了。我也没办法,就不再去外面买酒,买工地上的酒。就多花了2元嘛,我给他就是了。
还有在黄岩的时候,老板欠薪。快过春节了,老板说现在拿不出钱,扣了我500元,也扣了其他人一些钱,当然是开了欠条的。这样就可以把我们留住了,过年后还会回来拿钱,可以继续做。但这个工地的工资不理想,我们几个人早就不想做了,也就不管钱了,回家过年了。后来不小心丢失了欠条,那么钱是肯定要不回来的了。委屈的事说也说不完的。(叔叔在讲他的辛酸经历时,总会时不时插上这句话)
(这时,屋里进来一个中年男人和一个十几岁的小男孩。他们用家乡话相互聊了几句,似乎在解释我为什么在这里)
叔叔好!这是您的孩子吧?
(中年男人点了点头)
他在这儿上小学吗?
(点头)
学费如何呢?
(中年男人)比本地孩子要多,有200元的“借读费”。按照规定应该是一样的。
那你们可以去投诉啊,比如向县教育局举报。
(中年男人摇了摇头,满脸的无奈)算了,多就多吧,向谁说去,麻烦啊!
他们(指收费的小学)也了解我们的,知道我们不会怎么样的。他们对我们说,想读就交钱,不想交钱就不要在这儿读了。我们没办法的,就交钱了。
(中年男人走后,我继续和叔叔聊)
叔叔,您以后是有什么打算呢?
(叔叔幽默了一把)准备回家去种田了。人老了,做不动了,不如早点回家去种田。大概过几年就回去了。
(我不由地笑了起来)回家种田肯定是不可能的。在外面做得好好的,现在种田又挣不了多少钱……
哈哈哈……(叔叔和阿姨都笑了。停顿了一会儿,叔叔低着头摇了摇)
但实在是太辛苦了,太辛苦了……(确实,叔叔除了每天在工地上工作很辛苦外,换地方时搬来搬去也是一件痛苦的事。疲于奔波,疲于日晒,疲于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疲于没有喘气的连续劳动)
(雨停了,再三道谢后离开叔叔和阿姨。雨后的空气格外清新,夹杂着不知名的花香,沁人心脾。一排排未完工的房子的轮廓在夜幕中显得朦胧,我仿佛看到了建筑工人们在搭起来的竹架上辛勤地劳动着,挥洒着汗水,正是他们身上斑斑的泥浆,才铸就了这一幢幢昂然挺立的楼房)
访谈员手记:
访谈结束后,久久徘徊在我脑海中的两个字就是——艰辛。身处在安逸环境中的我无法体会到他们生活中的辛酸,无法体会到每天高强度地连续工作10个小时的劳累,无法体会到作为特殊人群的无奈与不甘,还有蛰伏在内心深处的希冀与梦想。
叔叔是个非常直爽的人,虽然岁月在他身上留下了很多烙印,但一路的艰辛并没有消磨他的斗志。他一直都在努力地工作着,为了家庭,为了生存。阿姨平易近人,脸上一直挂着浅浅的微笑。这是一对会把伤痛与苦难埋在心底的夫妇,虽然现在的生活并不能让他们很满意,甚至有不少怨言,但他们一直在笑着和我聊天,伴随着热情亲切的笑声。我不明白打工者对于幸福的定义。也许真的是与我们的定义不同,也许生活在安逸中的我无法体会他们的心情,也许作为一个艰辛奋斗、没有很好享受生活的体力劳动者来说,生活中一些小小的喜悦已经无法触动他们那根慢慢迟钝的神经。
也许快乐对于他们而言很简单,有满意的工资,宽容的包工头,足够的休息时间,而这些正是他们无法企及的目标。
农民工们由于种种原因,怀着戒备的心理与本地人相处。访谈时走进来一个妇女,不说一句话,只用戒备的目光打量我,让我有点尴尬;之前我在工地上好不容易“逮”到一个妇女,迎上去说明来意后,她也不愿多理我,径直管自己离去。这反映了一部分外来打工者的心理(尤其是女性)——不愿融入当地社会,宁可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中,以便寻得自我保护,一心挣钱,避免不必要的冲突。
人是有群居特性的,而且谁不想工作之余有娱乐,谁不想被公平地对待,谁不想得到周围人的关心和肯定?而大部分的农民工总是在所在地区成为一个被无形隔离的群体。除了农民工本身的原因外,我们的社会也有责任。
他们不知道如何去正确维护自己的权利,即使知道也由于种种限制而去采取并不正当的方法去试图解决,有时候则是无奈地承受不公的待遇,就如叔叔提到的“委屈的事情”。这些包工头、老板的亲戚的做法让我非常接受不了。在面对这么一个弱势群体时,他们的表现不是同情、帮助,更多的是蔑视、欺诈,甚至漠视人最基本的尊严和自由。而农民工们自然不堪时时忍气吞声,他们会起来反抗,扞卫自己原本就很微薄的权利和自尊。有时会胜利,更多的时候是妥协。他们反抗的手段最多的是“打架”。是啊,除了打架他们还有什么办法去平息心中的怒火,维护自己的权利呢?投诉?向谁投诉呢?真的能解决问题吗?
他们匮乏娱乐,匮乏知识。劳作一天,唯一的娱乐就是看会儿电视,散散步,然后睡觉。记得有些在农民工聚集的地方,晚上会有“街头舞会”。虽然场面乱糟糟,音乐很嘈杂,舞姿并不美,但那些姑娘小伙子,甚至中老年人(有时本地人也会加入这个热闹的行列)的脸上都绽放着快乐的笑容,完全卸下了白天的劳累。不管这些活动是民工们自动发起的,还是当地某团体组织的,都是值得肯定的。
农民工,生活在城市边缘的一个特殊群体,默默无闻地为城市建设付出艰辛劳动的可爱群体,他们需要社会的正视和真正的认同。在喧闹的城市中,他们寻求着一块属于自己的天空,他们也希望得到城市人所享有的待遇。如果那样有点奢侈的话,他们希望享有人起码的尊严和自由。
近来,社会和政府对农民工确实投入了更多的关注,也制定了一些保障农民工基本权益的政策。这是个很好的现象。期待我们能给他们更多的温暖和关怀,让社会真正的进步、和谐!
(访谈员:朱瑞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