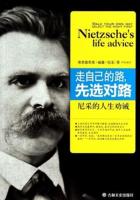杨绛对丈夫的散文小说诗思记述,运用了独特的视角:一是学术视角,二是情感视角,三是历史视角。当杨绛从学术视角切入对钱钟书的叙述时,她不可避免地要从《围城》入手。她并不对《围城》的主旨进行学术阐释,而是真实地再现钱钟书的创作生活,再现了他们的爱情生活。这种琴瑟谐和的情调本身,也就成为生命自由理想价值的追求和向往。“每天晚上,他把写成的稿子给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样反应。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这种笑的层次,这种笑的境界,这种笑的内涵,只有他们两心的情爱相知,其中,也间接透露了他们所共同追求的幽默效果。在散文的自由诗思中,杨绛让读者相信钱钟书的虚构和想象充满生活的乐趣,“创作的故事往往从多方面超越了作者本人的经验。要从经验的故事追求作者的经验是颠倒”,这无疑是以独特的方式写的“虚构颂”。当钱钟书的《围城》发热发光之后,钱钟书的《谈艺录》、《管锥编》成为“神话”之后,他的朋友、学生、青年学者,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关于钱钟书的“神话”和价值论美学阐释。在这一切声音之上,杨绛的发声是独特的真实的。她以散文小说诗思的叙述,最真实地展示了钱钟书的生活,她以夫人的身份和朋友的立场,披露了钱钟书真实的心灵世界。她真实地叙述了《围城》创作时的家庭生活和时代状况以及人物取材和构思经历,这是最真实的作家心灵的展示。杨绛的幽默风采,在情感视角观照钱钟书时充分展示着,她写道:“钱家人爱说他吃了痴姆妈的奶,有‘痴气’。
我们无锡人所谓痴,包括很多含义:疯、傻、憨、稚气、孩子气、淘气等。”杨绛旁敲侧击,突出钱钟书智慧性的弱点,活脱脱地写出了钱钟书的独立不羁。这种“痴气”,与他人眼中的钱钟书具有“傲气”相反相成,造就出奇异的学者性格。夫妻的情感和谐中无事不谈。钱钟书的童年趣事,显然,是在多方面的闲聊中浮出并深记的,长久停留在杨绛记忆深处的往事,连同中年过后的练达,显得风雅多趣。杨绛在对钱钟书的情感记忆中,非常重视钱钟书的“才”。“那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钱穆的一本书,上有钟书父亲的序文。据钟书告诉我,那是他代写的,一字没有改动”,这是写钟书的奇才怪才。“我常见钟书写客套信从不起草,提笔就写。八行笺上,几次抬头,写来恰好八行,一行不多,一行不少。钟书说,那是他父亲训练出来的,他额角上挨了不少‘爆栗子’呢!”这是达观的叙述者,在给来访的朋友介绍钟书的鬼才,这里,充满存在的怡然自得。
从杨绛的叙述过程中,可以看到,这对夫妻作家的幽默是相互创造的。
“我们俩日常相处,他常爱说些痴话,说些傻话,然后再加上创造,加上联想,加上夸张,我从中体味到《围城》笔法。”这些叙述,分明透露了这样的生命消息:无论是得意,还是失意,真正的知识者都不忘肯定自己的过去,肯定自己的才能,肯定自己生活的勇气。
真正能体现他们生存勇气的,还是从历史视角中观照钱钟书。杨绛和钱钟书,在“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岁月,承受了残酷的精神折磨。当杨绛叙述到女婿被迫自杀时,自己被斗时,钱钟书被剃成“阴阳头”时,他们都不忘用幽默达观的态度来排解。两人相互依靠,坚定信念而不失去“存在的勇气”,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正气歌,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理想放射的人格光辉。这种对时尚政治存在价值的抗拒,具有特别的意义,从散文的自由诗思中,应该看到,知识者的生命存在价值,自省而克制,他们无法直接挑战时代的政治生命价值或非自由的生命存在价值,但是,他们能够坚守生命存在的独立与自由,这其中,就呈现了知识者的价值信仰,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保持生命存在价值的正直与勇气。杨绛以生命感受,几十年的深厚理解,写出了特殊而又平凡的钟书,写出了知识分子的创造智慧和生存勇气。在苦难的岁月里,钱钟书仍痴情于中国古典文学和中外文化比较,这种信念,正是来源于知识分子存在的勇气。
杨绛以最真实生动的笔触,展示了高级知识分子之间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关心,正好说明,真正的知识分子,真正具有自由人格的知识分子,不会放弃自我坚定的人生信仰。无论他们身处何种逆境,都会勇敢地创造和奉献。杨绛的散文小说诗思,能达到这种思想深度,既是出于深度体验的自觉,又是出于理性的呼唤。
宗璞比杨绛年轻,但她对中国现代社会的急剧变革一直忧心如焚,她从父亲身上看到了知识分子的特殊使命。事实上,儒家人格从精神深处指导着她们的生命价值取向。宗璞对父亲的人格精神素描并不完整,她对父亲无限敬爱。宗璞之所以没有长篇大论地叙写关于父亲的生活,是因为冯友兰其实也是散文小说诗思家。冯友兰的一生,皆沉浸在以诗性散文与诗思表达之中,他的生命哲学观念的创造,例如,《三松堂自序》和《三松堂集》,可以视为冯友兰最优美的散文诗思结集。那些出色的散文诗思,是诗与哲学的融合,是诗与思的统一。宗璞长期照料父亲的生活并从事业余写作,也许宗璞的文学天赋优于哲学天赋,所以,她不可能或者没有精力去深究父亲的透彻之思。但是,父亲的人格观念,父亲的审美理想,朋友与父亲的交往,父亲的未尽心愿,父亲的着述过程和创作态度,以及父亲的不老诗心,宗璞是最熟悉不过了。遗憾的是,我们还没有看到宗璞关于父亲的散文小说诗思或回忆长篇,但就仅见的散文小说诗思篇什来看,这对父女的感情,是相当融洽而且平和亲切的。
宗璞的严肃责任感,培植了她对父亲超乎寻常的报恩或关心情感。
哲学家突然成了旋转的陀螺,不能自由选择方向时,是何等痛苦。“老实说,三十年来,从我的青年时代开始耳闻目睹,全是对父亲的批判。父亲自己总是检讨。家庭对于我,像是-座大山压头顶,怎么也逃不掉的。”当听到人们对父亲的重新肯定和科学评价时,宗璞感到自由与欢悦。宗璞的散文小说诗思总是由一点引发开去,由特殊意义上升到普遍意义上去。
如给父亲祝寿,她在散文的结尾写道:“为天下父母,喝一口酒”。她把个人的情怀和人类的情怀沟通在一起。正是从父亲的身上,宗璞看到了知识分子存在的勇气,她在散文的诗思中写道:“从父亲身上我看到了一点,即内心的稳定和丰富。这也可能是长寿的原因之一。他在具体问题前可能踌躇摇摆,但他有一贯向前追求答案的精神,甚至不怕否定自己。历史长河波涛汹涌,在时代证明他的看法和事实相谬时,他也能一次再一次重新起步。”冯友兰以儒家人格和生命哲学为本,通过儒家哲学的不断理解,寻求生存的真理,这是知识分子的探索道路,没有失去勇气的存在之路。
她着力突出父亲撰写《中国哲学史》的执着精神和不懈勇气,还专门谈到父亲的预言:“中国哲学将会在二十一世纪大放异彩。”宗璞十分重视知识的自由人格,知识分子要求做人的尊严;这种尊严神圣不可亵玩,充分体现在宗璞的散文小说诗思叙述中。
宗璞的散文小说诗思中,充满很强的理性成分,所以,感性的读者往往对她敬而远之。理性的读者,则从她的散文小说诗思中看见了精神深度。宗璞是冷峻的,诚恳的,严肃的。从杨绛的钟书论和宗璞的冯友兰论中,可以看到,她们在大致相同的文化环境和时代里,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心态。杨绛乐观、长歌当哭、幽默;宗璞沉思、认真、拥抱理性。如果说,杨绛的散文小说诗思充满喜剧精神,以喜剧去怀念生活,评论悲剧时代,歌颂知识分子的自由人格,那么,宗璞的散文小说诗思则充满悲剧精神,沉重地表现生活,恸哭着缅怀。宗璞在特定的文化中,很难乐观地笑起来,她悲思着;杨绛在动荡的岁月中,则蔑视丑角,敢于开怀大笑。面对荒诞,她敢于机智地逃避;为了亲人,她敢于作出牺牲,她们以不同的文化心理展示了中国知识分子女性的生命体验。由她们的钱钟书论或冯友兰论扩展开去,我们应该相信,中国知识分子永远不会失去自信力。人格完善不仅是古典的命题,而在将来仍然是具有永恒性的价值标尺。儒家性情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之本,一切自由和欢乐最终总是“孔颜乐处”。
5.3.3亲情坚守与普世幸福的抒情想象和期待
应该承认,对亲人的怀念、记叙和理解,在散文小说诗思创作中,只不过是杨绛和宗璞的外在生活的表现,她们创作的重要内容,更是对内在精神生活信念的传达,不是对他人存在的阐释,而是表达并肯定自我存在的勇气。这种深度的创造传达,是杨绛和宗璞散文小说诗思之魂,雅斯贝斯曾指出:“勇气不仅仅是生命力,也不仅仅是赤裸裸的挑衅的力量。它只能存在于从生存的桎梏里所争得的自由中,存在于揭示出来的无畏灵魂,坚定的信念,赴死的能力中。”杨绛和宗璞,早年皆就读外国文学,而且,曾先后在清华大学外文系深造过,这就构成了她们的某种相似性。杨绛对外国文学的理解,有《春泥集》和《关于小说》,宗璞也有类似的着译。杨绛对英国散文小说和塞万提斯的小说尤有创作心得,宗璞则对卡夫卡和德国小说尤有研究,她们在小说和散文诗思之间耕耘。我们甚至可以把杨绛的《洗澡》和宗璞的《三生石》这两部小说,当作散文小说来读,这是她们用血泪写成的篇章。杨绛和宗璞对知识分子精神生活的反省,再一次把人的“存在的勇气”这一问题提出来。活下去,要坚定地活下去,要敢于怀疑地活下去,这是杨绛和宗璞散文小说诗思所表达的共同信念,因为世界有真,有善,有美,等待我们去发现和创造。这些散文,真实地叙述了知识者的价值论美学信念和生命存在的自由价值沉思,他们重视通过艺术,通过情感的语言,通过心灵的记忆,通过自由之思,把生命的美感与生命的价值给予特别的重视。
在平和的环境里,每个人都会有存在的勇气,但是,在厄运和磨难的岁月里,存在的勇气就会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杨绛选择了那段不能忘怀的岁月,写成《干校六记》和《丙午丁未年纪事》。不堪回首的岁月,杨绛觉得实在新奇,那种中国几千年酷刑的各种变相形态,竟然在一时期完全复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那么复杂迷茫,杨绛仍是忙里偷闲,悲中找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