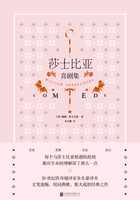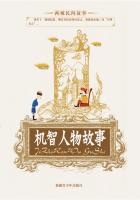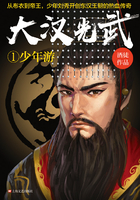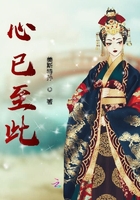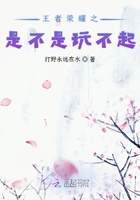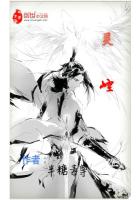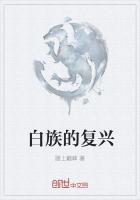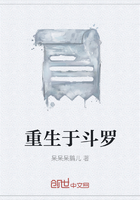“我”只有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才能感受到自然本性的体贴。这与“我”在人群当中感受到格外的寂寞和孤独形成强烈的对比。在这种柔性叙事当中,郁达夫将一个身在异国他乡的游子的心灵世界展现得细致入微,使小说更“有意味”、更“有情致”。郁达夫不是煽情的艺术高手,而是善于抒情的艺术高手,他的小说具有浓郁感伤色彩的柔美之情。从《沉沦》开始,他所塑造的“零余者”形象,无不浸染在一种哀婉、忧郁、颓唐的情绪之中。
这群“零余者”或是在国外深受异族鄙视的弱国子民,或是回国后身居畸形都市中报国无门的落魄文人、失业者、流浪人,虽有理想、有抱负,却穷困潦倒,在现实社会中没有立锥之地,是一群被挤出社会的小人物。他们自暴自弃、自哀自怜、颓唐堕落、沉溺酒色、放浪形骸。显然,主人公的情绪状态是建立在被遗弃、被放逐的孤苦伶仃的境遇之上的,对自身不幸遭遇的哀怨,以及由此产生的漂泊不定的飘零感,是郁达夫小说感伤之情的美学根源。郁达夫以柔性叙事的方式,打破了写实主义小说那种依据事件发展的线形叙事惯例,在将小说的重心置于抒情的链条当中,构筑了以柔性审美元素为主导的自然、流动的抒情性小说结构。
在使小说的主人公染上一种忧郁的柔情色彩的同时,也形成了他的抒情体小说所特有的,与柔性审美元素相关联的感伤之美。与郭沫若所抒发的雄奇之美不同,郁达夫的感伤之美更加凸现了历史行进中的艰难性和复杂性特点,折射出时代的负面因素在人们心灵中所投下的重重阴影。与郁达夫小说创作风格相近的浙西作家倪贻德,他的散文化的小说结构,重写意、重律韵、重抒情节奏,风格飘逸、柔婉。如小说《零落》,以自己家庭败落为摹本,写一个书香门第家庭的败落,表达出对家庭的深深惋惜和依恋之情,像江南绵绵细雨,丝丝缕缕,如梦似烟,小说柔婉的抒情味极浓,行文清丽、秀婉。
徐志摩的诗歌也是以“柔婉”的美学风格而享有盛誉的。最能代表他的风格的是那些“从性灵深处来的诗句”,也即那些追求单纯信仰、争取个性自由解放,歌唱理想爱情和大自然之美的抒情诗。徐志摩走的是“柔性自我表现”的艺术道路:以江南才子之灵气、英国绅士之风度,展现潇洒飘逸、秀丽缠绵的艺术风格。《沙扬娜拉》、《我有一个恋爱》、《消息》、《翡冷翠的一夜》、《海韵》、《雪花的快乐》等,所展现的是诗人顾影自怜、风流倜傥的自我形象:跃动飘逸、柔美细腻、空灵清澈。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
那一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
——沙扬娜拉!
——《沙扬娜拉》
婀娜的娇羞、似水的柔情,这首白话小诗就是这样通过对一个富有特征的动作(“一低头”)、一句富有深情的话语(“一声珍重”),将东方女性特有的柔婉温情,永远定格在人们的面前。这是诗的精灵,这是人间的真情,它绝不是一般世俗意义上的男欢女爱,而是表现出受五四新思想催醒的年轻一代,对“爱”与“美”理想的执着追求。又如,他献给母校的那首《再别康桥》: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
软泥的青荇,
油油的在水底招摇;
在康桥的柔波里
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1928年的秋天,一艘寂寞的海轮,载着诗人对母校依依不舍的眷恋之情而缓缓驶去。海风阵阵、雾气弥漫,离愁别绪,点点滴滴涌上心头,母校的一草一木又都重新显现在他的脑海中:落日的余晖、依依的杨柳,犹如盛装的新娘,矜持娇羞。“康桥”——“我难得的知己”、“永为我精神依恋之乡”,这是诗人于1922年8月在离开英国回国之前所作的题为《康桥再会吧》一诗的诗句。
在“康桥”的形象描绘中,徐志摩寄寓了他精神寻梦的理想和思乡情感。1926年1月,徐志摩在《我所知道的康桥》一文中细说他1920年离美赴英的原委,并在文末满怀深情地倾诉:“康桥,谁知我这思乡的隐忧?”“思乡”除了在显性的层面上,指的是对故乡的思念,还在隐性的层面上,传达了自己对精神家园的努力寻找。所以,“康桥”形象的柔美,对应的是诗人心灵的“思乡的隐忧”,是对“精神依恋之乡”的不断寻找。整首诗就是在这种柔婉、柔美的风格意境中,展现出了诗人那新月般的清幽而忧郁、纤秀而柔婉的情怀。
在审美意象的择取上,徐志摩总是善于择取那些空灵清澈、柔美细腻的形象来加以艺术的提炼。大凡星辰明月、云霞彩虹、白莲梅花、飞萤流泉、杜鹃黄鹂……都成为他择取的对象。这些来自大自然的清新形象,作为柔婉、柔美的艺术元素,经过他的审美提炼,都是以新鲜、浪漫、潇洒、飘逸、柔美、活泼的青春形象出现在白话新诗史上的,成功地提升了白话新诗的审美意境。
从杭州走出来的现代着名诗人戴望舒的诗歌创作,也是呈现出一种“柔婉”特征的美学风格。在诗人的记忆中,雨巷寂影则构成了他心目中的杭州印象,因为那忧伤、悠长而寂寥的雨巷,正好对应了一群觉醒了,但又找不到理想出路的现代知识分子那寂寞、忧愁、苦闷的心灵世界:
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逢着
一个丁香一样的地
结着愁怨的姑娘。
…………
她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
撑着油纸伞
像我一样,
像我一样地
默默彳亍着
冷漠,凄清,又惆怅。
雨巷的意象是阴性的、柔婉的、凄清的,女郎彷徨的身影,也是忧伤的、冷漠的、惆怅的。它不同于人们熟悉的古都杭城那种妩媚、秀婉、明丽的倩影,也有别于西湖一池春水的清澈、柔情、碧波荡漾,而是突显出烟雨迷离的江南古城、寂寥雨巷的细腻、绵长、柔美、凄婉的精神气质。
诗中透露出来的那太息般的感叹、凄清寂寞的身影、梦一般的“凄婉迷茫”,展现出了现代知识分子面对着沉重的精神负荷和激烈的冲突所形成的困惑、孱弱、沉重的心理境况,以及在风起云涌的时代浪潮前,惮于前驱却又不甘于滞后、梦醒了却又无路可走的犹疑、矛盾、痛苦的心态。
同时,在诗人将杭州、西湖浓墨重彩的风景转化为朦胧迷离、依稀可见的雨巷和哀怨又彷徨的寂寞姑娘的身影当中,柔婉的艺术展现,则消散了笼罩在江南古城的静谧、持重、典雅,冲淡了传统的江南山水的经典之秀美、古典之雅趣,使人只能在悠长、寂寥、狭小的雨巷,在如丝如缕而凄清、缠绵的细雨中,去追寻孤独,咀嚼苦难,品尝寂寞,让彷徨的身影消失在朦胧的雨巷里,最终化为虚空、化为乌有。因此,结着愁怨,像丁香一样的姑娘,也只能成为梦幻中的影子,成为漂泊、流浪,以及怀着乡愁的冲动到处寻找家园的象征。
来自浙西区域的女性作家的创作,则更显柔婉的艺术风格。为数不多的从浙西走出来的女性作家,如林徽因、陈学昭、郁茹等,也大多具有浙西区域江南文化的柔婉气质。像被称为现代才女的林徽因,她的创作构成了她生命的一部分,那秀雅、柔婉的艺术风格,更多折射着那个时代特定的文化审美风尚。尽管她的那种风尚的温婉,没有使她成为像同时代的冰心、庐隐、石评梅、淦女士,或丁玲、萧红、张爱玲那样,成为以写作为生,又为写作痛苦,从追求自由的爱开始,然后又为爱所困厄的新女性,然而,良好的家庭背景和教养,使她作出了符合自己个性、才情的选择。她的柔婉、典雅的现代女性气质,使她成为京派文化圈中最不平凡的一个现代女性。林徽因承认自己是受中西文化教育长大的,英语对于她来说,是一种内在思维和表达方式、一种灵感、一个完整的文化世界,而汉语对于她来说,也不仅仅只限于母语的功能,更重要的是汉语的文化,也即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母文化,孕育了她那特有的东方女性的温婉、优雅、贤淑的性格和气质。中西文化融合造就了一个“现代才女林徽因”、一个“现代诗人林徽因”、一个“中西文化林徽因”。
她是诗人、作家、建筑家、艺术家,她的作品既具有现代女性的独立人格与个性,同时又不失传统美德及本质的温婉美好,显示出现代知识女性特有的高贵与典雅。林徽因在《别丢掉》一诗中就这样写道:“别丢掉,/这一把过往的热情,/现在流水似的,/轻轻/在幽冷的山泉底,/在黑夜,在松林,/叹息似的渺茫。/你仍要保存着那真!/一样是月明,/一样是隔山灯火,/满天的星,/只有人不见/梦似的挂起,/向黑夜要回/那一句话——/你仍得相信/山谷中留着/有那回音。”
全诗在柔婉的风格中展现出了现代知识女性对理想、对真理的执着精神。因为在她看来,只有这种执着的精神,才能够真正地显示出生命面对无常所具有的高贵的意义。在题为《时间》的诗中,她是这样抒发自己对生命的叩问的:“人间的季候永远不断在转变/春时你留下多处残红,翩然辞别,/本不想回来时同谁叹息秋天!/现在连秋云黄叶又已失落去/辽远里,剩下灰色的长空一片/透彻的寂寞,你忍听冷风独语?”生命自身也许是无法呈现自身的意义的,但具有生命意识的人,必须赋予有限的生命以无限的意义。因此,叩问生命、寻找意义,是林徽因创作的主题思路:
什么时候再能有
那一片静;
溶溶在春风中立着,
面对着山,面对着小河流?
什么时候还能那样
满掬着希望;
披拂新绿,耳语似的诗思,
登上城楼,更听那一声钟响?
什么时候,又什么时候,心
才真能懂得
这时间的距离;山河的年岁;
昨天的静,钟声
昨天的人
怎样又在今天里划下一道影!
——林徽因:《无题》
对生命的叩问、对生命意义的探寻,作为女性作家,林徽因找到的依然是人间的爱,如同她在《你是人间的四月天——一句爱的赞颂》所歌咏的那样: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笑响点亮了四面风;轻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
你是四月早天里的云烟,
黄昏吹着风的软,星子在无意中闪,细雨点洒在花前。
那轻,那娉婷,你是,鲜妍百花的冠冕你戴着,你是
天真,庄严,你是夜夜的月圆。
雪化后那篇鹅黄,你像;新鲜
初放芽的绿,你是;柔嫩喜悦
水光浮动着你梦期待中白莲。
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
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
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生命、爱,在林徽因柔婉的抒情意境中,达到了情感的极致。同样是现代知识女性的陈学昭,她的创作也始终离不开现代女性的主题,离不开柔婉的艺术抒情,特别是她早期的创作,也是以清丽、秀婉、柔美的笔触,写出了现代女性,尤其是现代知识女性对生命理想的追寻。在早期创作的《倦旅》、《寸草心》、《烟霞伴侣》等作品中,陈学昭往往是以青春少女心灵独白的方式,传达出受五四新文化影响而觉醒了的现代女性的彷徨、苦闷之情:这样烦闷的生活,为什么要挨着的呢?
生存着为什么呢?
梦醒了却无路可走,往往是五四青年男女共同面临的人生问题。
陈学昭用如诗似画的艺术传达,展现了五四青年男女对生命的咏叹、对美好生命的企盼,整个艺术风格清新、飘逸、细腻、柔婉。相比之下,出生在杭州的现代女作家郁茹的创作,虽然略带有一些刚性色彩,但总体风格仍然保持着江南女子那种特有的柔婉风格。她的代表作《遥远的爱》对时代女性的形象塑造,颇具茅盾的风格,不仅在思想认识方面具有“慑人的光芒”,而且也极具“细腻”、“俊逸”的艺术魅力。作者以两性情爱为视角,通过对罗维娜“唾弃那两个厮守着的狭的自私的爱”,走出家庭,融入社会主潮,成长为昂首阔步的抗日新女性,充满矛盾和痛苦的内心斗争的心路历程的叙写,热烈地歌颂了勇于反叛灰色生活的积极进取精神和献身神圣事业的高尚品格。为了凸现这一主题,作者运用了浓郁、柔婉的抒情,细腻、缜密的心理刻画和人物性格的对比、衬托等艺术手法,真实地描绘出时代女性的心灵世界。正如茅盾所指出的那样,郁茹的艺术风格是“有细腻的心理描写和俊逸的格调”,同时“更具有女性作家所擅长的抒情的气氛,而构成这氛围的,又是那虽非纵横磅礴,但却醇厚深远的对于人生的热爱,对于崇高的理想的执着”。
茅盾还高度赞扬她的代表作《遥远的爱》是“给我们伟大时代的新型的女性描出了一个明晰的面目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