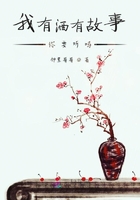守令去留
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二月初十的绵密春雨中,李超琼雇下一条摇橹船,提前一夜赶到横眄镇。船就歇在一座小石桥底下,他和艄公一起缩在船舱里过夜。次日天麻亮时,风雨未见稍停,反而越下越大。不能再等了,他请艄公冒雨解缆,鼓枻而进,渡过江去。天大亮时,摇橹船在浦江西岸的杨家渡靠岸。这里已是上海县的地界。
新任知县李超琼浑身湿漉地走进了位于小东门的上海县衙署。原以为李超琼要等雨过了才会到,现任的上海知县王少谷有些匆忙,赶紧着人在衙署签押房里隔出一角,搭上个铺,这样才算是给新知县做成了一个临时下榻处。
这次人事变动是对调署理,李超琼来上海,王少谷去南汇。两人不但有同龄、同年、同寅之谊,而且,“交好十余年,相契至深”,是一对官场上少有的“忘形之交”。
三十多年前,李超琼第一次从长江上游的合江老家出来,经上海转轮船去京都赶考,上海沿江正在兴建的连片成带的异样建筑群曾使他觉得有些奇怪。虽然,当时上海还没有通电,轮船上、马路上、洋楼里点的还都只是汽油灯,但夜幕降临后,黄浦江左岸黑暗衬托下的华丽和璀璨,仍然足以让他倍感惊艳。“四十里中金碧炫,泝流疑到蜃楼居”,就是他当年躲在船舱里摸黑记下的诗句。
在后来的岁月里,他因公因私多次进出这座迅速成长中的既喧嚣又时尚的城市,享受过它提供的各种服务,见证了它的成长和扩张,但每次都只不过是作为一个匆匆过客。有朝一日会成为主宰这座城市的守令,是他绝对没有想过的。
年初,李超琼在省城苏州被告知将调署上海时,曾当场力辞。他反复强调,自己“才力既弱,精力亦恐不逮”,当不了上海知县。但是,苏州藩台陈启泰告诉他,这是“午帅”——两江总督端方本人的意思。
几天后,江苏巡抚陈夔龙单独召见李超琼。陈夔龙强调:务必维持上海的“和平安静”;目前已有多个国家在上海设立租界,而且有合力从我国谋取利益的趋势。作为上海知县,要妥善应对,不可意气用事。李超琼强调自己“才力本骀,精力亦衰”,再次据理力辞。但仍不见陈夔龙有半点松动。
其实,这次上海知县的人事安排,既意味着江苏省的当轴大吏们对李超琼人品、官守和处置复杂事务能力的看重,也意味着对另一个由朝廷直接委任,将在道台层级上主宰上海事务的人的人品、官守和能力的担忧。这另一个人,就是新任上海道台瑞澂。
瑞澂,姓博尔济吉特,字莘儒,文渊阁大学士琦善之孙。因为家世显赫,从小放荡不羁,纨绔成性,一向与大学士劳乃宣之子劳子乔、云贵总督岑毓英之子岑春暄共享着“京城三恶少”的称号。庚子事变中,太后、皇帝领着满朝亲贵逃往西安时,他却找借口滞留北京,事后又靠花言巧语混到了一个“留守京城”、“勤王有功”的名声。他又凭这样的政治资本,趁朝廷重用满人亲贵的机会,换到了上海道台的头衔。
此时的上海,已形成英美租界、法租界和上海县三者分割管理的局面,中外交涉纷繁复杂。上海县是中国的基层地方政府,一举一动都在脸面和利益上代表着国家。上海道,是监管上海县的江苏省派出机构,按惯例,一应对外交涉,都由它代表上海县出面,历来如此。现在,瑞澂这么个不着调的纨绔公子空降而来,如果没有一个资深的基层官员压阵,随时可能出大事。
陈夔龙先把王少谷从阳湖县调来。但是王少谷到任不久就与瑞澂发生摩擦,以致无法相处。于是就有了王、李对调署理的安排。王少谷,又名念祖,安徽太湖县人。光绪癸未科进士,曾任江苏金匮、长洲、阳湖等县知县,所到之处官声蜚然。此人与李超琼是不分彼此的挚友,又向来“视官如弃履”。他欣然乐意服从安排。南汇在黄浦之东,上海在黄浦之西,隔江相望,互为犄角,王、李两位“老基层”的紧密配合,有利于中西交汇的新兴大都市上海的稳定。
到底是京城里来的高干子弟,瑞澂初到上海,就经常对着包括李超琼、王少谷在内的下属县令高谈阔论,枉论时弊。即使连公开评点江苏省的“当枋诸公”,也毫无顾忌。
九月里,瑞澂升任江西臬台,要去南昌接印。上海道台一时出缺,临时找了个人来代理。迎接上海道代理道台的宴会,轮到在上海的皖省绅商做东。瑞澂是当然主宾之一。谁也没想到,席间,这位公子哥突然发飙,就某位州官缺席的小事,破口大骂起来,非要认为缺席官员是“以告病为托辞”,“抗不应命”,必须参劾。
座席间的衮衮诸公,多为上海滩上的大佬。其中一位叫施省之的出来说了句公道话,证明这位缺席的州官“其病非虚”。瑞澂大怒,冲着施省之大吼起来,话语中“所出多市井俚亵之词”。
施省之做过大清国驻纽约总领事、京汉铁路总办,可不是什么等闲之辈。他坚持说理,毫无惧色。一时间,两相冲突,“喧哗互起,几有动武之势”,把好端端一场华堂美宴,搅得不欢而散。
瑞澂调江西,本来就只是为混个三品臬台去走走过场。半个月不到换了副顶戴就返回上海。在上海,一个更显赫的职位——正二品的苏州藩台,正等着他去取呢。
瑞澂乘坐的江永轮停靠在码头上,众官出迎。入见之际,上下级官员见面照例都按规制行礼。排在上海知县李超琼之前的是一位直隶州同知。不知怎么回事,那位州同知一见瑞澂就按照旧规矩,屈膝跪下,五体投地,行的是跪拜礼。下一个就是李超琼,李超琼按照新规,只行揖手礼,他不慌不忙,俯身拱手,站立不跪。瑞澂“乃大不怿”,一脸的不高兴。
官员相见历来都行跪拜礼。但自从国门打开,西风东渐以来,跪拜礼在越来越多的人眼里成了野蛮落后的象征。这一年的新年到来之前,江苏就开了个风气之先,巡抚陈夔龙登报通饬全省各级官员,宣布江苏官场从此废除跪拜礼。并且明文规定:无论品级大小,初见三揖,常见一揖。请安之类一律免除。
李超琼是真心拥护这样的礼仪改革的。大年初二,大团的海防哨官江大有按照老规矩,一大早老远赶来县衙,给县太爷磕头道贺。省里已经明令禁革,但传统陋习仍旧如此难以改变,是李超琼在这个新年里最强烈的感慨。他当场严厉批评了江大有,还亲自书写楹联一对,着人在客厅里高高挂起,以表明自己的态度。联曰:
在官逾二十年,始终义命是依,讲砺名,讲要脸;见客只一两揖,彼此廉耻为重,不请安,不磕头。
他自己在各种大小公务活动中,都以身作则,率先践行省里的礼仪规定,只揖手而不跪拜。废除跪拜已经十个月,无论在南汇还是在上海,既简便又得体的揖手礼已经蔚成风气。巡抚陈夔龙倡导的礼仪改革,瑞澂又不是不知道,但这位公子就是抑制不住对李超琼的痛恨。在他看来,正是这个倔犟的四川老头,煞了他的风景。于是,即使在见面寒暄中,两人谈话也是“语必抵牾”。李超琼是下属,只是“以谨默应之”。
官运来时,真是挡都挡不住。十二月初,瑞澂真的晋升苏州藩台,正二品。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完成了道台、臬台、藩台的“三级跳”,令整个江苏官场都为之侧目。
当官当到了苏州藩台,瑞澂的纨绔劲儿发作起来,偏狭任性,暴戾恣睢,愈发变本加厉。这人视牧令不如奴隶,逞官场形同市井,把省城苏州的各个衙门都搅得人人自危。不但动辄口出秽言,诟骂僚属,还当众撕毁巡抚的饬令,更令人发指的是,他竟在公堂之上抽打州县官的耳光。只要认为需要,他还会带上戈什哈(武装卫兵),突击搜查僚属的住处,监督僚属起居。但尽管如此,这人背景太大,连督、抚两宪都拿他没办法。
李超琼远在上海,与瑞澂难得一见,也算能落得个相对清静。但有关瑞澂恶行的消息,时时从省城传来。
李超琼气愤地想:君王和臣子,历来讲究以礼相待,一个小小的藩台对下属怎能这样无礼呢!动辄以罪囚对待那些直接面对老百姓的州县官,又怎么可能让州县官代表朝廷去施政治民呢?做官的规则和职守在哪里!这样下去,我们这些州县官还有可能厕身官场吗?
当时,正好有几句政治俏皮话从京都传来:“励精图乱、发奋为雌。破格用我,下诏罪人。”说的是庚子年以来京城里的官场乱象。看来,像瑞澂这样的宝贝,不但江苏有,京城里也有,这其实也是大清国的不祥之兆。李超琼悄悄把它们记识于册,以作备忘。
看法如此强烈,李超琼当然会有所议论。而且,偶尔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也会临时充当“折冲将军”角色,通过尽量委婉的方式,去减轻瑞澂这位纨绔藩台对地方事务和具体官员的无端伤害。
有一次,他陪瑞澂在上海的码头上迎接一位过路的京城高官。轮船公司老板向藩台反映,近来公司有客船遭土匪抢劫。瑞澂不假思索,当着客人的面夸夸其谈起来:“本藩早就知道某某县的治安不好。那个什么破县令,向来老奸巨滑,只会巧言推诿。本藩跟他说了多少回了,那段河道迟早会出事……”
李超琼连忙出来圆场,而且带着说笑口气:“抢劫现场没准儿还在百里外的什么地方呢。那个破县令,即使再滑头,恐怕也不至于大老远地跑去担当治安责任呀。”
果然,再一了解,客船抢劫案发生在松江府娄县的某条河道上,离瑞澂所说的那个县相距一百四十里。
三十三年(1907)末,由于政绩卓著,上海知县李超琼和南汇知县王少谷双双被上报推荐为受朝廷表彰的年度“卓异”官员。这一年,江苏的州县官中获得此项荣誉的仅此两人。
但是新年刚过,苏州官场的朋友们纷纷来信来电,告诉他:藩台瑞大人已经对他深有嗛恨,而且“訾议之词,甚形严切”。李超琼说:“麻烦和丢脸都是他自找的,怨别人有什么用!”
有朋友劝李超琼,藩司是管干部的,不好惹,你得赶紧去“求人疏通”。李超琼说:我已经一年比一年衰老了。这把年纪还挤在卑微小官的队伍里,在别人看来,早已是个顽固愚钝,而且没脸没皮之人了。如果再委曲自己,低三下四去求人,做出什么钻营取巧的事来,授人以柄,那不就是把自己做人的最后那点尊严都丢掉的自败之道吗?(“因年衰年,犹逐队于卑官,已等于顽钝无耻之列。若委曲求人,是且自以‘巧为钻刺’四字授人以柄也,岂非自败之道。”)
报应说到就到。三十四年二月,苏州藩司挂出牌示:李超琼调任长洲知县。这条任命其实是要把已经背负严重亏累的李超琼逼上绝路。长洲县和元和县、吴县一样,同是江苏省会苏州府的三首县之一。李超琼再去做一任首县知县,无疑是雪上加霜。
八天之后,居然绝处逢生。南汇知县王少谷从省城办事回来,带来藩司衙门的一个口头通知,令李超琼“勿懈其职,无庸亟于交卸”。这意味着“调长洲”的命令将被收回。
为了这个好消息,这天晚上,李超琼拿出合江家乡名菜菽乳腊肉,与王少谷两人一醉方休。
六月底,苏州藩司不无尴尬地再次牌示,重新任命了一位长洲知县。这项重新任命,实际上是以不作解释的方式,宣布了前次对李超琼任命的作废。
关键时刻留住李超琼的,是新成立的“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发给江苏省各衙门的一封公函。在公函上签字的是上海滩上十几位最有头脸的地方士绅,为首的是李平书。
各人头上一方天。此时,公子瑞澂的官运还是好得没个完,还在继续 “小步快跑”喜滋滋地升他的官。这一次他又从“苏州藩台”跳到了“江西巡抚”。
瑞澂在沪西小沙渡置有私宅一处。他从苏州去南昌接任江西巡抚之前经过上海,就住在小沙渡。李超琼作为上海的地方主官必须按照礼节去为他送行。一连去了小沙渡五次,瑞澂竟然一概避而不见。最后时刻,李超琼赶到火车站,才算赶上一揖而别。当然不是跪拜。
在一声声汽笛长鸣中,李超琼目送着火车缓缓远去,心里反而有些失落。他实在想不明白,命运之神会载着这位有点可笑的幸运儿驶向何方。
宣统元年(1909)瑞澂再回江苏时,已经由“江西巡抚”改任“江苏巡抚”了。从江西巡抚到江苏巡抚,一样的巡抚,含金量哪能同日而语。说起来是量移平调,其实是平步青云的一大步。宣统二年(1910),瑞澂又有了大进步,这回是当上湖广总督,成了一品大员。
历史的幽默,常常出乎人的想象。它似乎是有意要让这位平步青云、蛮横跋扈的纨绔公子去亲手点燃那把葬送整个清王朝的熊熊烈火。
宣统三年(1911)八月,博尔济吉特·瑞澂因为没能深入领会朝廷的意图,在武昌追捕革命党人过于疯狂。十八日午夜,又在盛怒之下处死了三个疑犯。正是此举,促使湖北新军工程八营的一名士兵扣动扳机,打响了中国人民推翻千年封建王朝的第一枪。
当武昌城里枪声大作时,瑞澂跳上军舰,弃城而逃。此公从此亡命天涯,直到窝窝囊囊老死在上海。[注]
[注]以上未加注释或说明的情节和引文,均出自李超琼《石船居在官日记》稿本,苏州工业园区档案馆馆藏。
长夜如磐
光绪三十四年(1908)四月初,李超琼、王少谷等知县共同去苏州谒见江苏巡抚陈夔龙。谈话中,李超琼有“牧令之难,至今而极”之议,说的确实是一番肺腑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