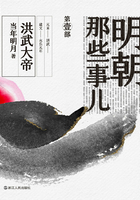根据康有为的表述,梁启超几年前曾在上海创设一份《时务报》,这份报纸参照东西洋各国报章体例,议论明达,翻译详明。其中论说皆切合实际,参酌中西,所提方案大体合理可行。所译东西洋各国报刊,其言兵制,言学校,言农矿,言工商等各政,条理粲然,足备参考。这份刊物经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山西巡抚胡聘之、湖南巡抚陈宝箴、浙江巡抚廖寿丰、安徽巡抚邓华熙、江苏学政龙湛霖、贵州学政严修、江西布政使翁曾桂等地方大员全力支持,在全国已有广泛影响,为国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舆论阵地。这个说法大体不差,合乎事实。
然而奏折中接着建议,过去两年,民风大开,通达时务的士大夫也越来越多。大家比较公认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效果,主要是因为《时务报》鼓吹宣传的结果。鉴于此,奏折建议朝廷将《时务报》收归官办,由政府出资收购报馆中的商业股份,国进民退,使之改造成政府系统的舆论工具。这个建议从原则上说并无大错,只是鉴于梁启超、黄遵宪与汪康年相互纠葛、相互冲突的事实,这个建议就显得有点不合理、不厚道,有点仗势欺人的意思了。
康有为起草的这个奏折建议政府收购、接管《时务报》,除了上述理由外,还与《时务报》最近期的情形有关。奏折说,这份刊物几年来一直办得不错,只是自去年九月梁启超应湖南巡抚陈宝箴聘请,出任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之后,未遑兼顾,再加上报馆中办事人办理不善,致使《时务报》效益大幅度下滑,经费不继,主笔告退,刊物或将停刊,果真如此,实在可惜。按照这个意思,《时务报》有点办不下去了,由政府接盘,只是拯救了这个刊物,保住了一个品牌,然后再利用这个品牌扩大影响,宣传新政。这个说法合乎逻辑,但不合乎事实。《时务报》在梁启超离开之后效益是有所下降,但无论如何,也没有达到破产的程度。汪康年正在办得有滋有味。
我们知道,梁启超本来在半个月前(7月3日)已奉诏筹办译书局,而且也办得有滋有味,自得其乐。现在再建议他接管《时务报》,梁启超能够忙得过来吗?这个担心,在康有为(其实可能就是梁启超本人)看来小菜一碟,而且两个项目加在一起,相互配合,相得益彰,一点都不冲突。奏折说,译书与译报,事本一贯,其关系之重,二者可容偏畸;其措办之力,一身似可兼任。
由此,康有为借宋伯鲁之口建议朝廷明降谕旨:一是将上海《时务报》改为《时务官报》;一是委派梁启超督同向来主笔人等实力办理。并建议将改组后的《时务官报》移至京师,并入译书局,再依译书局之例,在上海设立《时务官报》分局。这样,梁启超在主管译书局的同时主管《时务官报》,并随时往来京沪两地,总持其事。康有为还建议朝廷明谕各省督抚支持《时务官报》出版发行,一如《时务报》旧例,最好由各省公费订阅,扩大发行。这确实是维新运动中一批最合算的买卖。
在这份奏折中,康有为还利令智昏地荒唐建议朝廷将民间所有报刊一律收归国有,彻底实行国进民退,所有报刊等传媒,均由政府主办,统一舆论。康有为的理由是,各省民间通过商业招股设立的报馆,言论或有可观,但体律似乎并非尽善,且间有议论悖谬,记载不实者,因此他建议此后民间所有报刊在出版后都应该先送官报局,责令梁启超悉心稽核,认真审查,然后选择精善内容进呈,以备圣览。至于各地报章杂志中悖谬不实之处,当然也应由梁启超主持的官报局进行纠禁。
不难看出,不论康有为这一建议的真实目的是什么,这一建议实际上必然导致新的文化专制主义,使过去数年刚刚形成的民间社会与民间舆论趋于消散,这势必导致维新势力的急剧分化。
清廷收到这份奏折后并没有立刻接受,而是转发给管学大臣孙家鼐酌核奏明,妥议办理。
孙家鼐此时正为京师大学堂章程中总教习权限问题与康有为、梁启超闹气,所以他在得到朝廷指示后,并没有很快回奏处理结果。在他等待和调查研究的那些日子里,可以想象肯定会有不同方面向他施加各种各样的影响。7月26日,孙家鼐向朝廷提交了处理意见:
一、不同意调梁启超兼办《时务官报》。理由是梁启超已奉旨办理译书局事务,现在学堂筹备已经进入非常阶段,招生开学在即,急需教材,译书局在这方面负有繁重责任,必须尽早编写教材,以供大学堂和全国各地各级学堂青年学子使用。如果调梁启超兼办官报,恐其分散精力,不利于译书局的工作。
二、建议调康有为督办官报。但对改为官报后的《时务报》,孙家鼐在这里提出比较严格的管理建议:一是先前的《时务报》虽有可取,而庞杂猥琐之谈、夸诞虚诬之语,实所不免。现在既然遵旨改为官报,就应该责令主笔者慎加选择,如有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挟嫌妄议、渎乱宸听者,一经查出,主笔者不得辞其咎;二是《时务官报》既为政府主办的报纸,就不能像民间报纸那样自由议论,应该规定该报不得议论时政,不准臧否人物,其主要功能就是翻译外国报章杂志上有用文章,以便阅读者略知各国情形;三是《时务官报》的经费,孙家鼐建议主要应该由该报自筹及其发行所得,按照市场化原则自负盈亏,政府不必也不应该强行要求各省督抚公费订阅或摊派。至于开办之初的部分经费,孙家鼐表示可以考虑由上海道代为设法,但应由康有为自往筹商,自己担保。
三、对于宋伯鲁原奏中提出的将各地民间报纸一律送官报局审查的建议,孙家鼐提出反驳,以为人君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近代西方报馆林立,人人阅报,其报能上达于君主,亦不问可知。现在《时务报》改为官报,仅一处官报得以进呈,尚恐见闻不广,以偏概全,偏听偏信,不利于朝廷的决策。其实,最近几年天津、上海、湖北、广东等地都创办了许多报馆,有些报馆在质量上言论尺度和社会影响上也并不比《时务报》差或小,因此孙家鼐建议朝廷谕令各省督抚将辖区内各处报馆的样刊样报,均应呈送都察院、大学堂各一份,然后由都察院、大学堂择其有关时事有参考价值而无甚悖谬者,录呈御览,以期使朝廷使圣上兼听则明,统揽全局。应该说,孙家鼐的这一反建议不仅封杀了康有为企图垄断舆论的计划,而且具有更多的近代意识。
当然,如果仅仅从孙家鼐与康有为的私人关系说,孙家鼐的这些处理意见确实蕴涵着许多阴谋,但是这些阴谋通情达理,公事公办,在表面上无可挑剔,于是朝廷当天就批准了这个建议,以为报馆之设是为了宣国是而达民情,当然应该由政府倡导、由政府出资和管理,因此按照孙家鼐的报告,将《时务报》改为官报,派康有为督办其事,所出之报随时呈进。其天津、上海、湖北、广东等处报馆,凡有报单,均应由该省督抚咨送都察院及大学堂各一份,择其有关时事者,由大学堂一律呈览。至于全国各地报章杂志,自应不断总结经验,分析利弊,以开拓国人见闻为主,对于中外时事均应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不夸大、不隐恶、不丑化,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不要辜负朝廷明目达聪、勤求治理之至意。至于《时务官报》筹办初期的经费问题,朝廷同意孙家鼐的规划,先由上海道帮助解决,由康有为自行前往榷商。
康有为原本准备为其大弟子梁启超谋得一个丰厚实职,却不料被更精明的孙家鼐反制算计。更令康有为想不到的是,孙家鼐的调虎离山计,其主要目的就是将康有为赶出朝廷,赶出北京。
从康有为本意说,他一直替梁启超觉得有点冤枉、有点亏,大清王朝历史上罕见的布衣见皇上,竟然只给了一个六品衔的译书局主管。这不是破格,而是连格都没到。
事情既然这样了,康有为也毫无办法,他曾多次想方设法为大弟子改善地位、改善环境,毕竟梁启超是他最得力的助手和最忠诚的信徒。无奈康有为这批政治新锐锋芒太露,在京城受到官僚士大夫阶层的普遍敌视,除了那几个郁郁不得志的言官御史外,并没有多少官僚愿意与这批政治新锐过分密切。
懊丧之余,梁启超多次想过离开北京南下上海或广州继续办报,他似乎觉得自己的能力可能还是在文化学术方面,而不是政治。另一方面,梁启超通过康有为的笔,执意要夺回《时务报》,可能与其心结有关,毕竟他与汪康年关系日趋恶化,汪康年越来越风光,而梁启超先前的贡献几乎被汪康年一笔抹杀。这不能不使梁启超负气而为。
为了挽回对《时务报》的影响力,为了证明自己曾经是《时务报》的功臣,似乎也是为了弥补那个六品卿衔的不足,梁启超通过其师借助于政府压力迫使汪康年就范、屈服。
梁启超的这些想法都曾向康有为表示过,康有为也曾托人致函汪康年,劝说他知足常乐,最好将《时务报》总经理一职让给梁启超,并称梁启超刚获得皇上召见,新蒙宠眷。如果由梁启超接任总经理,可使《时务报》声价跃起,发行量猛增,效益大幅度提升,必将彻底改善经济状况,重现辉煌。
康有为的建议当然被汪康年所拒绝,没有丝毫可以讨论的余地。而且,谁也想不到的是,康有为原本在梁启超的请求下,通过宋伯鲁上了一个奏折,为梁启超谋个兼差,可是竟然被孙家鼐顺手反制,成了驱赶康有为出京城的调虎离山计。康有为无法改变孙家鼐的建议,更无法改变朝廷御旨,他只好将计就计,致电汪康年,表示自己奉旨办报,但并不准备很快前往上海接手,一切依旧,望相助。大约有点糊弄汪康年的意思。
7月26日,康有为致函汪康年,详细解释自己不得不接手官报局的苦衷或无奈,但他将这个故事的前因后果作了几乎完全相反的解释。他暗示,过去的一个多月,在他的努力下,新政络绎,使人蹈厉。现在忽然接到上谕,命我康有为前往上海督办官报,这确实有点出乎我的预料。不过,仔细想来,这大概是那些大臣相爱相助,担心我喜事太甚,不够沉稳,故意将我放到外面接受锻炼,以敛其气。过去朱熹曾感叹其“立朝四十日”,而今我康有为竟然与此相似。天恩高厚,感激靡尽。康有为将一个原本失意的故事作了完全相反的解释。这显然是要汪康年相信自己在朝中的能力,乖乖交出你的《时务报》吧!省得大家伤和气。
关于《时务报》的创刊及演变,康有为是非常清楚的,他知道这份刊物是汪康年、黄遵宪、梁启超三人为主,还有其他一些朋友参与一起创办的,而自己连年在粤,一无所助。他在信中告诉汪康年,现在既然受朝廷信任,奉命接手,那也没有办法,不过他个人还是期待一仍其旧,馆中诸事仍望康年兄等相助为理,凡百皆拟仍旧。这是一个友好的暗示,当然也可以看做是一个警告:假如你汪康年不能合作,那我康有为肯定会换人的。
这封信的主旨主要还是着眼于交接,康有为告诉汪康年,想必报馆中存款不会很多了,现在既然改为官报,由政府出面出资举办,那么也就不能再收捐款,而官款也不是很快就能够获得,所以他告诫汪康年,在他到任之前这段时间,各项开支不能不稍作控制和节省,尤其是各项薪水,更不能如过去那样大手大脚。他甚至通知汪康年,让他准备好账单,以便将来复查。
信的最后,康有为挑明他知道其弟子梁启超与康年兄曾小有意见,但他坦然表示,这些小小的意见不应该影响我辈同舟共济,成就盛世伟业,不必在这点小事上太用心思,更不必记仇。他顺带告诉汪康年,因为他还有一些进呈书籍尚未告成,大约还须在北京逗留十天左右,他或许会奏派一二人先行前往上海与康年兄接洽交接事宜。这些问题一旦决定,一定会尽早告知。
康有为一系列分析和说辞并没有影响汪康年的判断,汪康年并没有被康有为糊弄得不知东西。他在京城的朋友早就告诉他康有为等人在那里的真实处境,而康有为刻意而不经意的描绘,反而证实那些朋友消息的真实性、准确性。汪康年知道,康有为此时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夺回《时务报》控制权,所谓同舟共济云云,不过是要表明他康有为虽奉旨接收《时务报》,但依然是为梁启超谋一个出路,所以他期待汪康年与梁启超的配合与通融。
无奈汪康年根本不吃康有为这一套,他从纯粹商业的立场上回敬康有为。汪康年表示,鄙人汪康年才是《时务报》创办人,梁启超不过是我聘用的一个主笔而已。不论梁启超今天的名气有多大,他得以荣显、得以崭露头角、得以执当今中国舆论之牛耳,其实都是因为我当年聘请他到《时务报》主笔。梁启超不知感恩也就罢了,为什么还要反客为主,将自己打扮成《时务报》的创办人呢?种种迹象表明,康有为改《时务报》为官报,并利用行政权力任命梁启超兼职主持,与其说是康有为本人的建议,毋宁说正是梁启超所期待的,或者干脆就是梁启超的建议与想法。
不料,孙家鼐的智慧打破了康、梁的梦想,而孙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反建议,也实在是出于康、梁尤其是康有为在当时官场上不太遵守游戏规则、人际关系急剧恶化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