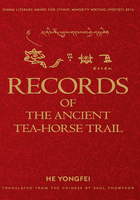时过三天,带着香气扑鼻的一钵乳白色的醪糟,就呈现在我们的眼前!钵的中心井中汁水清澈,米粒可数。大指拇和食指并拢蘸一点汁水,十分黏稠,慢慢张开,俩手指间会牵出一线像饴糖般的晶亮细絲来。糟体与汁水分明,犹如新酿的蜂蜜漂浮在汁水中。倘若轻轻拍一下瓦钵,醪糟若浑然不动,则算失败;倘若醪糟在钵内中自由转动,毋须品尝,从外形上就可猜测已属上乘。我猜,这大抵就是“拍醪糟”这“拍”字的特殊含义。
醪糟吃法多种,亦可直接食用。酷暑的夏季,当时市面没有冰淇淋、冰糕之类的冷饮,一两勺醪糟加上井里的凉水,又甜又凉,喝上一碗,嘴角一抹,解渴沁脾,舒服极了。家乡的人十分好客,逢上远道的亲戚或朋友临门,绝非斟一杯老荫茶就能表达主人的盛情,必烧一碗甜香扑鼻的鸡蛋醪糟端到客人跟前,才能表达主人的盛情。如备有糯米汤圆,烧一碗醪糟小汤圆,更是别有风味,清甜香糯,绵软滋润的感受,在口里久留不散,给人难以想象的惬意。遇上哪家的媳妇坐月子,当婆婆的必然要拍醪糟,每天煮上一碗,加一两个鸡蛋,再放点红糖,催奶颇见功效。家乡俗语说,产妇发奶有三宝,母鸡猪脚不如醪糟好。所以,有的家媳妇坐月子期间,拍几钵醪糟是常事。受朋友之托,我的母亲就帮助邻居拍过好几次。
我从小就喜欢吃醪糟,尤其是生吃。一次,趁母亲不在家,就偷偷用调羹尝新,甜在口里,再尝,蜜在心中,无法化开,自然,怎么也舍不得放下手中调羹。就这样,一钵刚出窝的醪糟,不花多少时间,就被我削掉一半的体积。过了十多分钟,母亲回家,发现我脸胀得通红,醉意朦胧,一语道破:“嘴馋,偷吃了醪糟吧?”
我佩服母亲眼光,谙熟醪糟蕴含的酒力,一眼就看出破绽。我的脸“唰”一下就红到脖子上,承认无法摆脱醪糟的诱惑,实说了偷吃的经过。
母亲开导我:“醪糟好吃,也醉人啊!世上许多好吃的东西,也像醪糟一样,不能多吃。吃多了,也要坏身体的。”
我一直把母亲这简约而富于哲理的话语铭记于心,吃东西,做事情,不温不火,力求把握中庸之道。对于儒家文化,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女性,目不识丁,若没有丰富实际感受,无论怎样都无法破解生活哲学中的子丑寅卯。只有借助时光的透镜,长期观察思考,才能集聚明晰的智慧光束,透析儒家文化中庸之道的精髓来。
殷实人家,做菜时,也离不开醪糟。做红烧肉时放少许醪糟调味,肉色红亮,肥而不腻,鲜美醇厚,是招待贵客的上等佳肴;以醪糟和番茄汁为主调料烹制的香糟炸鲫鱼,焦香酥脆,酸甜可口,是川菜中的一道名菜。不过烧制这道名菜的技艺,我们家里从没动过手——因为以前从未购买过鲫鱼——那些烹调技艺是我后来才知晓的。
在家乡的县城,醪糟店遍布大衢小巷。醪糟鸡蛋,醪糟小汤圆,冰水醪糟,拍醪糟用酒曲,用大小不同的陶瓷罐装新鲜醪糟,恐怕这是许多县城不曾出现的热闹景观。醪糟店焼醪糟是用带柄的铜锅。金黄的铜锅里,乳白的醪糟汤中,漂浮一个黄橙橙的鸡蛋,香甜芬芳。别说吃,看上几眼也够养眼。我读小学时,进校要路过好几家醪糟店,狠狠吸上几口飘来的甜香,惹得嘴里一天都是甜丝丝的,上课时,特别有精神。
后来到成都,那里也有醪糟汤圆叫卖。一见醪糟汤圆,家乡情感油然而生,也就叫了一碗。老板煮醪糟汤圆居然还要放上少许白糖,我觉得莫明奇妙。再尝上几口,又粉又淡,居然略带酸味,全然没有一点母亲制作的醪糟的味道。
五十年代末,糯米供应减少许多,家里米罐里就没有糯米了。本来猪肉就少,如果连醪糟都不拍,那年过得就更是平淡无味——母亲总是在非常清贫的家境下,把过年安排得有滋有味的。我以疑虑的眼神,凝视母亲的操作。她把用来做饭的大米量出半升,淘洗干净,蒸得恰当好处——母亲说,不能熟透,否则,拍的醪糟就要“烂糟”。她加上多于糯米一倍酒曲,拌匀后放入拍醪糟的窝内。过后三天,一小钵浓郁香甜的醪糟照样出窝了。有了醪糟,我们简朴的春节,终于又有浓浓的年味了。
醪糟生性娇嫩,颇似富贵人家深居闺阁的小姐,遇上天气转热,伺候不周,极易变脸,从醪糟转化为泛酸的米酒,不断溢出阵阵刺鼻的酒味。有钱人家遇到这家伙“不守贞节”,嫌弃丧失早先的纯洁,顺手就倒进潲桶,担心它在橱柜里串味,坏了别的饭菜。
我们家也遇到过这样事情,不过母亲倒这样告诫我:“用米拍出的醪糟,是粮食的精华,倒掉就太可惜了,我来想想办法吧。”她在烧开醪糟后,加上丁点小苏打,醪糟汤顿时冒起一团白色泡沫,酒味一会混着气泡飘散殆尽。再尝,风味依旧。我抚摸母亲的粗糙的手,高兴得跳起来,赞不绝口:“妈妈,你真能干!”
现在,家乡的醪糟早已是集约化大生产了,一出窝,就是成百上千瓦罐,又用易拉罐封装,贴上华丽花哨包装,名称大得吓人,在醪糟的前面冠之“东汉西汉”“霸王皇朝”的头衔,横空出世,傲视天下群臣,摆出世上醪糟天皇非我莫属雄姿。“春风得意马蹄急,一日看尽长安花”,出门就是坐飞机,乘火车,阔气要命,风光无限,最后堂而皇之在众多大型超市橱窗里显赫亮相。我尝了尝,远没有母亲拍的醪糟那种风味。
任绵长岁月流淌,始终无法冲刷对母亲深深的怀念,也难以卷走母亲制作醪糟的神奇韵味。
入夜,读书困顿之时,我常取案几上香茗或咖啡提神解乏,虽然芳香四溢,但远没有母亲用瓦钵拍的醪糟那样温馨,鲜润舒心,醇香醉人。
母亲留下一首歌
我的母亲是一个道地的文盲,认不得字,好在凭借自己聪颖和勤快,还学会手工缝制衣服的手艺。父亲去世很早,家里就靠母亲这门手艺,在一个小县城张罗,勉强维持全家的生活。
五十年代时兴男性着对襟和长衫,女性穿半衫,这样的成衣必须靠手工活才能完成。无论是对襟长衫还是半衫都需要盘扣、钉扣和挑边这三道工序。 盘扣是一门很讲究工艺的细活。母亲盘的布扣既紧凑,又匀称;钉的布扣既结实,又漂亮;挑衣边和袖口的针脚细密整齐,很让人喜欢,能在几家缝纫店揽到活计。为着生计,母亲又学习了剪裁,使用缝纫机。剪裁这些活计对于一个文盲来说,不识字,更不会计算,到底会带来多少困难,我们现在已经无法想象了。但母亲终究靠死记硬背,“转型成功”,她和几个街坊组成了一个小小缝纫店,也能制作一些诸如干部服、中山服、列宁服这样的时髦服装了。
在看母亲制作的时候,我耳濡目染,也懂得一点滴做衣服的常识。但母亲毕竟不会计算尺寸,学习新的款式受到许多限制,被人请去缝衣的机会毕竟不多。母亲经常告诫我:“孩子,你看,我认不得字,想学点新东西都没有办法,挣点钱多难呀!你要努力学习,将来才找个好饭碗哦。”我默默点头,从母亲朴素的话语中依稀懂得,知识与个人的命运密切相关,这辈子就得好好学习。
我从小喜爱读书,没钱买书,常向同学借。在仔细翻阅课本,连封底出版印刷信息一字不漏地读完后,每天在学校的最大快乐就是到图书馆读书看报,又及时又方便。我与管图书的老师混熟了,居然能享受钻进书架浏览的“特权”。无论寒来暑往的漫长假期,还是烧火做饭的点滴闲暇,总有一本好书相伴在身。干活间歇,贪婪读几行是种快乐;有宽裕时间仔细品味,更是无限享受。只要一读书,就把冻馁和叮咬的蚊虫忘得一干二净。
渐渐地,我在后来的学习和工作中,养成了一种习惯——无论何时何地,从不肯把大把大把的时间,当作糟蹋生命的葬品恣意消磨。以至于我那笨拙的思维方式延续至今,面临麻将娱乐风靡社会每个角落的现状,仍显得非常木讷。我无法明白,这样的游戏于朋友,于自己的生活和感情到底有多少价值。
母亲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她十来岁就开始缠脚,一双健康的大脚缠成三寸金莲。她脚趾完全变形,除大脚趾能伸直外,其余四个脚趾完全卷向脚掌,形成一个短小的三角形,走起路来一颠一簸,极不平稳。几十年劳累,胼手胝足,畸形的脚掌常生茧子和鸡眼,她不得不经常修剪,以便走起路来减少一些疼痛和颠簸,当然还得照样承担各种繁重家务。她经常背上一大背篼衣物,颠颠簸簸,去两里外的小河边,跪在石板上搓洗,也舍不得花一分钱,买担自来水坐在家里洗濯。她常常是洗完回家,天才开始发亮,碰上“好运”临头,还略有“收获”——把那些菜农在河边洗菜时扔掉的白菜老叶子、莲藕肠子捡回家,聊补无钱买菜之需。
母亲进菜市买菜总是精打细算,一分钱掰着几分钱花,常常是几分钱就买回一竹篮“罢市菜”,够吃上好几天。虽没有赶时令尝鲜的福分,我也知足常乐,不觉遗憾——能有菜吃总比强吞“白饭”好得多。母亲巧手腌制的咸菜和胡豆酱,也常是就饭的“主打菜”,即使没有蔬菜上桌,我照样能吃上几碗饭。两三个月里不知肉味,那是常事。除了买回米、盐最基本的必需品外,几乎从不敢奢望买点酱油、麸醋之类的调味品。我常吃母亲烹制的“白锅闹”(没有放油的炒菜),也照样觉得津津有味。
我早先经常赤脚,很少穿布鞋。上小学时从没穿过胶鞋,逢上雨天,就穿母亲特制的一种叫“鞋爪”的防滑雨鞋。这种布鞋鞋底厚实,鞋面抹上桐油和猪血,钉有防滑的铁钉,走路时会发出“砰砰”的响声。雨天上学读书时,许多同学都穿上时新的胶鞋,而我穿的这种鞋爪既笨重,噪声又特别大。有的同学常取笑我:“将军驾到!”这种揶揄一度令我非常羞愧,但我从不埋怨母亲,只是把这种嘲笑咽在肚里,暗自激励自己,排除闲言蜚语,走自己的路,努力读书吧。
在我的记忆中,过年极少穿上新添的衣服。挑选没有补丁的衣服洗干净后,聊当新衣,能穿上一双新作的布鞋,沾上一点过年“新”的喜气,就很不错了。
我穿的衣服,多年都是母亲用白布漂染而缝制的。母亲说,这样的衣服既耐穿,又省钱。穿着母亲自己用染色布制作的衣服,我读完了高中。
后来,母亲身体愈加衰弱,体重仅七十余斤,连脚踏缝纫机都乏力了,只好改做些针线活来维持生计。母亲几乎每天早上5点起床,从白天一直忙到深夜,鸡叫头遍,贪睡的我醒来时,还能望见清冷的灯光下母亲晃动的身影。她常自言自语:“深夜做活,没人打扰,比白天还强呢!”为此,她专门制定了夜间工作时间表:一双袜垫扎好后才能“按时收工”。想到一个夜晚的辛苦劳作,又能买回一斤大米时,母亲瘦削的脸颊顿时会露出一丝微笑。
晚上做针线活时,她总是把桐油灯芯捻得最小——只留一根灯草浸在灯盏里;后来改用煤油,也是把灯芯拧得细细的再用。
“纺织娘,没衣裳”,这句古老童谣描写的窘况与母亲的现状何其相似!身为裁缝的母亲,除了唯一一件面衣布料稍好些外,其余衣服几乎全是“和尚衣”,不知穿过多少年,上面补丁一层盖过一层,几乎找不出早先的原色布料了。
每逢开学前交纳学费,最难煎熬,如过年关。五六元的学费要从几个月前就开始筹措:要么翻箱倒柜,寻找能典当的旧衣,要么向夜晚要时间,加班扎袜垫攒钱,向自己生命的极限挑战。
记得,有一年开学时东拼西凑,仍差3元学费,想跟邻居周转,上次所借2元尚未归还,实在难于启齿,母亲只好痛下决心,把一件在箱底珍藏多年的阴丹蓝布半衫——唯一一件出嫁时穿过的嫁妆——找出来,典当了3元,总算凑齐了学费。
读中小学的十二年间,我家经济非常拮据,但从没有因缺钱而辍学耽误一天,也更没有申请过一次助学金和困难补助,因而自感慰藉。
对那些家境比我们优越若干倍,靠说假话,出具假证明,骗取学校减免学杂费和享受助学金的同学,我一直困感不解,曾问过母亲:“这是为什么?”
母亲淡淡地回答:“花有几样红,人有人不同。别管人家,我们做人要诚实,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你还是认真读书吧。”
母亲对人厚道,邻里街坊向我们找个针头线脑或用缝纫机打个补丁什么的,母亲从未拒绝,所以,她的人缘极好。但母亲总对我说:“不要随便向人家伸手,穷,也要有志气,要学会自己想法解决问题。”对别人的友善和对自己的严格,母亲总是和谐地融两者性格于一身,正体现了一个生活在社会最低层劳动女性的伟大的人格!
在不堪回首的六十年代初期,饿殍遍野,朝不保夕,母亲提着竹篮,拄着拐杖,挪动浮肿的双腿,甚至手脚并用,吃力地爬坡上坎,四处寻觅可以填充肠胃空间的野菜和“代食品”, 以缓解因长期饥饿造成身体极度虚弱的剧烈反应。母亲偶能捡些地菠菜、马齿苋、苎麻篼、芭蕉根回家果腹,如能刨到荒地里的一两块红苕或洋芋,那就太幸运了。我们有时连一点蔬菜咸菜都没有,就用丁点菜油炒盐拌饭。
数月不知肉味时常有的事情,常馋得心慌。听旁人说,老鼠肉也可食用。我们就用“砸板”捕得老鼠,剥皮挖去内脏洗净,加上一个酸萝卜烹制,还做出香气扑鼻小炒,我鼓足勇气将鼠肉送入口中,咀嚼起来还抵得上猪瘦肉口感。吃上几次这样的鼠肉,多少能消除一些心慌气短的恐惧。
我在一次乡下挖塘的劳动中,挖得一条黄鳝带回家。母亲高兴地说:“这样的黄鳝不剔骨和肠,熬汤最滋补身体。”她狠心地放了几滴油在锅里,熬了大碗汤,白白的,香香的,十分诱人。我和母亲喝上这碗汤,算做打了一次“牙祭”。那顿饭的情景,仿佛至今还历历在目。
母亲常念一句口头禅:“吃个虱子留只脚。”她老人家若有丁点可吃的东西,哪怕是邻里送的几粒水果糖或几块饼干,总是先舍不得尝尝,必要用一块小布包好。她故意说自己牙齿已经脱落,没法咀嚼,专给我留下。我每天晚自习结束回家,母亲总要把她仅有的2两米饭留出近乎一半,加上一碟水煮牛皮菜或青菜从街道食堂带回家,温在锅里,用来滋补我十分孱弱的躯体。
街坊邻里常关切地提醒:“你是老年人,也需要吃呀!”她只是笑着回答:“孩子在校读书,那么辛苦,他身体又那么瘦弱,不多吃点,怎么读得下去呢?”
母亲饥饿难耐,只是吞口水下肚,明知在世间生命时间十分有限,无力回天,却偏把生的希望留给了我。在我的身上,人类伟大的母爱得到最大限度的释放!我当时十分幼稚,竟然每次天真咽下母亲藉以维持生命的丁点食物,现在回忆起往事,我真悔恨自己儿时的无知。
抚摩母亲枯槁般的手脚,凝视她憔悴的面容,我不解询问:“妈,为什么我们的命运这样痛苦?”母亲潸然泪下,无言以对,只是把我紧紧搂在她的身边。
在母亲生命垂危,即将诀别人世的时候,她唯一的愿望是想喝一口鸡汤。此时家里一贫如洗,一件稍微有价值的家具和衣服都已卖掉换米,哪里找钱去买一只鸡呢?实在无法满足母亲临终的夙愿,这让我遗憾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