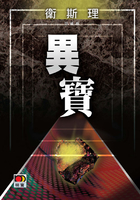第七卷 三、钟
自从那天早上受刑以后,邻居全都感觉到了,卡西莫多对敲钟的热情已经大大降温了。而在这以前,钟声会不时地回响,不息的晨钟会从初课一直持续到终课。有时是为了弥撒而敲,有时为了婚礼或者洗礼而鸣钟,那多姿的乐符在群钟之间来回奔走。这些钟声在半空中交织在一起,就像一幅用千万个迷人音符织成的云锦一样美丽。那古老的大教堂在钟声中不停地抖动,在轰鸣,好像沉浸在钟声的无比快乐之中。人们会不时感觉到有一个吵闹而无所不在的精灵的存在,而且借助于这些铜做的嘴巴在高歌。而现在呢?这个灵魂好像消失了一样,整个教堂显得有点死气沉沉的,而且是心甘情愿地保持沉默。
节日和葬礼的钟声十分简单,而且干巴巴,光秃秃的,只不过是一些礼仪上的应付,仅此而已。整个教堂有两种声音,在里面传来了管风琴声,而外面又有钟声,但是现在整个圣母院只有管风琴这一种声音了,好像钟楼里再也没有钟乐师了一样。其实,卡西莫多还在。可他究竟怎么了呢?莫非他依然对那天在耻辱上的感受的羞辱和绝望耿耿于怀,或者是行刑吏那“啪、啪”的鞭笞声还一直在他耳边回响,抑或是他所遭遇的一场已经熄灭了他心中所期待和拥有的一切,甚至也包括他对钟的热爱。或者是大钟玛丽在这个丑陋的敲钟人的心中已经遇上了一个劲敌,也是情敌,他为了那个更可爱,更美丽的人而冷落了所钟爱的大钟和他的第十四个妹妹?
在那个美丽的一四八二年,而天使报喜节恰逢三月二十五日星期二。这天,空气清新,还有丝丝微风,卡西莫多对他那些钟的爱好像恢复了一点点。于是他又爬上了北钟楼。同时,教堂执事已在下面把教堂所有的门都打开了。那个年代,圣母院的门都是用十分结实的木料做成的,用皮革做面,四周是用镶金的钉子做成的,外面还有分外好看的雕刻。
来到顶楼的钟屋之后,卡西莫多在那里注视了那几口钟一会儿,忧郁地摇了摇头,好像是在为某个不认识的东西而呻吟,而这种东西却在心中把他与这些钟隔开了。忽然,他把所有的钟都摇晃起来,他感到所有的音符在他的指中跳来跳去,当音乐之魔——这摇晃的金光闪闪的匣子,释放出的密楼的和应,颤音、琶音的精灵——一把抓住可怜的聋子,他顿时变得快活起来。他好像忘了一切,忽然他心花怒放,红光满面了。
他走过来走过去,拍着自己的手,从一根绳子跑向另外一根绳子,他用手势和声音为这些歌声加油,好像一位普通的乐队指挥在鼓励技艺高超的乐师。
他喊着:“快呀,加布里埃,快干呀!把你的全部声音都释放出来,泄向广场吧!今天可是个节日呀!”“蒂博,你又要偷懒!你慢了好多。快!加油!你生锈了吗?小懒虫!”“好,就是这个样子。快干!快得让人看不到钟舌。把人们的耳朵全都给我震聋,跟我一样什么也听不见。就这么干,蒂博,干得好!”“吉约姆!吉约姆!你可是最大的,而巴斯吉埃却是最小的,但他却比你声音大。我敢保证别人肯定是先听到它,而不是你。”“好!好!我的加布里埃,大声点!再响一点!”“嘿!你们两只麻雀在上面干什么呢?我可看不出你们有半点声息。”“怎么回事?你们好像不是在唱歌,而是在打哈欠。好了,你们干吧!今天可是天使报喜节呀!看,今天的太阳好美呀!这需要好听的钟声相配才好呢!”“可怜的吉约姆,看看你,都快喘不过气来了,我的胖伙计!”
他为了激励那些钟而忙得团团转,那六口钟也在争先恐后地响个不停,把它们那油光光的屁股摆个不停,就像一匹匹西班牙骡子,不停地被骡夫赶着,吆喝着。
忽然,在钟楼陡峭的高墙某个地方,透过护墙高大的石板瓦瓦缝,他看到了广场,却只看见一个衣着古怪的姑娘在那里,在地上铺了一块地毯。上面站着一只小山羊,外面围着一圈观众。看见此情此景,卡西莫多立刻改变了主意,他对音乐的热情马上凝固了,就像是在风中吹得熔化了的松脂。他马上停住敲钟,背过身去,蹲在石板遮檐下,双眼直视那个跳舞的姑娘,眼中充满柔情,但又好像是在思索、沉思。他的这种神情让副主教大大吃了一惊。这时,那些被人遗忘的钟也同时熄灭,让那些爱听钟声的人大失所望。这些人经常在钱币兑换桥上停留下来倾听钟乐,而现在也只好悻悻离去,好像一只被人家用骨头吸引来的狗一样,然后又被扔了一块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