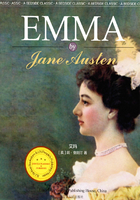第六卷 三、一块玉米发酵饼的故事 (3)
肥夫人乌达德生性多愁,她原来很想陪玛耶特感叹个没完。但生性好奇的瑞韦丝问题极多:“那怪物在哪儿?”她又问玛耶特。
“哪个怪物?”玛耶特反问道。
“巫婆们作为小女孩的交换品放在香特弗娄梨家的那个埃及小怪胎?他下场如何?把他淹死倒干净了。”
“没有。”玛耶特回答。
“什么,难道是烧死了?不过,对付巫婆的后代,这样更妙!”
“瑞韦丝,他既没被淹死,也没被烧死。大主教大人很关心他,给他避邪,赐他幸福,很谨慎地赶走他身上的魔鬼,又送他到巴黎,作为弃婴把他放到圣母院门口的木床上。”
“这些主教!”瑞韦丝咕哝,“就因为他们有学问,做事就奇怪。乌达德,我想问您,怎么能把魔鬼做为弃婴给人养呢?那小怪物定是魔鬼。——算了,玛耶特,他到巴黎后情况如何?恐怕没有什么愿意要他的善人。”
“不清楚。”兰斯女人说,“正在这时,我丈夫买了贝鲁的公证人一职,恰好距城两法里。从此我们不再管这事,并且贝鲁前边有塞尔奈的两座土山挡着,都看不见兰斯大教堂的钟楼。”
三个端庄的女市民一边走一边说,已到了河滩广场。由于有心事,经过罗朗塔楼时谁也没停,忽视了公共祈祷书,直奔耻辱柱而来。耻辱柱四周已聚集了很多人。要不是玛耶特领着的欧斯塔什忽然的提醒,置身这种人潮汹涌的场合,大概会让她们忘了这次是为老鼠洞而来的。好像那六岁小孩已本能地预感到老鼠洞已经过去了。他说:“妈妈!现在我能吃糕饼了吧?”
如果他足够机灵,即不那么馋,他应当过一会儿,等回到大学城中瓦朗斯夫人街安德烈?穆斯尼埃师傅的寓所,老鼠洞与这块糕饼被塞纳河的两股河流和旧城的五座桥隔开时,再胆怯地问这个问题:“妈妈,这会儿我能将这块糕饼吃了吧?”
欧斯塔什这会儿提问实在冒失,但也提醒了玛耶特。她叫着:“坏了!我们忘了坐关修女了!带我去老鼠洞,把糕饼送给她。”
“马上走,行善嘛。”乌达德说。
这样,欧斯塔什没什么好处可得了。
“哎呀,我的糕饼!”他边叫边用耳朵轮流地磨双肩,表达他已达极至的不满。
三个女人又回去了。在罗朗塔楼前,乌达德对其余两个讲:“如果咱们三个都往洞中看,就会把麻袋女吓着。我先去窗中看看,您们俩装作翻祈祷书颂经。我和她还比较熟悉。等你们能过来了,我会打招呼给你们的。”
她自己到窗口上去。刚看一眼,心情痛苦,完全表现在脸上。本来快乐直爽的脸上表情大变,似乎从太阳下走进月光下,她的眼眶湿了,抿着嘴角,好像要哭出声来似的。稍候,她把食指贴在嘴上,让玛耶特来看。
激动至极的玛耶特轻轻走过来,似乎走近快死者的病榻。
两个女人呆站着,屏息凝神,透过老鼠洞的铁栅窗往里看,里边的情景让人心碎。
这间窄小的房子的宽度大于深度,房顶是尖拱状的,外观好似主教冠的衬里。旯旮里光秃的石板地上坐着,更恰当地说蹲着个女人。她双手抱膝,膝盖紧挨胸口,下巴也搁在膝上,全力缩成一团,穿着一条有大褶裥的褐色口袋。前额上耸拉着灰白的长发,顺双腿一直拖到脚跟。乍一瞧,她仅是凸现于寮房黑暗底色上的一个奇怪的轮廓,是个黑三角,窗户射进天光,把三角形分成完全不同的明暗两色。她好比人们在梦里或在戈雅的怪异画中看见的半明半暗。苍白、安静、悲惨,在墓上蹲着或背贴牢房铁槛的鬼魂。她非男非女,没有生命,也没形状;她是个半真半假的幻影图形。长发垂地,半隐半现让人觉得下边有个严肃瘦弱的影子;一只光脚尖从长袍下边伸出,在又凉又硬的石板上孤单地抽动。那丧服下若隐若现的半人半鬼像,让人很害怕。
这个似乎在石板上钉死的形象好像不能动,不会思考,也没有气息。大冷天她只穿一条麻袋,没有铺垫,半睡在阴冷的寮房里的花岗石板上。没有阳光透进铁窗,只有冷风。她对这些不觉痛楚,又似毫无感觉,她似乎已与囚室一起化成石头,和季节一起化成了冰砖。乍看你会觉得这是个幽灵,再看会认为是麻石像。
但,她青紫的嘴唇有规律地稍微张着,好似在呼吸,接着像风中败叶似地机械地摇摆。
但,有一道莫名其妙的目光从那悲凉的眼中射出,深沉、永恒、悲凄,紧紧盯着房子中的一个角落,好似将这个可怜灵魂的一切阴郁想法都引向一个神秘的东西。
就是这个因为其住处而得名的“坐关修女”,因其衣着又被叫成“麻袋女”。
这时瑞韦丝已和玛耶特与乌达德集合。三人同时往窗内看。虽然屋中微弱的光线被她们的头挡住了,但那可怜女人没看见她们。乌达德小声说:“别打扰她。她在入神地做祈祷。”
这时,玛耶特更加惴惴地端详这瘦得没人形、面容憔悴、灰头土脸的女人。她饱含泪水地嘀咕:“太奇怪了。”
她把头探进气窗铁栅栏,终于把那可怜女人死死盯住的地方看清了。
她泪流满面的缩回头来,问乌达德:“你们叫这女人什么?”
乌达德说:“我们叫她古枉勒修女”
玛耶特搭话:“我管她叫雏菊?香特弗娄梨。”
乌达德听了大吃一惊。她就用手指挡住她的嘴,让她也伸头到窗内去看。
乌达德一看,在坐关修女可怕的目光盯着的角落,有一只满缀着金银饰片的粉红色缎面小鞋。
瑞韦丝也往里看。三个女人望着悲惨的母亲,涕泪交加。
但是,坐关修女不为她们的目光与眼泪所动。她仍然双手合十,紧合双唇,眼神痴呆。只要知道她的身世,看她如此盯着那只小鞋,定会肝肠寸断。
三个女人沉默着,她们不敢吱声。她们象在复活节或圣诞节面对主祭坛一样面对这巨大的静默与痛苦,面对这个除了一种东西再无其他的彻底遗忘。她们沉默着,屏息凝神,就差下跪了,好似在受难周的主日进入教堂。
三人中瑞韦丝最好奇,故而不太善感。她最终开口,想引坐关修女说话:“嗨!嬷嬷!古枉勒修女?”
她喊了三次,一次比一次大声。坐关修女一动不动,不说一句话,不回头看一眼,不喘气,好像泥尊木塑似的。
乌达德更温柔动听的声音响起:“嬷嬷!圣古枉勒嬷嬷?”
修女依然静默,没有反应。
“这女人好怪!”瑞韦丝说,“大炮轰都不动一下!”
“或许她聋了。”乌达德叹息着说。
“或者瞎了。”瑞韦丝又说。
“或许死掉了。”玛耶特说。
可以确定:如果这个麻木、沉睡、没有知觉之肉体还有灵魂,那么它已隐退到驱壳最里边,已无法感知外部器官的感觉。
乌达德说:“只好把糕饼搁在窗口了。但会有小无赖拿走的。如何叫醒她呢?”
这时,一条大狗拖一辆小车过来,吸引了欧斯塔什。车过去了,他才看见三个大人在窗口趴着望着什么。他好奇地爬上一块界石,踮起脚,贴在窗口那张粉红的胖脸,叫着:“我也要看,妈妈!”
坐关修女被这清脆响亮娇嫩的童声惊得一哆嗦。好象被一条钢丝弹簧发动似的突然回过头,把额头的头发用那双干枯的手撩开,接着用吃惊痛苦、绝望的目光盯着他。但这神情马上就闪过了。
“上天哪!”忽然她把头埋在两腿中,大叫起来。那发自内心的喑哑声音好像把胸腔撕破了似的。“起码别叫我看见其他人的小孩呀!”
“夫人,您好。”那小孩正正经经地说。
但,方才那震颤已惊醒了修女。她浑身哆嗦,牙齿咬得咯咯响,稍微将头抬起,两肘抵腰,又仿佛为让双腿暖和些,她把两只脚用手握住。“天哪!好冷!”
“可怜的女人。”十分可怜她的乌达德说:“生点火好吗?”
她摇头拒绝了。
“那么,这有甜酒,喝了会觉得比较暖和,快喝。”乌达德将一个小瓶子递给她。
她又摇摇头,愣愣地盯住乌达德说:“给点水吧。”
乌达德坚持说:“不,嬷嬷,一月份喝水怎么行?喝点甜酒吧,吃了这块玉米发酵饼,我们特意烤给你的。”
她推开玛耶特递过的糕饼,说:“我想要黑面包。”
发了善心的瑞韦丝把她的羊毛披风解下:“拿着,这比你那个暖和,把它披上。”
她不要甜酒与糕饼,也不要披风,说:“我要麻袋。”
善良的乌达德说:“您不知道昨天是节日吗?”
坐关修女说:“我知道。我的水壶中缺水已两天了。”
停一会儿她又讲:“过节时大家忘了我没错。我不怀念人世,人世为何要怀念我?俗话说人走茶凉。”
似乎说累了,她低下头,垂在膝盖上。心地纯朴仁慈的乌达德听了后几句话误以为她在埋怨太冷,就天真地说:“您是否要生火?”
“生火!”麻袋女奇怪地说:“我那可怜的小女儿已死了十五年。给她生个火行吗?”
她浑身颤抖,嗓音发颤,两眼炯炯有神,跪着把上身挺起来。猛然她伸出苍白而瘦骨嶙峋的手,用它指向那好奇地看着她的小孩,叫着:“带走这小孩,埃及女人快来了!”
接着她脸朝地倒下了,额头叩着地板,那声响好似石头撞石头。三个女人还以为她死掉了。谁知片刻后她又动起来。她两肘两膝沿地爬到放小缎鞋的那个地方。她们不敢也不忍心听那接二连三的亲吻与叹息,不时还有让人心痛欲绝的叫闹和沉重的好似用头撞墙的声音。接着一声十分猛烈的撞击传来,吓得三个女人站立不稳。然后没有任何声响了。
“她是不是自杀了?”瑞韦丝大胆地伸进气窗想看个究竟。“嬷嬷,古枉勒嬷嬷!”
“古枉勒嬷嬷!”乌达德也说。
“上帝啊!她不动弹了!”瑞韦丝接话,“莫非死了?——古枉勒!古枉勒!”
始终憋着气的玛耶特没出声。她最终拼命大叫:“等等”。接着,她将身子探进窗子,说:“雏菊!雏菊?香特弗娄梨!”
玛耶特把这名字猛然刺进古枉勒嬷嬷的心房,足以让人惊心动魄,就如一个爆炸的捻子没燃着,一个不知好歹的儿童吹着了它,炸开的爆竹炸着了他的眼睛。古枉勒的震撼比这个儿童要强烈。
坐关修女浑身哆嗦,猛然站起,赤脚跳到窗边,眼冒金星,吓得玛耶特等三位夫人和小孩急忙后退,一直在河堤的栏干前才站住了。
这时,坐关修女那可怕的脸贴在气窗铁栅上,狰狞地笑叫着:“噢!噢!埃及女人叫我呢!”
这时,另一个场面出现在耻辱柱前,吸引了她那忙乱的注意力。由于厌恶她眉头紧皱,将如枯骨似的胳膊探出小屋,声音好似临终喘息:“埃及娘们儿,偷小孩的女贼,你又来叫我了!大胆,你这可恨的该死!该死!该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