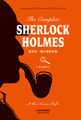奥洛拉的信终于来了,他的病已经有了起色,可以起床了。乔治只在信未签了一个名。奥洛拉没怎么问克利斯朵夫的近况,信上说自己的情况也不多;但却托他办一件事,要求把她丢在高兰德家的那条围巾寄给她。显然这不是一件要事,克利斯朵夫却因为还能为他们做点什么而高兴。外面正下着大雨,前些天寒潮刚过,下了一场雪,风是冰冷的,甚至有点儿刺骨。街上冷冷清清,克利斯朵夫在寄包裹的地方等着。职员不但无礼而且刻意拖拉,这使他非常生气,可是生气是不会解决任何问题的。他让自己心神完全安定下来,不让自己发火,近来的脾气一部分是由于生病所致;他的身体已经太脆弱了,无法再承受一次刺激。他浑身发抖地回家,看门女人在楼下递给他一段从杂志上剪下来的文字,他看了看,原来是一篇把他骂得甚至有点狗血喷头的文章。这些东西现在很少有了,打一个不觉得被挨打的人是没有什么意思的!即使是一些最执拗的敌人,尽管反对他,也禁不住对他产生了敬意,只因如此,他们心里更有气。俾斯麦曾经说过:“大家都说爱是最不由自主的,其实尊敬别人更不由自主……”
但那篇文章的作者是一个强过俾斯麦的强者,爱和敬都不属于他。他对克利斯朵夫任意侮辱,而且宣布以后还要发表几篇攻击他的文字。克利斯朵夫看到这儿笑了,一边上床一边对自己说:“哈,只怕到时他要大吃一惊呢!找我只有上天堂了。”
别人劝他雇一个看护,他坚决不肯,他说他习惯了清静的生活,这个时候雇看护不是妨碍他最后的清福吗?
只有女门房或她的孩子,他允许每天上来两三次看看他有没有事。他也托他们送信,因为在最后的日子里他还和爱麦虞贤有书信往来。两位朋友都病得很重,对自己的情况看得一清二楚。克利斯朵夫的有信仰自由的心灵,和爱麦虞贤的无信仰自由的心灵,浑然忘我,都到了物我不分的清静的境界。信上的字越来越不易辨认了,但他们从来不说自己的情况,只谈那些他们感兴趣的话题:艺术,他们的艺术,他们思想的前途。
直到有一天,克利斯朵夫努力用颤抖的手,写出瑞典王在战场上临终的话:
“我达到了我的目的,兄弟,你自个儿谋出路吧!”
就好像站在高峰上一样,他把自己的一生完整地看到了……青年时期拼命奋斗,是为了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后来顽强的奋斗,为的是争取自己生存的权利,为的是要挽救他的个性。即便是胜利以后,还得昼夜警惕,保卫他的战利品,同时防止被胜利冲昏头脑。友谊的幸福与考验,使孤独的心能与全人类沟通;然后是艺术的成功,生命的巅峰。他满认为征服了自己的精神,认为命运将由自己来掌握。不料突然风向一变,突然遇到了神秘的骑士,遇到了死亡、情事、羞耻——上帝的先锋队,他被打倒了,被踏在马蹄下,浑身鲜血地爬着,爬到了山顶上,锤炼灵魂的火焰在云中吐出火舌。他面对着上帝,跟他肉搏,像雅各跟天神的战斗一样。战斗完了,精力也耗光了。但他珍视自己的失败,明白了他的位置,应该在主指定的界限内完成主的意志。为的是播种,然后是收获,把那些艰苦而美妙的劳作做完以后,能够躺下休息,对阳光下的山峰说:“祝福你们!我不爱你们的光亮,但你们的阴影却如此美妙……”
这时候,爱人出现,拉住他的手,死神只能摧残她肉体的阻隔,她的灵魂溶入到他的灵魂里面。他们一同突破时间的洪流,到了极乐的顶点,——在那儿,过去、现在、将来,组成一个圆;平静的心同时看着悲喜交融,——在那儿,一切都是详和的……他太着急,以为自己到达了彼岸。可是胸口剧痛,脑子里纷乱的人影,使他明白还有一程最不好走的路要走……好,前进罢!……
他纹丝不动地躺在床上。一个蠢女人在楼上几个小时地弹着琴,她只会那么一首曲子,反反复复的只有一个曲子,自得其乐。这些音符对于她代表着欢乐,代表着不断变化的情绪。克利斯朵夫懂得她的快活,可是那么单调让人厌烦,几乎要掉泪了。要是调音低些倒也罢了!克利斯朵夫恨吵闹,……终于也忍受下来,能够听而不闻不大容易,但也没有像他想象中的那么难。他在慢慢地离开躯壳,离开这有着疾病而又猥琐的肉体……关在里面这么久也受够了!他看着它渐渐不中用了,心里想:
“很好,它关不了我多久了。”
他又想看看人的自私到什么地步,便问自己:“你究竟是希望哪一种?是克利斯朵夫的姓名流芳百世而让作品消失呢,还是作品传颂下来而姓名消失呢?”
他首先坚决地回答:“让我的作品留存毁灭我自己吧!在这种情况下,我要留下我最真实,惟一真实的东西。让克利斯朵夫去死罢!……”
但过了一会儿,他觉得作品跟自己一样,什么都不是,相信自己的艺术会永生,太荒唐了!他不但清楚地了解自己作品的命运,并且也了解所有现代音乐的命运,音乐的语言生命力极短;一二百年后,它也许只有极少的专家才懂得。现在谁了解蒙特威尔第与吕利?古典森林的橡树已被苔藓渐渐侵蚀。那些音响的建筑,我们在里面歌颂的热情,可是将来呢?会成为虚幻的庙堂,只剩下一片断壁残垣……克利斯朵夫觉得自己很奇怪,怎么能看到废墟而无动于衷。
“难道我其实不热爱生命吗?”他惊讶地自问。
但他立刻明白,这正表示他更爱生命……对着艺术的废墟痛哭吗?那是没有必要的,艺术是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反映。让它们一起消灭吧,让阳光淹没吧!他昏迷了很长时间,发着高烧,做着怪梦,等他醒来时梦境还在脑海中。他看着自己,摸着,寻找自己,可是找不到。他仿佛变成“另一个人了”。另外一个,比他更了不起的一个……谁啊?……仿佛梦中另外有个人附在他身上。是奥里维吗?葛拉齐亚吗?……心脏与头脑都很脆弱;分不出是他所爱的人中的哪一个了,而且认出来又怎样?他对他们都爱。
他精神虚幻,浑身酥软,不愿动弹。他知道痛苦在他身边伺伏,像猫等耗子,他就装死。怎么!死了吗?屋里没有人,楼上的琴声也消失了。孤独、静默。克利斯朵夫叹了口气。
他忽然听到一支乐队在演奏他的颂歌,不由很纳闷:
“他们怎么得到的呢?我们没有练习过,但愿他们能顺利地把曲子奏完,别出错了!”
他挣扎着坐起来,想让整个乐队都看得见他,他挥动粗壮的手臂打拍子,但乐队没有任何错误,很自信。多奇妙的音乐!啊!他们竟能自动接下去了!克利斯朵夫觉得很有意思:“等一等,好家伙!我肯定能追得上。”
于是他挥起棍子,痛快淋漓地把船驶了出去,向左,向右,穿越危险的栈道。
“这一句,你们能接上吗?……还有这个,赶快啊……又有一句新的了……”
他们总是很清楚,你给他们一些更大胆的,他们的答句也更放肆。
“他们还会弄些什么名堂来呢?这些坏家伙!……”
“真该死!倒是我跟不上他们了!难道我会失败?……你们知道,这玩艺儿是说不定的!今天我累了……没关系!先别下定论……”
但乐队所奏的奇妙的东西层出不穷,而且全都很新奇;结果是他只能听,听得透不过气来……克利斯朵夫觉得自己很可怜。
“混蛋!”他对自己说,“你完了,闭嘴吧!你也没其它的本事了,这个身体已经完了,该换一个了。”
可是身体与他过不去,剧烈的咳嗽使他听不到乐队的演奏。
“你安静一些吧!”
他的意志逐渐涣散了。克利斯朵夫闭上眼,可眼角却淌着幸福的泪水。门房的小姑娘在照顾他,很体贴地为他擦着眼泪,他却不知道。他再也感觉不到这个世界,乐队的演奏声也不存在了,他的耳朵里只有一片和声。出现在他脑海中一个问题。
“那个是什么和弦呢?怎么往下接呢?我很想找到答案,趁我还活着……”
突然响起了许多声音,其中有一个最真诚热烈的声音;还有许多眼睛,一会儿是阿娜那双哀怨的双眼,一会儿又不是了。啊,又是一双多么慈悲的眼睛啊。……
“啊,葛拉齐亚,是你吗?……究竟是谁?谁?我看不清你们了……太阳怎么还不出来?”三座钟平静地嘀答着。麻雀在窗前叫着,提醒他该喂它们东西吃了……克利斯朵夫在梦中又看到了小时候的卧室……钟声响起,天已黎明!多美的钟声啊!它们是从远方来的,从那边的村子传来……江水拍岸;声音似乎就在屋后……克利斯朵夫看到自己依靠在楼梯旁边的窗户上。他的一生像莱茵河一般在眼前流着。一生的经历,所有的生灵,鲁意莎,高脱弗烈特?奥里维,萨皮纳……
“母亲,爱人,朋友……叫什么名字呢?……爱人,你们在哪里?我的灵魂,你们在何方?我知道你们在这里,可是捉不住你们。”
“我们在陪着你。你安息吧,最亲爱的人!”
“我再也不想离开你们了,我找得好辛苦啊!”
“不要烦恼,我们不会再分开了。”
“唉!我不由自主地给河水卷走……”
“卷走你的河水,把我们一起卷走了。”
“咱们去什么地方呢?”
“到咱们相聚的地方。”
“快到了吗?”
“你看呀!”
克利斯朵夫拼命挣扎着抬起头来,——天哪,就像头上压着一座山——溢出的河水淹没了田野,缓缓地,差不多快停下来了。而在遥远的天边,一道银色的巨流像一道闪电,直冲向他,他又听到海洋在低吟……他的心在问:
“是他吗?”
那些心爱的人说:
“是他。”
濒死的头脑想着:
“门开了……我找到了要找的和弦!……难道这还不够吗?怎么又进入一个天高云淡的新世界了?……好,我们明天再前进吧。”
噢,欢乐,目睹自我在上帝崇高的和平中融化,眼看自己为上帝服务,鞠躬尽瘁地干了一生:这才是真正的欢乐!……
“主啊,你对你的仆人应该还算满意吧?我做得很少,没有做得再多一些。我有过奋斗、痛苦、流浪、创造……让我在你为父的怀抱中休息吧。有一天,为了新的战斗,我将再生。”于是,缓缓的河流,汹涌的海洋,和他一齐唱:
“你将会再生,现在先休息吧!所有的一切都是一颗心,日与夜在汇合,带着微笑。和谐是爱与恨的庄严结合。我将歌颂那个掌管爱与恨的神明。歌颂生命!歌颂死亡!”圣者克利斯朵夫渡过河,他逆流而上走了一整夜。他现在像一块岩石般矗立在水面上,左肩上负着一个娇弱的孩子。圣者克利斯朵夫靠在一棵挺拔的松树上,松树弯曲了,他的脊骨也弯曲了。那些目送他离开的人都说他不能渡过河。他们不停地嘲讽、取笑他。随后,夜来了,他们也厌烦了。此刻克利斯朵夫已经走了很远,再也听不到岸上的叫喊。在激流中,他听到的只有孩子平静的声音,——他用小手紧抓住巨人额上的头发,嘴里总在喊:“走吧!”——他就走,伛偻着背,眼睛向前望着黑暗的对岸,峭壁慢慢地显出白色。
早祷的钟声响起,无数的钟声在回荡。天又近黎明!在黑乎乎的危崖后面,尚不能看见的太阳在天空中升起。快支持不住的克利斯朵夫终于登上彼岸。他问那孩子:
“终于到了!唉,你真沉啊!孩子,你到底是谁呀?”
孩子回答说:
“我是未来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