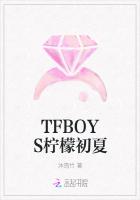心是一只美丽的小箱子
文/毕淑敏
我衷心希望每个人的小箱子里,都装满光明和友爱。
小时候上学,很惊奇以“心”为偏旁的字,怎么那么多?比如:念、想、意、忘、慈、感、愁、思、恶、慰、慧,等等等等,哈!一个庞大的家族。
除了这些安然地卧在底下的“心”以外,还有更多迫不及待站着的“心”。这就是那些带“竖心”旁的字,比如忆、怀、快、怕、怪、恼、恨、惭、悄、惯、惜,等等等等。原谅我就此打住,因为再举下去,实在有卖弄学问和抄字典的嫌疑。
从这些例证,可以想见当年老祖宗造字的时候,是多么重视“心”的作用,横着用了一番还嫌不过瘾,又把它立起来,再用一遭。
其实从医学解剖的观点来看,心虽然极其重要,但它的主要工作,是负责把血液输送到人的全身,好像一台水泵,干的是机械方面的活,并不主管思维。汉字里把那么多情绪和智慧的感受,放到它身上,有点张冠李戴。
真正统帅我们的思想的,是大脑。
人脑是一个很奇妙的器官。比如学者用“脑海”来描述它,就很有意思。一个脑壳才有多大?假若把它比成一个陶罐,至多装上三四个大“可乐”瓶子的水,也就满满当当了。如果是儿童,容量更有限,没准刚倒光几个易拉罐,就沿着罐子口溢出水来了。可是,不管是成人还是小孩的大脑,人们都把它形容成一个“海”,一个能容纳百川波涛汹涌的大海。这是为什么?
大脑是我们情感和智慧的大本营,它主宰着我们的思维和决策。它能记住许多东西,也能忘了许多东西。记住什么忘却什么,并不完全听从意志的指挥。比方明天老师要检查背诵默写一篇课文,你反复念了好多遍,就是记不住。就算好不容易记住了,到了课堂上一紧张,得,又忘得差不多了。你就是急得面红耳赤抓耳挠腮,也毫无办法。若是几个月后再问你,那更是云山雾罩一塌糊涂。可有些当时只是无意间看到听到的事情,比如路旁老奶奶一句夸奖的话,秋天庭院里一片飘落的叶子,当时的印象很清淡,却不知被谁施了魔法,能像刀刻斧劈一般,永远留在我们记忆的年轮上。
我不知道科学家最近研究出了哪些关于记忆和遗忘的规则,反正以前是个谜。依我的大胆猜测,谜底其实也不太复杂。主管记住什么忘记什么的中枢,听从的是情感的指令。我们天生愿意保存那些美好、善良、友谊、勇敢的事件,不爱记着那些丑恶、虚伪、背叛、怯懦的片段。当然这并不是说人应该篡改真相,文过饰非虚情假意瞎编一气,只是想说明我们的心,好像一只美丽的小箱子,容量有限。当它储存物品的时候,经过了严格的挑选,把那些引起我们忧愁和苦闷的往事,甩在了外面,保留的是亲情和友情。
我衷心希望每个人的小箱子里,都装满光明和友爱。
天真纯朴的心
文/席慕蓉
原来,如果你真的肯把生命放进去,这个世界也绝不会亏待你。
快下课的时候,我要学生再看一次亨利·卢梭的那一张画,那张在星光下的狮子和波希米亚女郎。
我问他们有什么感想?一个女孩子站起来回答我:
“老师,我觉得他是在告诉我们,不管这世界规定的法则是什么,像他画里这样温和平静的境界应该是可能会发生、可能会存在的。”
我微笑地面对着这个刚刚满了廿岁的女孩儿,心里觉得有许多的话想说出来。
她说得不错,在星光下沉睡的波希米亚女郎与狮子的邂逅似乎是不可能的,是要被所有自认有知识有理智的人嗤之以鼻的梦境。
可是,也有人能了解并且相信卢梭的世界,相信在那样的一个夜晚,在沙漠里,可以有那样的一场相遇。
在星光与月光之下,狮子轻嗅着身穿彩衣的流浪者,充满了好奇与关怀。宇宙间生物之中的关系除了为生存的厮杀之外,也可能并且可以发展到这样一种温和美丽的境界的。
艺术家在创作这样一张艺术品的时候,所怀抱的是怎样清朗柔美的心思啊!
奇怪的是:我们今天都能欣赏的在他画中所独具的美,却使艺术家在他自己的那个时代里受尽众人的奚落。大家都嘲笑他、戏弄他,甚至一起画画的友伴们也从来没有真心看待过他。
而卢梭却没有因此改变他对自己的信心和对这个世界的热爱,在他的作品里,总满含着一种天真纯朴的特质,使人在看了他的画以后心里觉得温暖和踏实。
“天真纯朴”应该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吧?不然,那样好、那样感动人的作品该怎样来解释呢?
前年夏天,当我在纽约现代美术馆里与“它”相对的时候,八九十年的时光已经静静地流过去了,可是,在画面上,卢梭想要告诉我们的那个世界却依然鲜活美丽。原来,如果你真的肯把生命放进去,所有的色彩和线条都会诚挚地帮你记录下来。
原来,如果你真的肯把生命放进去,这个世界也绝不会亏待你。
快乐小语
文/罗兰
快乐就是幸福,一个人能从日常平凡的生活中发现快乐,就比别人幸福。
世上没有比快乐更可贵、更为人们所普遍追求的了。我们的问题是,常常不知道如何认识及把握快乐,又有时不知道如何从不快乐之中去发现或提炼快乐。
合群是一种快乐。无论自己以为多么喜欢孤独的人,当与许多人携手并肩,用同一节奏奔赴同一目标时,也会觉得心情振奋。
人们常说,童年最快乐。通常我们只想到,那是由于童年无忧无虑。事实上,童年的快乐更是来自对环境由衷的欣赏和对人间的信心。
能克服困难,超越痛苦,由困难中取得经验,由痛苦中了解人生,这都是生活上的成功。
凡事能够大公无私,无愧于心,就是光明的行为。心情上也会觉得光明正大,高贵堂皇。这种心安理得的感觉,就是千金难买的快乐。
做事避免徘徊瞻顾,犹豫不决,有信心与决心勇往直前,不但成功的可能性大为增加,心情也会觉得振奋,生活自然就充满了希望与快乐。
荣誉的得来,一定是由于所做的事公正无私,对众人有好处。否则即使成功,也不光荣。不光荣,就不会享受到成功的真正快乐。
唯有心地光明,做起事来才会理直气壮。唯有能够理直气壮的做事,才可以不怕任何阻力,积极、坚定、勇往直前。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堂堂正正,受人尊重。堂堂正正就是守礼、守法、不自私,心地光明,行为正直。
快乐是一种美德,因为它不但表现自己对世界的欣赏与赞美,也给周围的人带来温暖和轻快。
没有一个人敢说他的生活中是没有一点痛苦而只有欢乐的。但是有人能始终对人生有着乐观和赞美的心情,这是因为他们知道,不但人间万事都有它苦和乐的两面,而且由苦中提炼出来的欢乐才更是胜利的凯歌。
认真说来,个人遭遇的痛苦是局限的,而人间的希望和生存的价值是多方面的。我们要能够不着眼在狭小与局限的个人遭遇,而看到广大的空间与丰富多彩的世界,即可知道,许多我们自己引为大事的,都只不过是一些毫末。
快乐就是幸福,一个人能从日常平凡的生活中发现快乐,就比别人幸福。
墙那边的前苏联
文/韩少功
它们带去的种子,也许会发芽,也许会枯灭,在血色残阳下的黄昏。
我家院西头墙那边是学校操场,再远处,是时静时喧的教学楼,还有不时冒出鸡鸣鸭叫的教工宿舍。这是一所九年制学校,全乡唯一的学校。
很多山区的孩子上学太远,没有办法,只好从小学一年级就寄宿。我从校区走过的时候,常看到一些孩子在保姆的指导之下洗脸、洗手、洗碗,乃至解裤带拉屎。稍大一些的学生,把扫地当做狂欢,用扫把搅出满天黄尘,搅出咯咯咯的欢天喜地。还有一些学生在那里排练仪仗,只是少先队礼行得不大规范,不但缩头缩脑,而且小小手臂弯曲如钩,钩住自己小脑袋,一副闯祸以后防备毒打的畏缩模样。
不知什么时候,墙那边有前苏联时期的歌声飘来:
当年我的母亲,
通夜没有合上眼睛,
伴我走遍家乡,
辞别父老乡邻。
当时天色刚黎明,
她送我踏上遥远的路程。
给了我一条毛巾,
她祝我一路顺风……
这是一首著名的俄罗斯歌曲,正在由一位女教师教唱。我很好奇,一首在耳际消失了数十年的歌曲,为何出现在这个老山角落,撞入了我的黄昏?更有意思的是,从这一首歌开始,院墙那边简直成了前苏联,《喀秋莎》、《三套车》、《小路》、《红梅花儿开》、《伏尔加船夫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等,一曲曲全成了清脆童声,经常使我恍若隔世,恍若入梦,差一点想翻上墙头,看看墙那边的白桦林和冰雪草原,向红色少年的骑兵军挥手致敬。
一天,我终于忍不住,到学校里去打听教歌的女老师,打听她为什么对这些老歌情有独钟——这些怎么听都有些忧伤和沉重的歌。我得到的消息是:教唱者是一位小姑娘,在这里四个月的代课已经结束,刚回县城去了。
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
河上飘着柔曼的轻纱……
小姑娘留下的歌声不时在校园里飞旋,如零散的蒲公英随风飘飞不知所往。它们带去的种子,也许会发芽,也许会枯灭,在血色残阳下的黄昏。
闲情
文/冰心
我觉得没有一时,不沉浸在轻微的愉快之中。
弟弟从我头上,拔下发针来,很小心的挑开了一本新寄来的月刊。看完了目录,便反卷起来,握在手里笑说:“莹哥,你真是太沉默了,一年无有消息。”
我凝思地,微微答以一笑。
是的,太沉默了!然而我不能,也不肯忙中偷闲,不自然的,造作的,以应酬为目的的,写些东西。
病的神慈悲我,竞赐予我以最清闲最幽静的七天。
除了一天几次吃药的时间,是苦的以外,我觉得没有一时,不沉浸在轻微的愉快之中。——庭院无声。枕簟生凉。温暖的阳光,穿过苇帘,照在淡黄色的壁上。浓密的树影,在微风中徐徐动摇。窗外不时的有好鸟飞鸣。这时世上一切,都已抛弃隔绝,一室便是宇宙,花影树声,都含妙理。是一年来最难得的光阴呵,可惜只有七天!
黄昏时,弟弟归来,音乐声起,静境便砉然破了。一块暗绿色的绸子,蒙在灯上,屋里一切都是幽凉的,好似悲剧的一幕。镜中照见自己玲珑的白衣,竟悄然的觉得空灵神秘。当屋隅的四弦琴,颤动着,生涩的,徐徐奏起。两个歌喉,由不同的调子,渐渐合一,由悠扬,而宛转;由高吭,而沉缓的时候,怔忡的我,竞感到了无限的怅惘与不宁。
小孩子们真可爱,在我睡梦中,偷偷的来了,放下几束花,又走了。小弟弟拿来插在瓶里,也在我睡梦中,偷偷的放在床边几上。——开眼瞥见了,黄的和白的,不知名的小花,衬着淡绿的短瓶。……原是不很香的,而每朵花里,都包含着天真的友情。
终日休息着,睡和醒的时间界限,便分得不清。有时在中夜,觉得精神很圆满。——听得疾雷杂以疏雨,每次电光穿入,将窗台上的金钟花,轻淡清澈的映在窗帘上,又急速的隐抹了去。而余影极分明的,印在我的脑膜上。我看见“自然”的淡墨画,这是第一次。
得了许可,黄昏时便出来疏散。轻凉袭人。迟缓的步履之间,自觉很弱,而弱隐含着一种不可言说的愉快。这情景恰如小时在海舟上,——我完全不记得了,是母亲告诉我的,——众人都晕卧,我独不理会,颠顿的自己走上舱面,去看海。凝注之顷,不时的觉得身子一转,已跌坐在甲板上,以为很新鲜,很有趣。每坐下一次,便喜笑个不住,笑完再起来,希望再跌倒,忽忽又是十余年了,不想以弱点为愉乐的心情,至今不改。
一个朋友写信来慰问我,说:
“东坡云‘因病得闲殊不恶’,我亦生平善病者,故知能闲真是大工夫,大学间。……如能于养神之外,偶阅《维摩经》尤妙,以天女能道尽众生之病,断无不能自己其病也!恐扰清神,余不敢及。”
因病得闲,是第一慊心事,但佛经却没有看。
银与福
文/毕淑敏
银子永远不能骑在福上头。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有一座魔鬼城。它是雅丹地貌形成的沟壑,被飓风的利刃和雨水的指甲还有岁月的剪刀雕刻镂空,塑就了千奇百怪的城骸和猛兽的残肢。最近被正式辟为地质公园,引来零散游客。
有一处地貌类似“无敌舰队”,无数高大的雅丹(雅丹是维吾尔语,意即陡峭的丘陵)层岩,昂首挺胸,好像被天庭的巨鞭抽打着,中规中矩地朝着一个方向航行,虽悄无声息但一往无前。每一座舰艇都似5层楼雄伟,朋友们隐入其中玩耍照相。工作人员一个劲叮咛,万万不可走远误入深处,此地渺无人烟,距彭加木和余纯顺的遇难地只有几十公里。
我因脚踝扭伤,无法走进波涛起伏的沙砾,只有坐在一旁看着瀚海发呆。忽然背后有幽灵般的声音响起,客人,买一幅羊皮画吧,它会带给你好运。猛回头,见一老媪披着漠黄色的袍子悄然移近我,枯瘦的手爪挥舞着一卷画轴。
我吓了一跳,觉得这老太简直就像是魔鬼城的常住人口。揉眼看不远处的越野车和天上的昏黄太阳俱在,胆子才壮了一些,问,你的羊皮画上都画了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