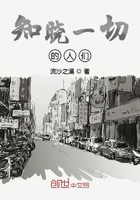年华
古斯米尔
那年冬天,一个孩子第一次用黑白分明的眼睛打量这个世界。我回想起那天傍晚黄昏的落日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悲怆。此后的许多个日月,落日余晖的阴影在我的生命里挥之不去,伴随着一个女人撕心裂肺的叫喊,幸福而痛苦。
我一直愧对母亲,一直一直……她的痛苦完全归咎于我的出世。母亲生我的时候难产,痛苦了一天一夜,幸运的是最后保住了命,但从此再没能站起来。当我第一次明白母亲卧床不起,从不陪我逛街、吃饭、买玩具等等完全是因为我时,我开始不断地诅咒镜子里那个还算鲜活的稚气未脱的小孩,并且从此害怕与镜子有关的一切。
还小的时候我曾经问母亲,“只要没有我,妈妈你就会好了,对么?”母亲轻轻地搂着我说:“傻孩子,妈妈从没有怪过谁。你是我这一生最幸福的选择,明白吗?”当时的我还不足以明白母爱的伟大,但那种坚定而执着的眼神令我至死难忘。
我慢慢长大,到了足够明白许多事情的年龄。对母亲的愧疚依然不变,但也仅仅是愧疚了。母亲平稳柔和的目光里那种幸福和执着不再晦涩难懂。
我必须做个好孩子,这是母亲唯一的心愿。在那些阳光明媚的日子里,白色的绵羊嗒嗒地踩着湿滑的青石板桥,响亮而欢快,以及少见的古木和窗口对面不高的沉寂的山峦……这一切构成了我记忆中最单纯的美好。嗒嗒的脚步声像支号角,悠长而缓慢地贯穿我的生命。
我的生命像一只透明的玻璃罐子,周围是许多我关心的和关心我的人。他们每人手里捏着一颗幸运星,不同的颜色。我说扔进来吧,装满它,于是我的生命变得五颜六色。可惜这些不是我的,快乐不是,悲伤不是,成功不是,失败也不是,统统统统都不是。我不停地为别人哭,为别人笑,为别人喜,为别人忧,这些都不是我自己的,我永远永远只是一只透明的玻璃罐子。
镜子里那个开始长出淡淡胡须的影子仿若素昧平生。我就这样告别了自己的童年,那些回忆除了数不清的白昼黑夜以外一无所有。青石板桥上白色绵羊的脚步越走越沉重,远方山峦起伏的轮廓在阳光里透着朦胧的金色,重彩油画不均匀底色辗转铺陈。我站在岁月的这一头眺望,风儿、鸟儿,一切我不曾拥有的东西。
琪琪说,做孩子快乐,这句话在我耳旁百折千回。我一直对“孩子”这两个字嗤之以鼻,于是盼望长大。可是为什么,心里竟隐隐作痛?为什么?我不知道,就像我不知道自己从何而来,又该去向何处。
在网上我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我用冰冷的屏幕隔绝所有的人情冷暖。一根纤弱的电话线连着一个世界,仿佛一种莫大的讽刺。我站在世界的尽头,目光漠然,一些莫须有的人物在莫须有的空间里忙忙碌碌,像一出永远不会落幕的喜剧。人生如戏,一场摆弄命运的游戏。现实中我们都玩不起,因为无法重来。网络中生与死的轮回有时只需要几秒钟,鼠标轻点,然后你不再是你自己。
很长的时间,我迷失在这种操纵命运的快感中无法自拔,在时间的尽头,我一个人行走。
我的超然物外一直到遇见Sunny才开始土崩瓦解。她说:“阿杰,你是个忧伤的孩子。我说,不!我不是孩子。”阿杰阿杰,我要怎么才能抚平你的眉头呢?她总是这样叹息。那晚上我第一次对着电脑屏幕自言自语然后泪流满面,那些湿润的液体一直流淌着,湿了裤脚湿了衣裳。而这一切只因为一个不知高矮胖瘦是人是鬼的Sunny和一些不知所谓的话。阿杰阿杰,你背负了太多沉重,而你只是个孩子。她这样说着,打了三个大大的惊叹号。我无言以对,那些文字中冷漠以外的东西我自己永远也看不穿。我想我其实是个害怕孤独的人,于是竭尽全力地想留住什么,然而越是如此便越孤独。我开始无法抑制地喜欢Sunny,像很多年前我喜欢白昼的阳光一样喜欢。Sunny笑啊笑的,用各种夸张的符号表示她的雀跃。她说阿杰我知道会是这样的,我就知道。
很多时候我都会莫名其妙地开始想念Sunny,如同想念过去阳光的味道。我向她陈述这些想念的时候她总是笑,一直笑。她说阿杰,当你学会每天都笑时,你就会忘记我了。永远永远地忘记。
不可否认,与Sunny相处的日子很快乐。只有这时我才可以忘记一些东西。一些过去我无法释怀的事物,譬如:阴影、阳光、愧疚。这种遗忘让我如释重负,然后我开始学着快乐,笑是世界上最纯粹的快乐,Sunny说。一直到有一天我终于开心地笑了,但是Sunny消失了,像她突然出现一样突然地从我的生命里消失得不留痕迹。她说当我学会笑的时候便会开始忘记她,她以为我会忘记她的。Sunny是个聪明的女孩,她悄悄地消失,再也没出现,连忘记的机会也不给我,一点也不。那段日子恍若南柯一梦,她什么也没留下,除了脸上的笑容和我的记忆。
再然后我遇见了现在的女友琪。我在想象中拼凑属于Sunny的特征,她全部具备,而那些灿烂的笑容如此熟悉。她在我的身旁从右手跳到左手,然后一直笑着,轻灵得让我心醉。我说:“琪你的笑容真像Sunny。”她说“什么?”是阳光,最美丽的阳光,我说。她又开始笑了,阿杰,你真的是个孩子,她说。
十七岁的最后一个夜晚无比孤独,很多的人在我的周围喧嚣嘈杂,很大声地不断用中文、英文、日文唱着《祝你生日快乐》。但我感到孤独,一种像玻璃一样透明冰凉的东西把我与世界隔离开来,看不见却摸得着,这种感觉让我浑身战栗。我开始不断地想念一些人—母亲、Suuny、琪、小安还有很多人。这种过于专注的思念让我头痛欲裂,但是我无法停止,唯有这样才可以摆脱那种寒冷。我可以清晰地感觉到沥青般粘稠的黑暗在手臂上蠕动,触体生寒。
就像蚂蝗,小安这样说。不同的是蚂蝗贪恋鲜血,而黑暗贪恋寂寞。
那天晚上我一直沉默,从十七岁到十八岁。
有些日子宁静安详,一切不顺心或者畏如蛇蝎的事物无影无踪,阳光洒满世界每个角落,那些明亮的光线平稳而温暖。
我笨拙但很小心地熬一碗银耳莲子汤,看着母亲一勺勺慢慢喝下。也许味道不尽如人意,但是母亲的眼里充盈着满足,她实在是一个很容易快乐的人。于是自己心里也无比的幸福。
和琪一起在东庄高大的梧桐树下悠闲地消磨时间。她一直跳那种很古老的《彩衣霓裳》,穿着普通的衣服跳,CD里放着斯特拉文斯基的《彼德鲁什卡》和弦。旋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心境。她像只蝴蝶般穿梭在飞舞的落叶中,咯咯地笑着。我告诉她我是那么强烈地爱着斯特拉文斯基,那些赋格奇异而且风格紊乱的曲谱死死地抓住我的感官。于是琪说,“阿杰,总有一天我会把所有的曲子跳给你看。“
我在这些闲散的平静里不断地迷醉并且欲罢不能,我不知道这种快乐还能持续多久,一瞬间还是永远,又或者,这是开始还是结束?
母亲终于没能过完这个并不寒冷的冬天,在一年的最后几天里她离我远去。我相信母亲是带着微笑离开的,就如同我相信sunny也是笑着消失一样。离别是个沉重的话题,尤其是生离死别。那天下着很大的雪,很大很大,尽管天气并不寒冷。一直到最后冰消雪融万默静寂,那些属于母亲的祝福化作汩汩清泉无声流淌。我没有哭。
有时候我傻傻地问琪,“你为什么不走。”琪很灿烂地笑着,有些潸然的样子,然后她就真的走了,乘很大很大的银灰色的飞机,像那些飘着的雪花,而落点是遥远的大西洋的另一边,一个我怎么也看不到的地方。
十八岁的冬天,我所熟识的人一个个消失,像那些雪花一片片飞舞,然后融化了。我看到天边的落日转瞬即逝,那些光线还来不及形成阴影便烟消云散,开始失去很多东西,直到我一无所有。我终于开始不再惧怕黑夜,因为我已经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失去,除了我自己,只有我自己。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也会离开,到天边有很多星星的地方。
看着夜空下闪烁的星辰,像妈妈幸福坚定的目光,还有Sunny的笑脸。“妈妈,我在笑呢,你看见了吗?”我轻轻地阖上了眼,一直笑着。
精品赏析
有些日子宁静安详。一切不顺心或者畏如蛇蝎的事物无影无踪,阳光洒满世界每个角落,那些明亮的光线平稳而温暖。女生麦子茜
左丽
麦子茜是我们班最高傲的女生,也是最孤独的女生。麦子茜其实很优秀,她有不俗的成绩,很蔻的美脸,可她就是没有朋友。就像说不清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我也说不清她是因为高傲而没有朋友,还是因为没有朋友而愈加高傲。更坏的是我们班的“八兄弟”事事糗她,损她的炫,就像某美国人排挤前联合国秘书长一样。
“八兄弟”其实不是男生,而是一群女生。我不知道她们为什么要与麦子茜作对,她们对别人挺友好的,可能是麦子茜偏激的高傲伤害过她们。总之,在129号女寝室里,麦子茜的衣服是要两个星期才能干的。每天早上起来,大家都会发现她那本来快要干的衣服又会变得湿湿的了。教室里,没有人会主动与麦子茜讲话,偶尔某人与她搭讪,“八兄弟”中的某一位会讲:“你叫什么呀,我们做作业呢!安静点。”那位就只好闭上嘴巴。尽管如此,麦子茜还是麦子茜,照例在早上用她的水果杯去食堂打一杯豆奶,照例在第二节课下课吃一个水果,照例穿具有欧洲风味的厚厚的布裙子,然后昂着头在人们面前走过,留下一阵风。
我并不是存心去看麦子茜的日记的,这点,上帝可以做证。那天,我经过她的课桌旁,看见地上有一个本子,就拾了起来,顺手翻了一下,厚厚的一个本子,居然写满了日记。我没有偷看人家日记的习惯,就合上本子,抬头,就看到麦子茜了。她身后跟着一个高大俊秀的男孩,那个笑起来很好看、两排洁白的牙齿教人想起儿童琴上的白键的男孩。如果你是我们学校的女生,就一定认识他。我把本子还给她,正要走,她忽然说:“本子里写的都是我跟‘八兄弟’的事情。”末了,她说,“我只是想看自己的忍耐力到底有多大。”我转过身,对她无辜地笑笑说:“我想,你误会了,我什么也没看到。”
我确实什么也没看到。
班上有了关于麦子茜的流言,关于那个男孩的。有人说看见他俩在麦当劳餐厅头碰头地吃薯条,有人说他俩在的士高溜冰场手牵手地溜冰,有人说……我知道流言在所难免,但想不到这么汹涌,像洪水,能淹没校园的任意一个角落。同学们都在叽叽喳喳地议论这件事情,不知他们说的是否是真的。但我们可以看到放学后他在走廊上等她的身影。于是同学们愈加添油加醋,我也更加明白了“舌头虽没有骨头,却比牙齿更锋利”的意思。终于,班主任风闻了这件事情,找到她谈话。她一出办公室就失踪了,一天没来上课,谁也不知她去了哪里,老师急得到处找,终于在秋风萧瑟的马路上找到了她。她回来了。她站在讲台上,对大家讲了一次话:“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不喜欢我,我觉得我不像个坏人。没有人告诉我该怎么办……没有人同我讲话,我就去和他讲话了,只是讲讲话……”她哭了。大家都看着她,看着她哭,看着那个高傲的麦子茜哭,大家突然也觉得想哭。
后来,“八兄弟”没有再为难过麦子茜。再后来,大家就同她讲话了。第二节课下课时,麦子茜的座位常常围了人,大家闹着要分吃她的水果……后来,我和麦子茜站在空旷的操场上,对着天空放声大喊:“我很快乐”
精品赏析
她哭了。大家都看着她,看着她哭,看着那个高傲的麦子茜哭,大家突然也觉得想哭。起死回生的友情
方冠晴
这栋楼房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建造的,楼高四层,样式陈旧,设施简陋。半个世纪的风吹雨打,加上年久失修,墙体已经裂了缝,给人摇摇欲坠的感觉。
市政府已经将这栋楼列为拆迁的对象,但楼里的居民迟迟不肯搬出去。因为这栋楼里的居民都是穷人,家里都没有什么积蓄,光靠政府发的拆迁费,买不起新的房子。
张星和侯晓就是在这栋楼里长大的。张星家住在一楼,侯晓家住在二楼。两个人在同一所小学读书,都读四年级。
张星和侯晓都是男生,两个人在学校里是要好的同学,回到家里是要好的伙伴。两个人经常在一起学习,在一起玩耍,上学放学,同进同出,友谊深厚。但是,今年夏天发生的一件事情改变了这一切。
张星和侯晓的父母都在菜市场以摆摊卖菜为生。那天,两家的大人为了争夺摊位发生了口角,到最后,竟大打出手,侯晓爸爸的头被张星的爸爸打破了,到医院缝了三针。张星妈妈的脸也被侯晓的妈妈抓破了一大片,进医院住了好几天。虽然经过居委会的调解,但两家大人的心里都积了怨气,从此成了仇人,即使是在楼道里碰着了,也谁都不看对方一眼。
大人间的恩怨起初并没有改变张星和侯晓之间的关系,两个人放了学,仍是一块儿玩耍,但是,张星的妈妈出院那天,看到张星与侯晓在一块儿,就气不打一处来,扇了张星一个耳光,骂张星不知好歹,要他今后不准搭理侯晓。侯晓的父母也是粗鲁的人,听到张星的妈妈在骂孩子,也跑出来,将自己的孩子揍了一顿,不准侯晓再与张星仍有往来。
两家的大人都以打自己的孩子来出气,指桑骂槐,险些又发生纠纷。这样一来,张星和侯晓虽然在学校仍是好朋友,但回到家里便不敢相互串门,更不敢在一起玩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