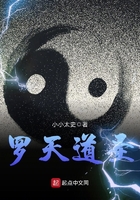云舒怀是疼醒的——都说十指连心,这话丝毫不假。
他睁开眼睛,就见容轻诺一手拿着一把精巧的小匕首,另一只手,嗯,他的视线稍稍往下,就看见自己的食指抓在她的手中。
拉开了一条口子,正在滴着血。
“哇啊——”云舒怀险些要跳起来了,才一动,就觉得那把匕首直直逼近自己的颈边。
文弱书生云舒怀立刻僵直了身子不敢动弹了。
容轻诺一脸的不耐烦:“别吵!”
云舒怀之父曾是文状元,善辩才,美仪容,却是生性厌武。湖阳公主贵为长公主,自小骄横,自然也不曾习武,到了云舒怀这一代,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碎了。想当然耳,也不曾练武。
也就是说,别说捏在容轻诺手里的只是一根食指了,就算是云舒怀的脖子,他也无可奈何。
血都滴在一块白色的帕子上,云舒怀再无知也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容轻诺皱着眉,显然心情不佳。
云舒怀心里也略感愧疚,他对解语倾心已久,恨不能抱得佳人归,昨晚又借酒撒泼,定然是什么都没有做。容轻诺虽然是将门之女,想来也是十分好面子的,这么清清白白地度过了新婚之夜,面上自然不好看。
看血滴得差不多了,容轻诺从怀中摸出个小瓶子,往云舒怀手指上倒了些粉末,那血很快就止住了。
就连疼痛也似乎减轻了许多。
“相公,新媳妇过门要给公婆倒茶请安,妾身就不奉陪了。”容轻诺静静起身,竟然已经穿戴整齐,“你自便吧。”
云舒怀眨了眨眼,这就完了?不是应该一哭二闹三上吊么?
将门虎女,也不过如此啊。云舒怀有点窃喜。
容轻诺却不理他,径直去了湖阳公主的居住的逸云轩。
“婆婆,请喝茶。”恭恭敬敬地奉茶,容轻诺垂首立在一边。
这湖阳公主天潢贵胄,对于将门之女本来不是那么看得上,总觉得她们粗俗,配不上自家那龙子凤孙。
只是如今见了容轻诺,倒是有几分明白,为何当日太子大手一挥,就偏偏点中了容轻诺。
端的是仪容端庄,娴静舒雅。
湖阳公主本来为云舒怀爱上了那名叫解语的头牌而着急上火,已经便秘数日,此刻见了新媳妇,又喝了媳妇茶,自然是全身通泰。只想扑到已经死去的相公,也就是云舒怀他爹的灵位前大哭一场。
“相公啊,我终于对得起云家了。我们那宝贝儿终于成亲了!而且新媳妇看上去很能生养。”
心里这么想着的时候,湖阳公主忍不住眉开眼笑,拉着容轻诺的手就开始互诉衷肠:“轻诺啊,不是为娘偏袒自家的孩子,舒怀那孩子从来是众人捧在手心里的,难免骄纵些,日后还望你多担待。”
“娘亲这是哪里话,”容轻诺一脸乖巧,可惜目光似剑似刀,“轻诺既然嫁进了云家,那相公便是轻诺的天。”
“好孩子。”湖阳公主窝心一笑,心中却在纳闷——那镇国公脾气自然是算不上好的,就连他那前三个女儿,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这容家的小四,竟然出人意料的品貌端庄啊。
真是越看越招人喜欢。
“府里人多嘴杂的,难免有人要在背后嚼主子的舌根子,”湖阳公主微微叹气,“但是,轻诺,你要相信舒怀,他决定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
“娘亲,你太多虑了。”容轻诺温柔一笑,“男人嘛,那个不风流呢。早逝的公公怕是那唯一的例外了,娘亲你真是好福气。”
湖阳公主听了这话,反而脸现惆怅。
当年算命的先生曾断言,湖阳公主命格太硬,生来是克夫的命。诺大京师,王孙公子,没有一个敢跟天抗命。
眼看湖阳公主已经年长,皇上也是暗自着急,承诺谁娶了自家小妹,就封他万户侯。
然而又过了几年,湖阳公主长成了老姑娘了,还是没有人敢娶。
这时候出了个云状元,虽是文弱书生,却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向皇家提亲了。
“我不如地狱,谁入地狱?我云逸尘今日愿娶公主,只想今生举案齐眉,白发偕老!”
当日豪言尚在,只是人踪已杳。
怎不令人叹息。
湖阳公主摸出个小手帕,擦掉眼角的几点珠泪。
又拉住容轻诺的手:“你这孩子,本宫十分喜欢,有空的时候,多多到娘亲这边走动走动。若是舒怀那臭小子对你不好,你尽管跟娘说。”
容轻诺端庄地点头:“谢谢娘亲。”——兵法长云,兵者诡道,能之示之不能。敌人才会松懈。
湖阳公主递了个红包过去:“乖。”
容轻诺双手接过,温婉地道了谢,这才慢慢退了出去。
回到自己住的凝碧轩,正巧司晨来收拾房间,看到容轻诺回来,脸上略略有些奇怪的表情,很快就恢复了正常:“夫人,少爷去了东宫,说是中午不回来。”
容轻诺静静点了点头,这云舒怀是太子伴读,平日里除了太子的东宫,就只有解语在的那个添香阁是他最常去的地方。
红袖添香自是人间美事,只是容轻诺自认不是大方的人,那个解语姑娘就算再如何情深意重,想进云家的大门,一个字——难!
“夫人,”司晨犹豫了半晌,终于慢慢开口,“如果少爷硬要将那位解语姑娘接到府中,你会怎样?”
“是相公让你来探口风的么?”容轻诺轻轻挑眉,冷冷一笑,“我与她,相公只能选一个。”
司晨伶伶一惊。因为容轻诺说这话的话,神情冷厉,哪里有半分温婉的样子?
她低下头,快速地收拾了并不怎么凌乱的床铺,逃也似的出去了。
容轻诺这话说的是解语,又何尝不是说给她听的?不管之前如何,在她之后,少爷房中想要添一个人恐怕也是不可能的。
她咬了咬唇,眉眼间一抹冷色横过——容轻诺不过是从边陲小地嫁过来的武将之女,在这人生地不熟的京师,又能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