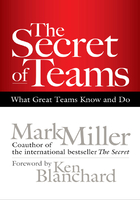去教堂的路上,伊格的掌心一直在冒汗,黏糊糊的很难受。他的肚子也不舒服,胃里翻江倒海。伊格知道这都是为什么,可还是觉得自己荒唐透顶--他连那女孩的名字都不知道,甚至没和她说过一句话。
他们唯一的交流就是女孩给他发出的信息。那天教堂里坐了满满一屋的人,有很多跟她差不多年龄的男孩,而她偏偏朝伊格看过来,用她那金灿灿的十字架向他传递某种信息。直到现在,伊格还没想清楚,自己怎么忍心就这么放她走,把她拱手让给别人,就像把棒球卡或CD送人一样,如此轻易就让她走出了自己的世界。伊格一直说服自己:李是个孤独而又贫困的孩子,他需要有人陪伴,而缘分是上天注定的,谁也改不了。他试着安慰自己,让自己为所做的事情感到高兴。可事与愿违,伊格没有感到一丝舒坦,恐惧如同一堵漆黑的墙,在他心中缓缓升起。他根本想不出,到底是什么神秘力量迫使他眼睁睁地看着李把女孩的十字架从他这里拿走。李今天肯定把它带来了,他肯定会拿去还给那女孩,然后女孩会谢谢他,礼拜结束后他们就会一起聊天。在伊格脑海中,那幅画面变得异常清晰:李和那个女孩肩并肩一起走出了教堂,当红发女孩走过去的时候,她朝伊格这边瞥了一眼,但是她的目光却没有停留,她根本就没有认出他--修好的十字架挂在她的颈上,熠熠生辉。
李已经到了教堂,他还坐在老地方,可他把女孩的十字架戴在了自己脖子上,这是伊格最先注意到的细节。他的反应很简单,完全是一种生物化学反应--就像一口喝下了一杯滚烫的热咖啡,整整一杯,一口气喝完,胃里一阵翻腾,像是烧着了一样,血液四处奔涌,仿佛随着咖啡因沸腾起来。
李前排的长椅一直空着,直到礼拜仪式开始前的几分钟,才有三个又矮又胖的老妇人进来就坐,恰好坐在上个礼拜天红发女孩坐过的地方。礼拜仪式的前二十分钟,李和伊格一直伸着脖子搜寻那女孩的身影,可是怎么找也没找着。她的红发就像编织起来的铜丝一般闪亮,怎么可能看不到--看来她根本就没来。最后,李看了看过道这边的伊格,滑稽地耸了耸肩,伊格也夸张地耸耸肩以示回复,好像他是李企图勾搭上“摩尔斯电码女孩”的同谋。
但伊格不是李的同谋。念主祷文的时候,伊格低下头,但他祈祷的内容不是标准的祈祷文--他祈祷拿回十字架,管他什么祈祷文。他渴望拿回十字架,他从未这样热切地渴望过一样东西,即使那时身在水中,面对黑暗的深渊和呼啸的灵魂时,他对呼吸的渴望都没有现在对十字架的渴望强烈。伊格不知道那女孩的名字,但他知道他们在一起会无比快乐--“在一起”这三个字本身就带给他无限的快乐。他知道,她用闪光向他传递信息的那十分钟是他在教堂里度过的最美好的十分钟。有些东西就是不能让给别人,不管你欠了他多少。
礼拜仪式结束后,伊格站在那里,父亲的手像往常一样搭在他肩上,看着教堂中的人越走越少。不论是教堂、电影院,还是棒球场,只要是在人群拥挤的地方,伊格一家总是最后一批走的,这仿佛已经成了一种家族习惯。李·图尔诺走过去的时候对着伊格随意地点了点头,好像在说“胜败乃兵家常事”。
人群一离开过道,伊格就赶紧跑到上个礼拜天那位红发女孩坐的长椅边,单膝跪地,假装系鞋带。父亲回头看了看他,可伊格点点头让他们先走,自己马上会追过去。直到家人都走出了教堂正厅,伊格才放开手里的鞋带。
那三位老妇人还坐在“摩尔斯电码女孩”曾经坐过的长椅上,她们拿起手提包,然后把披肩围好。伊格抬头瞟了她们一眼,突然觉得自己好像在哪里见过她们。上个礼拜天的时候,就是她们跟女孩的母亲一起走出教堂的。那时她们一群人走在一起,唧唧喳喳聊个不停,伊格当时还在猜想她们是不是那个女孩的姨妈,好像其中一位还在礼拜结束后跟女孩一起坐车走了。这些事伊格都拿不准,他宁愿这样想,却又怕这些记忆都是自己一相情愿的念想。
“请问……”伊格开了口。
“什么事?”离他最近的一位妇人说。那是个大块头的女人,头发染成了金属棕色。
伊格指了指那个长椅,晃着头说:“上个礼拜天曾有个女孩坐在这里。她不小心把东西落在这儿了,我想还给她。是一个红头发的女孩。”
那位妇人没有回答,只是坐在那里,尽管这时候过道已经空荡荡的,她也没有起身离去。最后伊格终于明白过来,原来她是在等着自己的目光与她对视。伊格看向她的眼睛,才发现她正眯着眼打量自己,眼里有种无所不知的感觉,伊格顿时觉得脉搏开始怦怦直跳。
“玛丽安·威廉姆斯,”她说,“她们一家只是上个周末来镇里看新房子。我之所以会知道这些,是因为他们要买的就是我的房子。我还带她们一家来这个教堂参观。他们现在回罗德岛州了,正收拾东西打包呢。她下个礼拜天就会回来的。我确定,你很快就能再见到他们了,很快。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把玛丽安落在这儿的东西带给她。”
“不用了。”伊格说,“没事。”
“嗯。”老妇人说,“我看你还是想亲自把东西交到她手上吧。你的心思都写在脸上了。”
“什么……什么心思?”
“不过啊……”老妇人又说,“我们这可是在教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