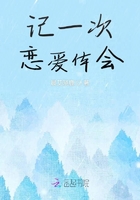否定先生
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
它既不像清晨朝霞那样迎着你的脸庞,也不会像傍晚夕阳那样追随你的脚步。它不是你街角转弯的意外邂逅,也不是载你驶向幸福的一叶孤舟。你低声吟唱时它总会用哭泣为你伴奏,你深夜安眠时它又悄悄在房间踱步。它也许是你秋日黄昏后在公园休憩时莫名的空虚,又或许是你漫步湖畔对影投石的突现的颤栗。它是你指尖的一抹斜阳,是你眼眸的游弋光点,又或者是你月下对影独酌的惬意。在你长夜失眠时它常牵引你的脚步,当你摸黑潜行时又不至使你迷途。它把脚印销毁、抹平,把身影藏于这重重薄雾之中,又让白蝴蝶在身后飞舞遮掩它所行之处的一切讯息。它常伴左右,幻化无形,又悄无声息。它住在半山墓地的一偶偏居,终日以贡品为食,以苔藓为裳。大雨初歇后,它常是像美女蛇那样蜷曲于路边,手里拿着诱饵,像垂钓者那样捕获离群的人子。有人曾与它偶遇,所幸逃脱,回来妄言说它是老屋夭折被人遗弃的幼子,说它是从悬崖失足的死尸,又说它是入葬后回光返照的在棺椁里一息尚存的孤独老人。不。他说错了。不是他说的那样。它也许是迁徙候鸟群里最柔弱的那只,也许是初冬都不凋谢的雏菊,但它并不是曾经记忆里悲伤的往事(再说,它何至于让人耿怀至今呢),也不是漫天雪花落入眼睛暖化的水滴。它的确隐居,但不是在老屋,不是在墓园,不是在棺椁,也不是在一簇玫瑰的花蕊里。我其实不确定。我只是觉得它无处不在,而又流于幻影。它住在无人知晓的角落,语言的禁区。文字在这里失去了效用,语言显得苍白无力。
但我仍要试着向你讲述这个秘密,因为我是因为它才去写小说的。
那大概是生命初期某个迷幻的夜晚。在昏睡的间歇,它潜入梦境,将一枚银针直刺进我的骨髓里。从那时起,它就寄居在我灵魂里,把我奴役。我的血肉里至今仍遗留着它阴狠的残毒,它将悲剧的种子掩埋在我身体了。我只是一具皮囊,只是供它寄居,休养生息的躯壳。清晨未醒,它就敲击着我的骨殖,抽调腿骨说那是芦笙上好的原料,它把皮肤裁剪成所要的衣裳的样式,把我的血液当做琼浆玉露向人们出售,它把我绑架,搁置在面板上,让蛆虫随意咬噬我的肌肤,那些汗毛就是它们休养生息的证据。它用铁锹挖掘我的发根,想用我稠密的头发铺在它妻子将要妊娠生产的温床上,可是它低估了发根植入皮肤的深度,于是它恼羞成怒,吸去黑发的色素,让它们全部变白。它最终还是将魔爪伸向了我的头颅,想要把脑液吸食殆尽,让我完全成为它的傀儡。但它后来不那么做了。因为它知道倘若我变为丧尸,失去了人的意识,它的肆意揉虐就没有折磨人的快感,它的乐趣还是旨在让我能感受到疼痛,感到屈辱。它让我还保留了人的尊严,好用酷刑让我觉得羞辱,它作为看客才有兴奋的成就感。于是它运用魔法让我随意变幻形状,变成畜生的模样。它在我面前嚣张跋扈,耀武扬威。我也曾哀戚,也曾祈求,也曾跪地不起。但它还是那样做了,那是它的乐趣。我因着长久的痛楚竟恨不得毁了自己。我察觉到自己在分崩离析,我没有束手就擒,我知道唯有消逝才能同它一起毁灭,才能永远获得安宁。可是能到哪里去呢。更何况,一条狗、一只猫、一条鱼那也是自己。现在你们看到了。我站在这里,枉然以人的形象,出现在视野里,从某些方面来看,也的确失去了某些作为人应有的特质。
在凉爽的春天或是深秋暖阳照耀时,它受够了皮囊里阴冷潮湿的空气,黑暗狭小的卧室,也要出来走走。这时它从呼吸里逸散,从汗水里渗透,从毛孔里爬出,探出头,感受这美好的天气,它妻儿也跟着出来了。它们在阳光下慵懒的打盹,悠闲的看着我憔悴的面孔。它们不用害怕回不去,因为它已经用我的骨骼作为支架筑造了爱巢,它们一家人都已经在我灵魂里定居了,如今我没有任何的防御能力,它们可以自由穿梭我的身体。它妻子提议说要去林间走走,散散步。它们获准让我一直尾随。林间苔藓遍地,到处还有黄白小花,那孩子牵着它们两人的手,高兴的不行。我走上前去,想要同它说说话。他不置可否,我权当是默认了。我们那时还没有像敌对关系那样仇恨对方,但我也不想像奴仆那样谦恭屈卑,我想要找他倾诉,因为它是懂我的,我只是像知己那般的聊聊天,既不让它怜悯,也不哀求,只是倾诉。我自然要说到我的苦楚和绝望,我作为人的权利,不同于畜生的特性。我从脚趾到发梢每一处被践踏过的伤痕(如今它们还有脓水流出)。我对它诉说没有任何恶意,甚至没有抱怨。我说我知道如今的自己是咎由自取,怪不了谁。我平静的说出我对未来的期望,说我还未实现的梦想。它无法沉默了,它终于忍不住咯咯的笑了,乐不可支。那副肥胖的脸颊在捧腹大笑中都快面瘫了。
我今后还会再讲诉这个没完的秘密。
我以前也在作品里也讲过这件事,不过总是轻描淡写,而我也不觉遗憾。因为我知道这是陪伴我一生的幽灵,这个恶魔小丑也许我穷其终身也未能将其详尽。我还要说说写作这件事。在压抑沉闷的日子里,在愁苦迷茫中踌躇徘徊,我常常听见它在我魂灵里狂欢,痛苦为它助兴,悲伤为它斟酌,它一盅饮罢,颜面红润,悠然自得的哼着小曲。这时候,我用笔墨描述山涧的一泓清泉,林间的陌上花开,或者是隆冬里的一捧白雪当做贡品送抵它面前,慰藉它,填塞它永不止息的胃口。写作也只有这个目的。把作品供奉给它,期望它犒劳自己,让身心得到片刻安宁。写作有时就这样担负成了不致让作者丢失尊严和自由的筹码。除此之外,对于永远发表不了的作品来说也就没什么意义。写作不是兴趣或是爱好,而是需要,是支柱,是妥协时的令牌,在它的威胁下不至到了卑躬屈膝的地步。不过,我很明白,它已经把我摧毁了,失去了成为人的勇气,否则,也不会在写作中越成功,现实中就会越失败。
然而最让我哀伤最让我痛苦最让我不堪忍受的还是它潜移默化的毒害,毫无情谊的剥夺了人活着的表征。它拉扯着我驶向暗黑的着魔之地,带我在重重鬼蜮之间穿梭,无助的徘徊在现实与梦幻的边缘,生与死都无力管辖的地界。它拖拽着我游街示众,心满意足的看着非人的人匍匐在它面前。它在那里自立为王,翻云覆雨,驾驭着我,像是脱缰野马那般带它去任何地方。我知道,它在我身上做了手脚。我被改变了,这是真的。问题就出现在眼睛上。我诉诸于言语,可是词句又是那么贫瘠。我的心里只是涌现些时隐时现的记忆。我觉得自己好像只有被包裹在沉重的暮霭里才能安心的呼吸,在暗夜的庇护下才能觉得惬意。我是墙缝间的游蛇,是下水道里的仓鼠,是彩虹上的纸鸢,总之是不能出现在地面上。我并非没有做过任何努力。可是当与人相见时,它总是用眼睛泄露我的秘密,出卖我的灵魂。透过眼睛,血肉、肝脏、心好像直接呈现在人们眼前。我是害怕的不行。你从那眼睛看到了什么:尊严尽失的奴仆被软禁在囚笼里,跪坐在它身前,而它悠然的坐在椅子上,点燃一支烟,仔细端详着他坐在地上怎样哭泣。眼睛就这样成了人们探监的窗口,成了好奇的孩子看到那么悲催的人羞辱的理由。有时候,直想痛哭,直想玉石俱焚,或者成个瞎子也好。这样除了脓黄的眼球,污浊的眼白,谁都无法窥视我眼睛了。
我必须要说明。
现在,正值隆冬时节,窗外雪漫无目的的下着。北风呼啸,雪飞扬,纷纷扰扰。冬闲的农人们百无聊赖的打发时间。空气昏昏沉沉,午后光阴被无限拉长。我躺在床上。我沉默着。在喧嚣吵嚷的呼喊中,在酒气浓郁的熏染里,我听着他那屋里酒杯碰撞声断断续续,猜拳声此起彼伏。有人吆五喝六,借着酒精的助兴畅言叙旧。那股真挚、热情劲直让你感动,仿佛情同手足、骨肉情深的弟兄。然而我早已看透了这一切。这些乡野村夫不过是大言不惭、溜须拍马的酒囊饭袋,接着酒劲像放屁一样保证答应了的诺言。他们不过是寻着酒气而来,在桌面上只为尽兴,才称兄道弟,毫无真诚可言。我想,人们常把大把时光浪费在这无聊的酒肉口水上,沉湎于虚假的幻觉,的确让人觉得匪夷所思。因为就在大家举杯的那刻很多人就已知道自己不过是逢场作戏的过客。
我想到这些,突然感到震惊:我好像一直忽略了些什么。
我意识里的暗流开始在涌动了,仿佛在寻找狭小的隘口。可是他那屋子里的喧闹扰乱了我的思绪。我看到了黎明时的曙光,一只思想的松鼠已经从洞穴探出头来。星星点点的火花在遥远的地平线上已经开始燎原了。
不。不对。肯定有东西被遗忘了。
漫天繁星被点燃了,光亮将我环绕。我躺在银河里的一叶孤舟上,我要说些什么。我留心观察过,那些客人进屋时并没有经过客厅。他们好像是凭空出现在他屋子的。我总不愿意相信他们是攀窗而入,因为那样,如果仅仅为了喝酒就太猥琐了。那,他屋子是否独自有扇门,他们也是依门而入的呢?又或者这屋子根本就没有第三间,只有客厅和我的卧室,他从未曾跟我住在一起?我这样想着,我顿时觉得世界崩塌了,眼前变成无尽的黑暗,而自己已经浮尸于璀璨的星河里了。我们一直隔墙说话,他那屋里我也未曾造访。我向来觉得虽然我们从未相见,可始终还是住在一个屋檐下。在那些困难的日子里,因为相互陪伴,还不至于孤独致死。因为就算被世界抛弃,或是抛弃世界,我始终知道,他会在我身边。可是到头来,才发觉世界并不只有这屋子和它本身。我心中有种被背叛的痛觉。我依然过着与世隔绝的日子,与生活决裂,因为执拗不肯与现世握手言和。而他也许早已离开了这屋子,和广大世界融为一体了。只有我还醉生梦死躺在这里,呆在这屋子里,因为不敢拨开眼前云翳,而躲藏逃避。
我仿佛枉度了生活,得重新思考活着了。
我此刻就站在窗前。在逝去的漫长的光影里,我见证着窗外海市蜃楼般的景色。我看到春秋冬夏依次轮回,雨雪风霜轮番交替,玩味着这窗前的众生相,这寂静与喧嚣,繁华与凄凉,落魄和漠然。我也能看到都市与森林,人潮和马群。我甚至可以幻化无形,随风飘散。愉悦时晚霞绚烂,悲伤时沉云落泪。春天我让手指如垂柳般抽芽,寒冬令白发似苍雪飘下。我可以是暗夜里温柔夜莺的一声轻啼,也能是夏日槐树鸣蝉里不经意的悲戚。我拨动命运转盘就能让时光倒流,在星云里畅游翻腾也能让它们斗转星移。我在长河里潜伏只为捕捉记忆的游鱼,有时在雪原上冰封就是等待岁月的花季。然而这一切终究美的更像是场骗局,我不能永远麻痹自己。我知道——尽管不愿承认——我从未离开过这里。
早至的黄昏带来了漫长的夜晚。酒足饭饱后,他的屋子人群散尽,只剩寂静,只剩推杯换盏后的残羹冷炙还意犹未尽的回味适才的喧嚣。他躺在床上,没有醉到不省人事,也没有睡着。因为我并没有听到沉重的呼吸和响亮的鼾声。他在低声说着每次酒醉后悔悟的话语。我看着窗外,天色还隐约透亮,雪还在下,灰蒙的屋顶上透着昏黄的雪色,让人迷醉。
“这根本不是家。这就是座监狱。”我说,“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我想离开这里。”
“那到哪里去呢?”
“不知道。可是世界那么大,我真的想看看。去哪里不行呢。”
“你哪里也别去。未沫。就在我的羽翼下呆着。这样他们就不会说你是个废人了。”
“可是我是个人。是个正常的人。是个男人。你不能这么对我。”
接着是一阵长久的沉默。我从这死寂里感到羞辱。黄昏薄暮,我依然站在窗前,看着银装素裹,地平线上还未入夜的幸福的雪城。雾霭突然稀薄了,从云缝间穿过黄昏的余光,那城市在光线里也变得虚无缥缈了。并无实体的城,在冬日破晓时的黄昏下,我好像已经看到了霓虹闪烁的街道,白雪也被印染了色彩,城市幻化成了流光溢彩的油画。
我那么看着。我想。
世界在变。而我始终如一。这让我难过。因为我已经意识到广大世界正在同我远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