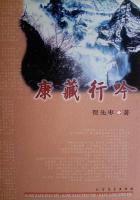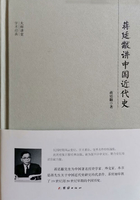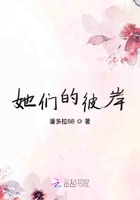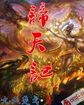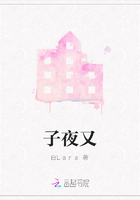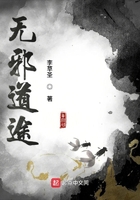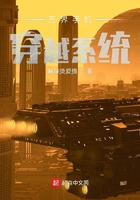这段话很有意思。最先引起我注意的是,“他的言论和著作从未引用马克思、列宁、******的片言只字”。我们这些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学生,写文章动辄引用马克思,马克思说什么,马克思这样说,马克思那样说,惟恐引用得不够多,不够全面。似乎有了引用,论文才能算是马克思主义学科的;有了引用,就足以表明自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一些人看来,有了足够的引用,作者自己就有了护身符,甚至成为真理的化身,趾高气昂,得意洋洋。陈望道的例子告诉我们,是否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否是一篇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文章,不在于引用的多少,一句不引也没有关系。
然后,我又注意到,“他从来没有标榜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这可以理解为,陈望道觉得自己还不够格,不能随便扯马克思主义的大旗。也可以理解为,没有必要如此标榜。动辄强调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有什么必要呢?是又怎样,不是又如何?不好说陈望道究竟是谦虚还是拘谨,是不以为然还是漠不关心,但看看他所写的文章,他关心的语言、文字、修辞、翻译和种种社会问题,我们大致能确定,陈望道津津乐道的是思考具体的问题,如何把问题的思考推向深入,至于自己思想的政治身份,他没怎么考虑过。“他始终是一个革命的实干家”,重要的是革命并且实干,声言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倒在其次。
这篇序言作于1979年7月13日,在那个时候,胡愈之很自然就写出了“他不断刻苦学习马列主义和******思想,以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直到最后一息”,这样的句子是那个时期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上面引述的胡愈之序言,落脚点显然是这句话。当时的读者,大概不会有我前面两段的想法。胡愈之本人,估计也是如此。他只是陈述事实,并在其时的意识形态氛围中自然地抽离出结论:陈望道不标榜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不引用马克思、列宁和******,相反地倒是不断刻苦学习马列主义和******思想。
我们在今天的语境中解读这段话,却不能不想到很多。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时候,国人中先进的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了解多少呢?也就是在翻译的过程中,陈望道率先接触到马克思主义;通过译本,其他的人们开始了解马克思主义。******本人后来承认他读过这个译本。也就是说,******是通过陈望道的译本走进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的公开提出是在上个世纪40年代中期,即使陈望道刻意学习******思想,也是那之后的事情了,何况,我们也没怎么看到他的学习报告。因此,我们不会在意胡愈之的评述“落脚点”,他谈到的事实则引起了我们的极大兴趣。
对我们这些马克思主义学科的从业者来说,引述马克思、列宁和******在所难免,但需要以研究的眼光,把它们作为研究对象看待,而非为自己观点辩解的武器。现在很多论文,都是马克思说什么了,博引一番,事情就解决了,就这样了,无需进一步的思考。这不好说是学术的态度吧。陈望道的例子提示我们,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身份和学术研究如何结合,才能既不辱没马克思主义的名声,又不误解学术的工作。
结尾问题
读书时写作文,老师常提起虎头蛇尾这个成语,字面意思是说,有那么一个东西,头大如虎,尾细如蛇,比喻人们做事情,往往开始声势浩大,到后来劲头很小,以至于悄无声息。老师说,应当像刘胡兰那样,“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后来读到“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我想,这是我所喜欢的开始和结束。
结尾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七七八八写了那么多,并非为促成结尾的到来,但结尾是必然的,作文必须有个了断,不能无休止地写下去。初写作文,大多数同学无话可说,开始没话,中间没话,结尾还是无话可说。渐渐有了兴致,倾诉的愿望强烈起来,滔滔不绝,废话连篇,自己过后读都生厌。
每个作者都有很多文章要写,读者呢,也期待早点看到结尾。几千到几万字的短篇味道不够,就一二十万字的中篇吧,若还不能显示容量,也只能长篇了,几十万字洋洋洒洒,读者还勉强能有兴趣。弄个数百万字出来,读者可就寥寥无几了。关键还在于故事情节,该多少字就多少字,就像衣服,长短自有讲究。
从开端到结尾,有时自然而然,一气呵就,水到渠成。有时写着写着就偏离了起初的意旨,等发现时已无力扭转,只好草草了结。我当年高考作文就是这样,得分较高,估计是判卷老师只看了开头,无暇审视结尾:开篇恢弘,结尾一定差不到哪儿去,不用看了。有时总也找不到通往憩息的小镇,七拐八拐,也从密林中绕不出去,但天色已暗,只能随便寻个地方,落下脚来。
结尾需要高调;结尾要画龙点睛;结尾应当具有开放性……老师举了很多范例,我们自己却总是对结尾耿耿于怀。年少的我们,怎么可能具备高超的结尾意识呢?开端容易,随便那么一想,甚至不用想,就那么开始了。接下来,就得自己左思右想,左右逢源了。
期末是一种结尾。高中时,就读于父亲工作的学校,每逢期末,同学们都回家了,我和为数甚少的其他老师的子女滞留,晃悠在空荡荡的校园里,间或走进教室,故意弄出一些响动来,驱除心底的落寞。
毕业是一种结尾。校园里穿着学位服四处留影的学生,主楼前草坪上围坐的男女,要离开校园了,依依不舍。即使下个学期继续在这个学校读研,现在也是一种过去时的心境。
毕业典礼、晚会一类的仪式隆重而催人泪下。恋人分手,夫妻离异,能有什么仪式呢?有时一段新的感情产生了,才恍然发现,还有旧情有待了断。若剪不断,就只能理还乱了。“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这首《乐府民歌》仅仅是一种追求,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悲剧结尾也凤毛麟角。“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真的有困难出现了,“人生似鸟同林宿,大限来时各自飞”。
婴儿出生后20秒钟内,会发出第一声响亮的啼哭,仿佛在宣告:“我来到了人世!”何等有力的开端啊……童年、少年、青年、壮年,一路崛起,之后开始走下坡路,老眼昏花,颤颤巍巍,头脑糊涂,意识渐渐散乱。
若把人生比作一篇作文,那么,等结尾戛然而止时,人们不是不由自主,就是稀里糊涂,难得提起笔来,写出最后的那一段,那一句。
婚姻问题
在网上看到关于结婚的帖子,自己多少有一些思考。结婚是个问题,更严格说来,是个问题域,其中包括:是否结婚;和谁结婚;何时结婚;怎样结婚;等等。在所有这些问题之前,首先还有一个结婚念头何以产生的问题。泛泛而谈,有四个因素:
外界的督促。一个人到了一定年龄,父母家人、亲朋好友乃至不相干的人,都会关切和焦急起来,似乎这个人不结婚,亲人和旁人就承担着巨大的压力,肩负着重大的使命。只有把这个人送进婚姻里面,不管是幸福的殿堂还是牢固的枷锁,只有拉拉扯扯地送进去了,周围的人们才能松一口很大的气:啊,终于了了一件事。别人都这样着急,当事人不得不稀里糊涂地忙慌起来。
朋友的影响。一起长大的伙伴纷纷成家,再也不可能像从前那样成天泡在一起,特别是节假日的时候,都回自己的小家或者大家,单身汉和单身女子不能不受触动。当同龄人的孩子喊自己叔叔或阿姨时,受到的冲击尤其严重:不成家,不为人父母,自己就始终是个孩子,显得傻乎乎的。于是,耳闻目睹过的婚姻的束缚与不幸都置之脑后,结婚成为全力以赴的头等大事。
情感的冲动。据说,每个人单独都是一个半球,到了一定年龄,他/她就会觉着孤单,寻找自己的另外一半。一些人运气好,很快找到匹配的半球,一些人运气糟,勉强找到一半,尽管不是严丝合缝,免不了磕磕碰碰,但总归是不孤单不寂寞了,于是选择将就,成就婚姻,把磕磕碰碰经常化、日常化、终生化。
欲望的驱使。所谓的爱情里,爱与欲始终难解难分,究竟是爱引发欲望,还是欲望促成了爱,莫衷一是。爱情至上论者相信有一种纯洁的爱,尽管最终落实在欲望的满足上,但源起绝对和欲望无关。欲望先在论者以为欲望是爱的生理基础,把唯物主义原则贯彻到爱情里,很容易承认欲望第一、爱情第二,没有欲望何来爱情。动力和源泉也罢,目的和归宿也好,欲望终究是无法回避的。为了欲望的合法化,婚姻成为堂而皇之的理由。
作为问题域的结婚问题,既是说结婚是个问题,也是说不结婚是个问题。在谈过结婚成为问题的由来后,接着谈谈不结婚问题的缘起。
在年青的一代中,迟迟不结婚的人越来越多。粗略说来,有五个因素:
外界的淡然。社会的发展愈来愈趋于多元化,结婚与否只不过是个人问题、私人问题,旁人乃至家人都不再过多地关注,当事人少了外界的推动,自然轻松了许多,那份由外界引发的焦虑消失殆尽。于是,不结婚成为不是问题的问题。
朋友的影响。周围朋友一个个兴冲冲地闯进婚姻的围墙,免不了吵吵闹闹,至少失去了单身的诸多自由,天色晚了得及时回家,稍一不留神做了父母,更是不得不老成持重,负重蹒跚。幸好,自己的脚还在围城之外,赶紧打住。
情感的漠然。或许是从小生活环境的缘故,年轻一代愈来愈活得自我,依然有爱,但很难寻死觅活的刻骨铭心;依然有情,但很难曾经沧海难为水,没有什么不可以变化,没有什么不可以遗弃。爱都没有了,堆放爱的神圣殿堂也就不必造就。
欲望的弥散。随着社会的开放,欲望越来越不是问题,放纵的渠道多种多样,不再需要婚姻的庇护。不只是没有婚姻的欲望宣泄是正当,没有爱的欲望表现也是正常的。
经济的压力。婚姻意味着家,随着社会生活需求的整体提高,家意味着一套属于两个人的房子。房价一路飙升,婚姻的成本大幅度增长,一些年轻人恐惧于“房奴”的前景,一些年轻人连当“房奴”的资本都缺乏,没有空中楼阁,婚姻就没有安身之处。
没有压力也没有动力,婚姻的内在价值和意义被一层层地剥离,当一些人还在为结婚是个困难的问题忧虑时,对另外一些人来说,不结婚根本不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