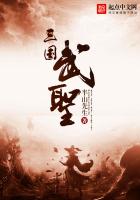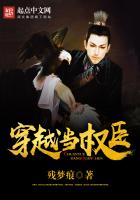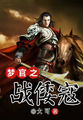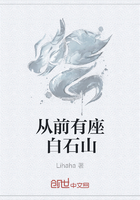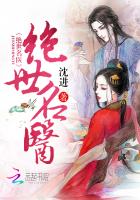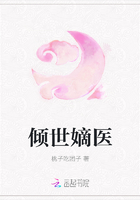第一节商贸交往
1949年以前,渔业生产是京族人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有关的调查表明,1949年以前江平一带绝大多数京族家庭每年的生活费用中约有70%以上依靠捕鱼。这样的经济生产活动类型决定了京族对外经济交往的需要更为迫切,因此,京族人很早就有了商贸活动。
因与越南越族同源同宗,京族有与越南进行经济交往的传统,与越族的商贸关系较为密切。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年代,商贸活动主要是互通有无的以物易物方式。到了商品经济活动较为频繁的清末,有的京族小商贩还利用他们的优势经常跑到越南经商,但人数不多。一些近代文明词汇,也是那时从法语传入越语再传入中国京语里来的,如“肥皂”、“毛线”等词。从这些词语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京族和越南越族商贸交往的状况。1949年以前,澫尾、巫头等地就有不少京族村民到越南芒街等地经商。1950年代至1960年代,虽然国内政策对边境贸易多有限制,但京族和越族边民之间的贸易往来仍然没有中断。而即使是在1979年中越关系严重恶化期间,京族地区也仍然有人到越南边境地区贩卖商品。1989年,中越边境贸易重新恢复,由于京族人与越族之间不存在信任障碍,占有天时地利人和优势的京族人成为边境贸易的最大受益者。
因为江平集镇、东兴集镇的商贸比较发达,京族与这一带的汉族人的商贸交往也很密切。清末,不仅有广东、福建和越南的商人来到东兴与京族人做生意,也有不少京族人到东兴从事商业活动,做小商贩。江平镇是离京族聚居区最近的商品集散地,更多的京族人则是每到街圩,涉水而来,用鱼产品和汉族、壮族等换取粮食、日用品等生活必需品。京族与汉族密切接触、京族人当中出现不少双语人,正是从集贸市场的讨价还价开始的。抗日战争胜利后,有的京族商贩在江平镇购置房屋经营小本生意。如当时江平镇有5家经营鱼汁的商店,其中有4家就是由京族的小商贩经营的。京族人的双语使用情况更加常见。
由于京族地区的商品销售渠道不畅,1949年以前京族地区渔业产品的销售价格较为低廉。一些老年村民说,一斤鱼还换不到一斤米,在当时是一件极其平常的事。因此,尽管鱼产颇丰,但京族人的经济收入普遍较低。京族渔民家庭的经济开支,主要用来购买粮食。除恒望、红坎、山心,大部分京族人聚居的村庄由于土地贫瘠,大米、玉米、红薯、木薯等粮食作物不能自给,只能从集市买入,价格往往比较高。而居住在山区的汉、壮、瑶等同胞,由于交通不便,与外界来往甚少,自产农产品但缺乏鱼虾、海盐等海产品,这和京族的经济生活形成了互补。一些京族渔民肩挑海产品,游走于附近山区的大小村庄之间,以咸鱼干等换取山民的大米和木薯干。由于同样缺少现钱,在部分京族渔民与当地山区农村的壮、汉族村民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以鱼产品换取粮食的以货易货形式。这种只求获取所需而没有过多赢利目的的商品交换形式,不仅使当地农民和渔民能够各取所需,同时也免去了以货币作为流通工具所带来的种种不便,密切了京族人与山区的汉族、壮族、瑶族的商贸往来。
解放后相当一段时间,由于各种政治运动及边境战事等影响,京族与外族的商贸活动非常稀少。改革开放后,京族聚居区的商贸活动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市场经济的浪潮也席卷到了京族聚居区,京族人与外界的商贸联系日益增多。与传统的纯渔业捕捞相比,改革开放后海产养殖、海产品加工等新行业得到了发展,京族人与外界的商贸活动比以往更密切、频繁和深入,不仅与附近的各族人民开展了贸易活动,有的甚至还把业务拓展到了港澳台等地。边境贸易的升温,京族人发挥精通越语、有亲戚朋友在越南居住、了解越南情况的优势,充当边贸经纪人、中介人,与越南越族人的边境贸易成了京族人的龙头从业项目。经济学家指出,语言是贸易中最有效的交际工具,与说相同语言的人最容易发生直接的贸易关系。越南人做生意喜欢与京族人直接联系,而且也比较信任京族人。在边境做生意的还有其他民族的商人,但一般总是先由京族人用本民族语言与越南商人商量好后,再由京族人与外族商贩洽谈生意。除了充当翻译和中介,京族人还从越南采购国内所需商品运回国内销售,又将越南市场需求的商品,通过陆路、水路运到越南销售,直接加入了边境贸易的行列。京族的族际商贸往来,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达到了历史最高值。
第二节族际往来
一般地讲,由于社会制度和所实行的政策不同,民族关系也随之具有不同的本质和内容。京族与外族的族际往来,以1949年为界。在此之前的族际关系,因为剥削制度、阶级因素、历史遗留问题等原因,呈现出较为复杂的状况;1949年后社会主义制度的推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政策的实施,京族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则较为融洽、和谐。
一、和汉族的往来
京族来到现今的聚居地之初,由于海水阻隔,与大陆上的汉族接触是非常少的。京族人以近海捕捞作为主要生产方式,打到鱼后,就会拿到江平集市卖。在集市上,才与汉族人民产生有限的接触关系。因为民族间的经济生产方式是互补的,因此,京族与汉族交往存在互利互惠。
当然,一个民族不可能在封闭的环境下发展,一些村落,如恒望、潭吉、红坎、竹山等地都是京、汉族杂居。在阶级社会下,阶级制度的存在对民族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总会产生影响,各种社会关系(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及其它各社会集团之间的各种物质的、政治的、道德与法律的关系等等)是相互交错、互相制约的。
京族一直打渔为生,较少耕田或经商。京族人种植水稻是向周边的汉族学来的,后来还从汉族那里学来了煮盐技术,而汉族也从京族渔民这里学到了渔业生产的不少经验。这是京、汉两族人民友好互助的见证。
解放前,京族人由于经济落后,因此不得不向经济宽裕的租用一些生产工具。如在江平,就有一些汉族人出资购买包括渔网、竹排等捕捞工具,然后租给贫穷的“不会打算”的京族渔民,京族渔民打到鱼后就得按“东家”定的价卖给他们,而且在计量上往往受“东家”的牵制。另外,不少京族人自小即给汉族地主或财主打工。在阶级社会,经济剥削方面是不分民族界限的,但是这些有钱有工具的“东家”、地主、财主,绝大部分是当地汉族,因此,在经济关系上,部分汉族上层小资产者与京族普通大众之间实际上形成了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一旦关系紧张,很容易就和民族压迫等敏感问题联系起来。
在政治上,汉族官僚阶层与京族普通群众之间相当程度上表现出统治与被统治,压迫与反压迫的不平等关系。
国民党统治时期,相对于汉族,官吏们总是对京族群众征更重的捐税,如“用粮赋税”、“渔盐海税”、“人丁税”、“过秤税”、“乡保长米”、“自卫班长”等,可谓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无奇不有。这是京汉不平等关系的一个表现。
随着人口压力的增大,汉族人也陆续来到了原先只有京族聚居的海岛上。虽然京、汉族人民一起共同开发了这片土地,但是,公共资源是有限的,后到的汉族人,为了生存,便凭借人多势众,利用各种手段巧取豪夺原属于京族人的山林、耕地、农田。因此械斗时有发生,出现伤亡事件。而官府又往往站在汉族人一方,引起了京族群众的不满。为保护京族的居住地,京族群众团结一致,曾在澫尾的东西南北各方位划出界线,作为京族人的“保留地”,汉人不许侵入。而在20年代,京汉两族人还曾为山林归属纠纷打过官司,后来在岛上立了一块界碑作为林地及居住地的界线。国民党时期,原来属于自然领袖的“翁村”,有一些变成国民党政府任命的乡长、保长、甲长,其性质因此产生了变化,也被利用作为统治京族人民的工具。而且,当时分保、甲完全按民族居住区域来分,实际上是进一步把京族与汉族隔开。这是认为制造民族隔阂的表现。1948年12月,国民党江平联防主任、恶霸地主黄某,指挥其保安团中队长邓某,借捉共产党为名,在山心岛上捉去京族青年共30多人进行威逼吊打,勒索钱财。在尾村,1948年12月,村长、副保队李某,勾结惯匪陈某假冒共产党,洗劫了尾岛京族人民的财产,还绑架了吴世隆等人勒索钱财;过了几天,他们又把巫头岛的京族人民洗劫一空。这些来抢劫者都是汉族,而且他们只抢京族而对旁边的汉族却不动分毫。这样,给京族群众以“汉人专门欺负我们”的感觉,加深了京族与汉族之间的矛盾。
在私有制和阶级社会条件下,剥削阶级中的反动统治集团为了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总是挑起民族纠纷,唆使各民族互相残杀,以实行其民族压迫剥削政策,这就造成了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不平等、不团结的关系。而在面临外敌入侵的情况下,京、汉两族人民往往团结起来共同战斗。如19世纪末法帝入侵,京族人民和汉族人民一起参加了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转战边疆,在共同的战斗中是不分京族汉族壮族的。在国民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共产党人倡议并实行民族平等、反对大汉族主义的政策,深得民心,不少汉族、壮族、京族人民直接参加了防城(今广西防城港市境内)起义、镇南关(今广西凭祥市友谊关)起义、钦廉(钦州和廉州,现广西北海市境内)起义等,很多人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共产党领导各族群众在防城、江平一带进行革命斗争,京族人民与共产党游击队、工作组密切配合,反抗官僚恶霸,从而与共产党政府、汉族同胞种下合作谅解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