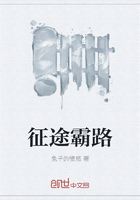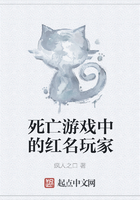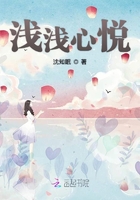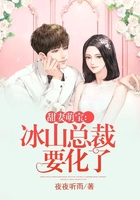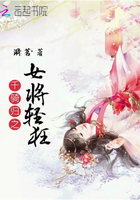第一节民族教育发展
一、古代时期的教育
赫哲族古代时期的教育还萌芽在家庭教育之中。在这初级阶段,教育这个概念还不十分显现,人们只朦胧在家庭自然的传统教学环境里。父母言传身教子女怎样捕鱼、打猎、削木、裂革插草记事等,这些简单的学习行为,即说教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模式,也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进行,这一时期便是教育的萌芽时期。
二、近代时期的教育
在清朝末期,赫哲族教育只有在官吏和比较富裕的人家流行,而可供他们上学的学校比较少,只有在松花江沿岸的噶尔当、苏苏屯、大屯和乌苏里江沿岸极少的村落设立学校,而赫哲族的子弟因贫穷而上不起学,只能随父母下江捕鱼上山狩猎。公元一九〇七年(光绪三十三年),苏苏屯赫哲人捐助出长三十六丈、宽二十丈“宅基地”并要求政府办学(《黑龙江史志》1984年第二期第36页)而被获准创办了赫哲人自己的一所小学。赫哲族流行病学专家毕天民就是在这个苏苏屯自己家乡的小学念书并在后来成名的。
民国初年,街津口村就有了小学校,据在此上学的汉族学生吴德喜讲,还没有赫哲族子弟在这所学校上过学,后来这所学校毁于战火之中。
三、现代时期的教育
一九三七年(日伪统治时期)街津口村成立了小学。在二十几名学生中,赫哲族学生占二分之一,但都是穷苦人家的孩子。日本侵略者强制学校增加日语课。这使学生们非常反感,人们经常这样流传着:“日本话不用学,再有三年用不着”,由此可见,他们对抗日胜利的到来充满信心。
一九四五年街津口与东北全境一样都解放了,但当时小学在动乱中停办。全村村民在迫切求学的愿望下请了一位姓孙的老师教孩子们上学,这时全村供老师伙食又另外凑给老师报酬为条件的私塾教育。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黑龙江畔的勤得利成立了小学,于成敏先生担任第一位校长。这所学校共有38名学生,其中赫哲族学生八、九名。第二年街津口村正式成了民族联合小学。共有二十六名学生,其中有十二名赫哲族学生。紧接着,八岔和四排在一九五二年也成立了民族小学校,此时,赫哲人重获新生,翻身当家做主,赫哲人民的子弟也有了上学的权力读书的机会。学生们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努力学习,刻苦用功,学习的热潮很高涨。
从此,赫哲族的教育逐步走向正规化。一九五九年,国家拨专款二千多元为四排村盖了一栋草房校舍。一九六九年,街津口、八岔两个赫哲族乡中心特设了初中班,一九七八年又增设了高中班,统称为中学。一九八一年又撤消了高中班,这些根据上级及教育部规定而施行的。
到一九八九年为止,国家拨款为街津口、四排、八岔三个民族乡建砖瓦结构的校舍共2630平方米,栅栏围墙980延长来,并购置了常用的教学仪器和体育器材。此后,国家在每年还发给赫哲族中学生70元,小学生10元的助学金。与此同时,国家还在每年发给各乡学校民族教育补助费。在此大好形势中,幼儿班、学前班应运而生。在中考和高考国家对赫哲族学生采取降低分数线标准,目的是为了使赫哲族学生能够有更多的机会深造,培养更多的有知识、有文化、懂科学、有觉悟的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参加祖国各项事业的建设。
为使赫哲族学生有更广阔的学习机会和建立民族系统的教育体系,快速培养民族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特增设省民族中学,民族师范学校、中等专业学校和省民族干部学院等。
四、当代时期的教育
现在街津口、八岔、四排三个赫哲族民族乡的学校均实行赫哲族中心学校体制,是具有小学、初中班为一体的教学范围。
迄今为止,国家均已将三个赫哲民族乡中心校舍建为砖瓦结构的教学校舍,其中有街津口赫哲族乡中心校新建的三层结构的教学楼,约一千多平方米,八岔赫哲族乡中心校的三层砖瓦教学楼,约六百平方米。改善了办学条件,为赫哲族教育发展提升了一个新的台阶。
在教学质量方面,据“三乡一村”的赫哲族中心校提供的数据资料统计,赫哲族的适龄儿童入学率已达到100%,小学学年升学率达到90%,初中学生升学率达到95%,普及率达到100%,巩固率达到99%,教学平均质量上升。近些年,赫哲族学生每年都有十几名学生考入全国各大院校。据有关资料统计,现在在各单位工作的大学生已有34名,其中如全国十一届人大代表刘蕾(佳木斯大学),同江市副市长尤利军(中央民族大学),街津口赫哲族乡政府秘书孙俊梅(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等。
如今,各地赫哲族学校的教学设施都已完备,从黑板到实验设备,从体育设施到办公用品都达到了现代化水准,尤其是赫哲族学生的教学程序中都已用上了先进的电脑教程。
现在赫哲族中心校都已开设了一门新的教学课程,这就是为继承发展赫哲族民族文化,抢救赫哲族濒临失传的赫哲语言,专设了一门赫哲语教学课程,如街津口赫哲乡中心校赫哲族教师毕立勇提议下由其主教赫哲语教学教程。教学课程从小学开始,这样使学生记忆牢固,易懂易学,为传承发展赫哲族文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二节民族文学创作
一、赫哲族民间文学创作
赫哲族民间文学的创作也就是口头文学创作,口头文学主要是用赫哲族传统的“伊玛堪”的说唱形式表达出来,创作者主要的思想和意境是传扬民族历史、歌颂伦理道德、崇尚英雄人物而抒发情感、教育后代、开发智力等涉及社会各层面。其内容反映了赫哲族在旧社会精神生活的各层各面,如对英雄和亲人的纪念,对萨满和神灵的崇拜及对正义和爱情的热烈追求,对幸福和光明的无限想往,对大自然的热爱、恐惧、憎恨等等。口头文学在不同时期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创作者,不同时期的创作者有不同的思想和世界观,他们在捕鱼、狩猎的劳动过程中所经历的事件和感悟的思想及在劳动中对真善美追求的灵感的闪现和浪漫的幻想即是口头文学创作的源泉,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和世间的动物。赫哲人认为“万物有灵”,因而,睹物思人,触景生情是赫哲人口头文学的创作想像的翅膀,成就了“伊玛堪”脍炙人口的篇章。如《木竹林莫日根》《木都里莫日根》《希尔达鲁莫日根》。
二、赫哲族戏剧家乌白辛的文学创作
1963年,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在全国公演后,这部电影便乘着《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歌声红遍祖国大江南北。然而,它的编剧乌白辛却一直不被人注意。直至文革开始,这部电影被点名列为“毒草”,而作者也随着这株“毒草”走进了历史,走完了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不朽的艺术总是不能埋没在过去的尘埃中的,“文革”结束后,《冰山上的来客》重获新生、又红遍神州大地,久映不衰。它的编剧,这位很有才华的赫哲族着名戏剧家乌白辛也越来越被人们所熟知,成为已故的文坛巨星。
乌白辛(1920~1966),原名吴宇宏,赫哲族,祖籍乌苏里江支流毕拉河畔的红石子村。十七世纪中叶,其父随同祖父一同迁往吉林省响水河子经商。乌白辛出生于吉林市松花江畔的西关果木园胡同4号,一个用木栅栏围成的小院子里。青少年在吉林市和立文中学读书。他在剧团当过演员,后参加革命,在东北民主联军先后任记者、文工团编剧、副团长。参加过抗美援朝。五十年代在“八一”电影制片厂任编导,先后到新疆、西藏等地采访,他的足迹遍湖南、广东及帕米尔高原、昆仑山、冈底斯山、直至喜马拉雅山,采写了大量的随笔和散文,并创作了着名的短片《在帕莱尔高原上》《风雪昆仑驼铃声》等纪录片、艺术片,并由此写下了着名的红色经典影片《冰山上的来客》,正当他精力充沛创作正旺的鼎盛时期,正赶上文革可惜这位很有才华的赫哲族戏剧家不幸在“文革”时被“四人帮”迫害致死,年仅46岁。
1958年乌白辛从八一电影剧片厂调入哈尔滨话剧院是他主要的创作阶段,使他的创作进入黄金时代。他先后创作了话剧《印度来的情人》《黄继光》《雷锋》、歌剧《映山红》《焦裕禄》和电影文学剧本《冰山上的来客》及散文随笔《从昆仑道喜马拉雅》和诗歌《九月的歌》《南行草》等。
由此可见,由于乌白辛没有生长在赫哲族聚居的地区,远离族群,而且他的青壮年时期又在非赫哲族中走南闯北,因而,他的创作题材几乎是非本民族题材,这是生活环境所决定的,但他以热情、诚挚的笔触讴歌了祖国各族人民的辉煌的发展历程。据有关资料得知,乌白辛曾在六十年代初到过他的祖籍乌苏里江及其他赫哲族聚居区采访,话剧《赫哲族婚礼》(1963年)就是采访回去后创作的。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部关于赫哲族题材的话剧作品。他的成名作,电影文学剧本《冰山上的来客》是他文学成就的顶峰,将伴随着他永远在人们心中闪亮。
三、赫哲族作家孙玉民的文学创作
1.作家介绍
孙玉民(孙木恩,玉民)赫哲族,中共党员,当代唯一的赫哲族作家。他是赫哲族有史以来唯一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
1961年1月17日,赫哲族作家孙玉民出生在全国赫哲族人口最集中的同江市街津口赫哲族乡。他的祖父孙木恩,明远是街津口第一户人家,那时父亲孙有喜兄弟五个,结婚四个。孙玉民自幼与父母生活在“哈拉莫琨”氏族的这个大家族地氛围里,给他打上了深深的民族烙印。青年时期捕鱼劳动的生活经历,给了他浓郁而丰富的生活体验,积累了丰厚的创作底蕴,他的文学创作始终根植于本民族的土壤中,这使他的文学创作带有浓郁的民族色彩和迷人的艺术魅力。他的创作成就早已代表着一个民族在国家级文学创作水准的高度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中国文坛上是一颗冉冉升起的东方红星。在56个民族中是56个闪耀的星座之一。
赫哲族作家孙玉民是赫哲族有史以来第一个本民族作家写本民族题材的唯一的一位作家,他创作的小说《乌苏里船歌》(《北方文学》1997,6)是赫哲族有史以来的第一篇小说,他是赫哲族文学的拓荒者、领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