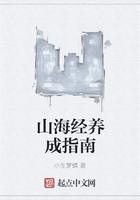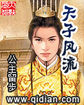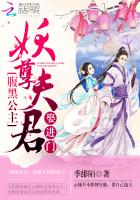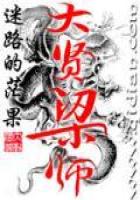自古以来能医百病的大夫几乎没有,无论是扁鹊、华佗、李时珍和皇甫谧,真正会治病的医生只是专治一种病症,或在专治某种病症时捎带着医治一些与己专长有关的病痛。但奇怪的是,仅仅能医好一种或几种病症的医生,人们就会称之为神医,冠以妙手回春的美誉,甚至名留千秋。
古人说:“有病乱求医。”当一个人深受病痛折磨,百无聊赖,便会不惜代价,四处寻访能够祛病排忧的人,哪怕只有一线希望。其实真正会医病的郎中不单单在药方上下功夫。“七分化解三分治”,好的大夫往往会把调节病人的心理放在首位。中医讲究“望、闻、问、切”,在完成这四个程序的过程中,会医病的大夫已经了知了病人的心绪,建立起信任关系,耳濡目染、肌肤相触、排忧除惧、体恤鼓舞,已使药力增加了数倍,所以有的病人看过大夫,药还没服,病已好了大半。人们议论大夫的好坏、医术的高低,首先谈到的不是他的药品,却是他的人品和医德。痛在身上,病在心上,就是这个道理。
至今,记忆犹新的是我曾怀着切肤之痛,抱着自己受伤的女儿去一家医院急诊。女儿唇上的伤口须缝合七针,三寸长的钢针在我眼前一晃,吓得我直出冷汗。可大夫为了不损伤孩子的智力,动员我不使用麻药,我还在迟疑,大夫却早已与我的女儿建立起克服疼痛的攻守联盟,女儿点头同意不用麻醉。终于,我看到我那只有四岁的女儿,噙着眼泪一声未吭地配合大夫缝好了伤口。而且为了保证伤口的正常愈合,女儿遵照医生的嘱托,半年没有开怀笑过,也没有咧嘴哭泣,甚至吃饭都小心翼翼,各种情绪都以眼神来表现。
有这样的医生,才会有这样的病人,有这样的病人才能成就一个个名医、神医。
今天,来到宁夏海原关桥乡马湾村,看着这座孤立沟边的虎家堡,听到它的主人是一位神医时,我便联想起有关医术的这些事。当我知道这位被誉为神医的虎贤清老人活了91岁,去年农历九月十八已去世时,我顿时心生懊悔。我前后四年五次来到这里,竟没能去海原县城拜访这位老人。追究原因,并非因为我懒惰,而是这样的土堡在西海固不计其数。这座,只是其中渺小的一个。正是今日得知这座古堡是一名受人敬佩的医生的个人堡宅,我才决定选录入本书的。
记得第一次探看这座土堡时,我直接驾着轿车进了与它一沟之隔的村子,得知这里是马湾村第六组。当时一位妇女正从自家水窖里打水,我没有来得及打问土堡的事情就被她指到了村东的一条咸水河边。那根本不能称为河,那只是一条黑湿的滋泥中淀出的几个水泊。水泊周边有些许牲畜踏出的蹄窝,估计这水只能饮牲畜,或者像那位妇女说的,连牲口都觉得苦涩。第二次是春天,我刚步行到土堡前,就遇到了一位放驴的小伙,他跟在我身后,不远不近,不快也不慢,使我很局促。问他这土堡空了有多久,曾经有没有人住过,我所有的问题他全用一句话来回答:“这是我们村的堡子,不许别人来住。”我准备照几张相片作筛选的资料,他却一个劲挡住镜头,而且牵来毛驴,让我为他照一张骑着骏马冲锋陷阵的纪念照。可惜我把那些叱咤风云的照片背过他以后就删了,不然还真能看到这位勇士怒目扬鞭的画面。第三次是正值隆冬,白雪皑皑,我突然觉得自己站在沟壑边可能有滑下去的危险,我打了一记寒颤,就转身离去了。第四次是一个春天,地里已经有了稀稀落落的绿色。我走进一家农户的院子,这户人家敞开的院落里,母女俩正给牲口铡草。她们专心致志地配合着,铡刀在女儿手里一起一落,麦草在母亲双手输送下一茬一茬从刀刃下吐出来。干旱习以为常,苍凉的原野,静坐的土堡与她们鲜艳的衣着和节奏分明的动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今天算是第五次来到这里,也是得知这座古堡的主人是位神医的缘故。四年来,我走遍了西海固这片特殊的土地,不但增进了理解,而且感情越来越深。我知道,清末以来,有钱有势和有地位的人家大多都建有自己的土堡,穷苦人家为了自卫也都集力合资筑建了堡子。唯独没有见过这种钱财并不很多,地位不高不低,更无良田的医生所筑建的私家古堡。听说这位医生还真做过一段时间的“地主”,后来又被平了反。这样的命运转徙也许正是因为这座土堡吧。
听说这位医生儿孙满堂,也曾有个民国时期上大学的弟弟和几位进城工作的儿子。听说这座土堡农业合作社以后只作过一段时间的菜园子。
把这座土堡选入《失守的城堡》,不知他的后人们愿意不愿意,我想他们应当是愿意的。一则堡内现在确实没有住人,南边的堡墙已半壁颓下,如此下去,终会成为废墟。二则立字为据也算是怀念故人,钦佩先辈的壮志,敬叹古垒的风范。
到此,我该停下来想一想,已好些年没有听见神医这个词了。也许这个词会随着药疗设备的不断更新而慢慢消失。我还得纠正一下前边对这位老堡主的尊称,他不信神,他敬奉真主。
独行马海湾
庸医施药
良医用心
你莫非是传说中神医的女儿
在切药——“嚓,嚓,嚓”
其实,是药三分毒
其实,每一根草芥都有心
——请别柔肠寸断,请别让潮起潮落的人群
带着伤——
我三番五次揭帘
我三番五次捧起药丸,养大的心灵
这也许是一种独有的病症
无法喂养的虐疾
无可救赎的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