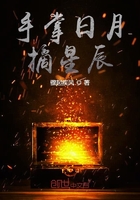有等的人,有等的理由,等其实就更难熬。难熬里又是一半欣喜一半忧虑,怕要等的人等不到,或者是等到了,自己没看到。四点过后,落了雪的地面格外好看,是一层粉底,把坑坑洼洼的地方磨平。她张着眼睛,不愿错过每一粒雪花,更不愿意错过每一个路人。那会儿出现在街上的都是清洁工,已经开始扫雪了。天空是黑,又是灰,是蓝,还带着一点靛色,雨雪洗刷污垢,空气过了一遍放大镜,越发透明。明月浑身都是冷的。尤其是腿,冻了半截儿,她站一会儿就蹲一会儿,耳朵上也起了红疙瘩,她把手机调到最小音量,借以保存电量,然后把耳朵对着扬声器,听主播说话。她一路就是这么听来的。
五点半的时候,主播关闭了点歌通道,说他六点就下班了,随后广播里传来《摇篮曲》的旋律。明月手机自动关机了,她赶紧往当初相遇的那个路口去。路口还是原来的路口,只不过盖了雪,又不那么像当初的路口了。她站在路边,在灯下来回踱步,看着马路的两头。这个季节,他还会骑自行车吗?可是下雪又冷,路又滑。她又怕等不到他。这样的情况发生过。正这样想着,两束灯光打在面前,有辆车停在面前。她以为挡了路,正避开,这时又响了两声喇叭,那个少年从车窗里探出头,叫她。
他一张口,她立马就认出他来了。对明月来说,耳朵比眼睛敏锐多了,人的相貌可能随着时间不断改变,但声音,过了变声期之后,大体是变不掉了。所以他的声音对她来说,像是共鸣,记忆还没识别出来,但身体已经不由自主地走向他。他的面容在模糊的清晨中也模糊着,她迟疑地看向他,看到了那张围在围巾里的笑脸。
她顿时心里泛起一阵暖暖的火光,语调自然而然地轻松起来。她的嘴巴冻了大半夜,张了两下,才张开嘴,第一次没说出话,第二次才转动舌头,打趣了他一句,说他发财了,换车了。对于再次相见,明月在等他时酝酿了无数次重逢的对话,可结合到现实里,一句跟不上。再次相见并没有什么尴尬。虽然中间也有沉默,但那沉默不会让人感觉不自在,相反,明月觉得是一种很惬意的冷场。完全不用掏空心思说些什么。
他打开车门,让她上车。车里很暖和。很惬意。她忽然想起今天还有工作去做,但转念一想,她都替别人好几回了,别人也该替一回了。她坐在少年旁边,窗外依次掠过去大楼和街道,昔日单车穿过午夜街道的那种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一到熟悉的感觉前,她就有些肆无忌惮,甚至是任性,从说话到动作,都完全释放开来,一会儿摸摸这个,一会儿摸摸那个。他让她别动,系上安全带,她不听。等他叹了一口气,露出疲惫的面容,她连忙照做了。
一路上明月想说的话很多,但是都说不出来。本来主动准备,变成了被动应答。人是两年前的人,话题也是两年前的,仿佛这一两年时光是她们成长的真空期。他们都避而不谈。谈的只有现在。明月说着说着,说漏了嘴,把等了他一夜的事说了出来。他责备了她两句。她知道他是在意她的。自从母亲去世后,她没有听到任何责备。她长这么大,发现责备其实是带着感情的。只有在意,才会当面指出来。真正的厌恶,是无动于衷,是笑脸相逢。她听着他慢慢地责备自己,忽然很感动,一时想起母亲,泪花在眼眶里搅来搅去。
他把围巾绕下来,搭在她的脖子上,让她系好。那动作是带着温度的,围巾也残留着温度,那温度加在她身上,从心开始往外暖。她脸红了。她的心不平静,和狂躁时候的不平静不一样。她越发为昨夜劈头盖脸的一番话感到羞愧,于是她低下头,轻轻说了一声对不起。可他没听见,而是兴高采烈地看着外面的早餐摊,停下车,请她吃早点。她卖了几天早点,对那味道有些排斥,再加上在外边呆了一夜,其实她有些发烧。虽然没有咳嗽,但脑门那滚烫的温度,她是能感受到的。这一回上车下车,忽冷忽热,她觉得烧得有点迷糊,反应不仅迟钝了,而且喉咙里像卡着什么,想吐。她怕他看出异样,一直说话盖过去。可他觉得她是拘谨,一定让她喝粥。她实在是喝不下去。知道他上了一晚上的夜班,不想看他皱眉头,明月抓起碗,囫囵喝了两口,憋在嘴里,生生咽下去。他看到她的样儿,缓缓笑了。
两个人都没有吃多少。重新坐上车,她躺在副驾驶睡了起来,脑袋一直偏,一直偏,最后落上他的肩。她整个人病着,再加上困,睡得死死的。她做了梦。这个梦不怎么快乐,不然被叫醒的时候,为什么眼角一片湿呢?原来是到了地方了。这是两年前白老大腾给她的屋子,两年过去,这个小区更老了,他的记忆力很好,两年的路线居然没有错。可是他忽略了,明月已经不住在这个地方了。开始说的时候,他以为她开玩笑,等听她说完了,又揉揉肩膀说:“那为什么不早说!”
她忘了。她睡着了。她心里也不舒服。因为他皱眉头了。他一定是累了。她不想给他添麻烦。害怕他因此讨厌她,从此之后再也不理他。于是这次一点迷糊不敢犯,睁着眼看着导航上交叉的路线。
“做什么梦了?”他问她,眼睛盯着前方。
“梦见我的猫跑了。”她记不起梦境,随口胡诌。
“没事的。”他一如既往地安慰她,“梦境都是反的。”
说了一段路的话,导航提示到了目的地。
明月抬头看看周围,发现到家了。心里有些舍不得,但得赶快下车,他很累了,不能再折腾他了。路边排满了车,车盖上都有一层薄薄的雪花。他把车停在最前面。等到车定下来,明月打开车门,想了想要解下围巾,他却说:“外面冷,你围着回去。”明月走得很磨蹭,他怕走错了,问她:“这次没错了吧?”
“就是这里。“她答道,然后来来回回挥了几次手。他也笑着回应,并说:“记好啊,大晚上的,外面天寒地冻,别出去溜达了。睡不着,就听我的节目。”
她缓缓转身,点头。头重脚轻,走道儿有点颠倒。心里总有点不甘心,听见他汽车发动的声音。她又转过身,问他的名字。因为她忽然想起来,她们见过这么多面,却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他有些意外,又带着一丝责怪,只不过,这一次没有皱眉毛:“你看,你果然不听我的电台。每次开头、结尾我都介绍说主播晨星,主播晨星的。”
“晨星,晨星。”她在嘴里念叨了两句,“这是真名吗?”
“有什么奇怪的?”
“真巧。我叫明月。咱们一个星星,一个月亮,组成一起,是不是就是一个星空?”
她说完这一通话,脸又红了,这次不是害羞,纯粹是烧的。怕再待下去就倒在这儿,她迈开腿就往回跑。一口气跑回住的地方,踢了鞋,扒了外套就钻到被子里。浑身都是冷的。她抱着自己,像是一团不会化的冰。四肢都硬硬的,冷冷的。闭上眼就睁不开。在半睡半醒里,她忽然又想,自己忘记要他的电话号码了。她一觉睡了很长很长时间,再醒来,四周已经是漆黑一片。烧还没退,咳嗽又来了,浑身都像被抽空了一遍,轻飘飘的。她打开手机,没电,充了会儿电再开,发现有十多个未接来电。她认得那号码,都是同事的。自己无故旷工了,她打电话来很正常。还有一个号码是北京的,但她不记得和谁有过交集。她就想,也许是晨星的。打开手机,果然又看到这号码发来的一条短信:“到家了没?”
她一阵窃喜,又一阵疑惑,他是怎么弄到自己号码的?想了想,昨夜点了歌。她缓缓站起来,喉咙痛得呼吸一下都肿着疼。摸摸兜,不知怎么丢了一个钥匙坠儿。可惜了唯一的一张照片。她还记得是十五岁生日的时候,母亲带她去照的。但也庆幸丢的只是钥匙坠儿,如果丢的是现在这房子的钥匙,她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她先给同事回过去电话,同事得知她的状况后,好言安慰了两句。明月睡了一天,肚子饿透了。先喝了点热水,又找了两包方便面,就热水下了,在里边打了两个鸡蛋。煮面的时候,她给晨星回短信:“我到家了。不用担心。”
很快,那边的短信又回来了:“你是在楼道走了一天才到家?我以为你走丢了。”
她能想象到他发短信时候的表情。她开心地笑了笑,又咳嗽了几声,准备回:“死不了的。”想了想又删掉了,改成:“我就是睡过头了。”
发过去短信,她忽然长吁一口气,这是第一次,她这么在意自己的措辞,她开始怕。怕他皱眉头,怕他生气。怕他不理自己。以前完全没有这样的担忧,可是现在有了。她渐渐喜欢上他了。原来,这两年间她对他的思念不是毫无理由的,而是埋着好感的种子。喜欢也有喜欢的苦恼,就是患得患失。明月虽然二十岁了,但是从来没有动过心。或者说,因为禽兽继父,让她对男性天生就有种排斥。奇妙的是,晨星不在这个排斥之列。他有种奇妙的能力,能让人信任,而事实证明,他也值得人信任。他能给她温暖,也许那点儿温暖对他说不算什么,对她,没有可就冻死了。
“快过年了。”他又发了这么一句。他说话也是,发短信也是,有时候只发前半句,让她猜不透他到底在想什么。
她暂时没有回,因为浑身还是难受得厉害,站一会儿就直犯恶心。她披上衣服,往楼下去。的确是快过农历新年了。想想看,长这么大,生日和过年,没有一件值得开心的。每当过年,母亲像佣人,带着她到白老大的家里张罗年夜饭。白家的几个媳妇儿十指不沾阳春水,在那里嗑瓜子聊天,任她们母女俩从白天忙到晌午。小明月择菜、洗菜、端菜,她母亲负责煎炒烹炸。
一桌子菜上了桌,她们举杯欢庆,母亲还在厨房忙着炸春卷。她的汗从脸上流到身体里,可是厨房里并没有暖气。
“过年了,你可得送我礼物。”明月走下楼梯,低头回了一条短信。说起来,除了竹竿留给她的mp3,她真的没有收到过什么礼物。因为没有过,所以期待。
“好。可是送什么好?”
路灯开着,一片路都是亮的。这是当初她在这里租房的重要原因。她要看着灯。一路走进了楼下的诊所。前面东倒西歪地排着几个人。那些人的影子模模糊糊,变成重影儿,她有些晕,靠在长椅上睡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