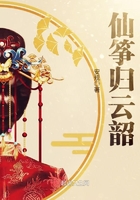第二章 因病停演 (32)
“你放心吧!”部长答应。
“好啦!谢谢,再见了!——来吧,先生?”他对兄弟说。亲王表面上目光镇定地望着两兄弟,他们的举止、体魄和性格如此不同:一个勇敢,一个懦弱;一个淫逸,一个严肃;一个诚实,一个贪污;他心想:“这懦夫不会去死的!而我可怜的于洛,那样廉洁的人,死亡就在眼前了!”他在扶手椅中坐下,重新拿出非洲的公事来看,动作中同时体现出指挥官的冷静和对战争景象的深刻怜悯!因为,事实上没有人比军人更富于人情味,尽管表面粗鲁,而且作战的习惯养成了战场上绝对必须的冷酷。次日,几份报纸在不同的标题下发表了几则不同的文字:
“于洛?代尔维男爵阁下业已申请退休。该要员之决定辞职,闻与由两职员一死一逃而引起的阿尔及利亚当局的帐目不清有关。获悉部下犯罪,且不幸因该两名职员系自己信任荐任,于洛男爵当于部长办公室内因受刺激而瘫痪。于洛?代尔维阁下系元帅胞弟,供职已达四十五年。他不但精于行政,且私人品质亦为人称道;虽经挽留,但终因辞意坚决未果,甚为识者惋惜。其在帝国禁卫军华沙军需总监任内,以及1815年为拿破仑临时征召的军内组织各种事宜,均业绩卓著,至今仍有口皆碑。此事为又一帝国元勋离开舞台。于洛男爵自1830年起素为行政法院及陆军部不可或缺之干才云云。”
阿尔及尔讯——一度由某些报刊大肆渲染之粮秣一案,兹因主犯死亡而告结束。若安?菲谢在狱自尽,一同谋在逃;但此犯将受缺席判决。菲谢系军队老军需供应商,为人诚实,备受称赞。此次难以忍受在逃之仓库主任夏尔丹之蒙骗,故而自杀云。”
在巴黎社会新闻栏内,又有如下消息:
“陆军部长元帅阁下,为避免今后之一切流弊,决定于非洲设立一军需办事处。已调派科长玛内夫先生负责此机构事宜。于洛男爵之继任一事引起群雄逐鹿。据闻此职由议员、拉斯蒂涅克伯爵的内兄玛尔蒂亚尔?德?拉罗什—雨贡伯爵所获。行政法院审查官玛索尔先生可能任命为行政法院参议,而由克洛德?维尼翁继任审查官。”
在各种谣传之中,对于反对派报纸最危险的是官方的谣言。无论记者如何狡猾,他们有时会自觉不自觉地受骗上当,骗他们的人往往是昔日他们当中的同行,如克洛德?维尼翁之流,从新闻界转入政界权力高层的人。报纸只能被新闻记者攻倒。因此,我们不妨套用伏尔泰的句子:巴黎琐事并非是浅薄的人所想象的那回事。于洛元帅把兄弟带回家去。弟弟恭敬地让哥哥坐在马车后座,自己坐在前面。两兄弟没有交谈一句话。埃克托尔垂头丧气。元帅聚精会神,好像一个人正在集中力量准备托起千斤重担。回到府邸,他不出一声,用威严的手势把兄弟带进书房。伯爵曾经从拿破仑手中得到一对凡尔赛工厂制作的精美手枪。他从书桌里抽出枪套,那上面刻着皇帝拿破仑赐于洛将军字样。他指着手枪对兄弟说:“这是为你治病的医生。”在半掩的门里张望的利斯贝德,赶紧跑向马车,吩咐即刻迅速地前往普吕梅街。二十分不到,她就把知道了元帅威胁兄弟一事的男爵夫人带了回来。伯爵不看兄弟,打铃叫来了跟他三十年的当差老兵。
“博比埃,”他对老兵说,“你去把我的公证人、斯丹卜克伯爵、侄女奥唐瑟和国库券经纪人一起叫来。现在是十点半,我要这些人在十二点到。你去要车子……快了还要快!……他从前常常挂在嘴边的共和党人口头禅又说了出来。他又摆出了吓人的嘴脸。当1799年在布列塔尼与保皇党人作战时,他就是用这副神气使士兵们不敢怠慢的。(见《舒昂党人》)
“遵命,元帅,”博比埃行个军礼说。老人始终不理睬兄弟,回到了书房,拿出一把藏在写字台里的钥匙,打开了一只铜面上镶着孔雀石的首饰盒,这是沙皇亚历山大的礼物。拿破仑皇帝曾派他把从德累斯顿战役中缴获的战利品送还给俄国皇帝,用以交换旺达姆将军。沙皇极慷慨地作为回礼,把这首饰盒送给了于洛将军,并对他说希望有一天能给法国皇帝同样的礼遇;但是他并不放回旺达姆。首饰盒全部鎏金,盒盖上有金制的俄罗斯帝徽。元帅把盒内的银票及金币点了一下,共有十五万二千法郎!他不由得做了个满意的姿势。这时候,于洛夫人进来了,她的神态连政治法庭的法官都会为之心软。她扑向埃克托尔,用疯子般的神气不断地望着手枪套子和元帅。
“您为什么要整兄弟呀?我丈夫对您干了什么?”她的声音那么响亮有力,元帅居然听见了。
“他丢了我们大家的脸!”共和国的老战士回答,这一开口又触痛了他的伤疤。“他盗用公款!他使我的姓受人憎恶;他让我恨不得早死,他已经把我杀了……我还有活着的一点力量只是为了归还公款!……我在共和国元老面前,在我最尊重的维森堡亲王面前丢尽了脸面,我还错误地在他面前辟谣呢!……这还算是小事吗?这就是他对祖国的罪债!”他抹去了一滴眼泪。
“现在说说我的家庭吧!”他接着说,“我三十年来省吃俭用为你们积起来的生活开支,一个老军人节俭的心血,全被他抢走了!这就是我准备给你们的!”他指着桌上的钞票说,“他害死了菲谢叔岳,一个高尚和正直的阿尔萨斯儿子。他可不像这位,能够忍受在农民的名字上抹黑。还有,宽厚为怀的上帝允许他在所有的女子中挑选一位天使!他有齐天洪福娶阿德莉娜为妻!但是他背判了她,一次次地让她悲伤,把她丢在一边,去找些婊子、淫妇、贱女人、女戏子、卡迪娜、若泽法、玛内夫之类……这就是我一向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自己的骄傲看待的人……走吧,冤家,如果你要过让你堕落成这样的下流生活,滚出去!我!我实在没有勇气诅咒一个我这么爱的兄弟;我对他像你一样的无能为力,阿德莉娜;可是他再也别在我面前出现。我禁止他为我送丧,跟在我的棺材后边。即使他不思悔改,也应该有点知罪的廉耻吧!……”说完上述庄严的话,元帅脸色惨白,跌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也许是生平第一次,两行泪水流出双眼,在腮帮上徐徐淌下。
“我可怜的菲谢叔叔!”利斯贝德呼喊着,用手帕蒙住眼睛。
“大哥!”阿德莉娜跪倒在元帅面前,“为了我,您要活下去!帮助我,我要让埃克托尔改邪归正重新做人,让他将功赎罪!……”
“他!”元帅说,“如果他活着,作孽还没有完呢!一个糟蹋阿德莉娜这样女子的人,一个把真正共和党人的感情和我拼命灌输给他的爱国家、爱家庭、爱穷人的品质都丢光的人,是魔鬼,是禽兽!……如果你还爱他,把他带走吧,因为我感到内心有一个声音在叫我一枪让他的脑袋开花!打死他,我便救了你们大家,也救了他自己。”老元帅恶狠狠地站了起来,吓得阿德莉娜惊叫一声:“来呀,埃克托尔!”她抓着丈夫,把他带着离开了房子。男爵浑身发软,她只得雇了一辆马车将他带回普吕梅街。他一到家就睡上了床。这个几乎瘫软如泥的人一连睡了好几天,拒绝进食,一言不发。阿德莉娜哭哭啼啼才使他咽下几口汤水;她坐在床头看护他,再也没有了不久前充满内心的怨艾,只有深深的哀怜。十二点半,利斯贝德把公证人和斯丹卜克伯爵引进了她亲爱的元帅的书房;她见到他脸上的神情大变,害怕得寸步不离了。
“伯爵阁下,”元帅说,“我请您签署一份必须的许可状给我侄女即您的妻子,让她出售那份空有产权的年息存单。菲谢小姐,你要同意放弃对这次出售的用益权。”
“是,亲爱的伯爵,”利斯贝德毫不犹豫地回答。
“好,亲爱的,”老军人说,“我希望活着的时候能够报答你。我毫不怀疑你是个真正的共和党人,一个人民的女儿。”他捧起老姑娘的手吻了一吻。
“阿纳坎先生,”他对公证人说,“请您立一份必须的委托书,我准二点钟要,以便能在今日的交易所上出售。我的侄女伯爵夫人持有证券,她即刻就到,她将会同菲谢小姐一起在委托书上签字。伯爵将跟您到府上先签字。”艺术家见利斯贝德对他使了个眼色,便恭恭敬敬地对元帅行了礼,出去了。次日上午十点钟,福尔兹安伯爵去见维森堡亲王,立刻被接见了。
“好啦!亲爱的于洛,”科丹元帅把许多报纸递给他的老朋友,“你瞧,我们已经挽救了面子……你念念。”于洛元帅把报纸放在他老同事的办公桌上,再把二十万法郎交给他。
“这是我兄弟挪用的公款。”
“瞎胡闹!”部长叫道。他拿起元帅给他的助听器,对准他的耳朵补充说道,“我们不可能收这笔赔款,否则我们就将被迫承认你兄弟的舞弊行为;而我们已经安排好一切把此事隐瞒了……”
“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但我决不愿在于洛家的财产中有一个小钱是从国库中偷来的。”伯爵说。
“我会就此事奏请王上。我们别再谈这件事了吧,”部长回答道。他知道这老人的正直固执是不可能说服的。
“再见,科丹,”老人握着维森堡亲王的手说,“我觉得自己的灵魂已经结冰了……”然后,他走了一步后,回过头来,看见亲王情绪激动异常,于是张开双臂去紧紧拥抱他;亲王也拥抱了元帅。
“我觉得向你告别,就像向整个帝国大军告别……”
“再见了,我亲爱的老伙计!”部长说。
“是的,永别了,因为我要去的地方是我们曾经痛哭的士兵们所在之处……”正在此时,克洛德?维尼翁进了屋。拿破仑麾下两个宿将正在庄重地彼此行礼,已经抹去了一切激动的痕迹。
“亲王,您该对报上的消息满意了吧?”未来的审查官说。“我使了一点手段,让反对党的报纸还以为公布了我们的秘密呢……”
“可惜,一切都无济于事了,”部长看着元帅从客厅走了出去。“我刚才说的诀别使自己非常难受。于洛元帅没有三天好活了,我昨天就已经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这个人,正直廉洁,炮弹都要因他的勇敢而远敬他三分的……瞧,就在这儿,在这张扶手椅子里,……却受到了致命的打击,还是从我的手里,仅为了一张纸!……请打铃,吩咐套车。我要到纳伊利去见王上,”他说着把二十万法郎塞进他的部长公文包里去。尽管利斯贝德细心照料,三天之后,于洛元帅还是死了。这样的人便是他所在党派的荣誉。对于共和党人来说,元帅是爱国主义的典范;因此他们都来送丧,后边跟着无数人。军队、政府机关、王室、老百姓,大家都来向这位德高望重、清廉正直、纯洁光荣的军人致敬。老百姓来送丧不是谁想要他们来就能做到的。这次丧礼充分地显示出敏感、高尚和真诚,相隔很久仍使人体会到法兰西贵族的品德与荣耀。元帅的灵柩后面还有蒙托朗老侯爵,他的哥哥在1799年舒昂党人的叛乱中曾是于洛的手下败将。侯爵因中了蓝军的子弹而临死时,曾把他弟弟的产业托付给这位共和国的军人。(见《舒昂党人》)于洛接受了这口头托付,居然成功地救出当时侨居国外的年轻人的财产。
因此,九年前战胜保皇党人的共和党军人,身后仍获得了法兰西旧贵族的敬意。元帅之死发生在颁布最后一道婚约公告前四天,这对利斯贝德无疑是晴天霹雳。连谷仓带收藏的谷物都全部烧毁了。洛林姑娘做事未免过于顺利了,乐极生悲。元帅就是死于她和玛内夫太太对这家庭接二连三的打击。正在大功告成,老姑娘的仇恨得报的时候,忽然希望成了泡影,于是仇恨更加增大了。利斯贝德跑到玛内夫太太家痛哭流涕;因为元帅租的房子签的是终身契约,她现在变得无家可归了。克勒韦尔为了安慰瓦莱里的好朋友,拿了她的积蓄,更加慷慨地加上一倍,用五厘利存好,产权归塞勒斯蒂娜,用益权归贝德。这么一来,利斯贝德就有了两千法郎的终身年金。在清查财产的时候,他们找到元帅的一份遗嘱,要他的弟媳、侄女奥唐瑟和侄子维克托兰三人共同负责付给他的未婚妻利斯贝德?菲谢小姐一千二百法郎的终身年金。阿德莉娜见男爵生死未卜,就把元帅的死讯向他隐瞒了几日;但利斯贝德来时披麻带孝,他终于在丧礼后十一天得知了凶讯。这可怕的打击反而使病人提起了精神,他起了床,看见全家穿着黑衣服,聚集在客厅里;见他一露面,全家都不出声了。半个月里,于洛瘦得像个鬼魂,大家如见到了他本人的影子。
“应该想个办法,”他在一把扶手椅里坐下,声音无力地说。他见除了克勒韦尔和斯丹卜克,整个家族全聚集于此。
“我们不能再住在这里,”男爵出现的时候奥唐瑟正在发表意见,“房租太贵了……”
“至于住的问题么,”维克托兰打破了难堪的沉默,“我供养母亲……”听到这句似乎要撇开他的话,男爵把本来低着的光凝视地毯上的花纹而不看众人的脑袋抬了起来,对律师儿子可怜巴巴地望了一眼。做父亲的权利永远是神圣的,即使当他是个堕落和身败名裂的人也一样,维克托兰因而马上停住了话头。
“供养你的母亲……”男爵说,“你做得对,我的儿子!”
“套间在我们的上面,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