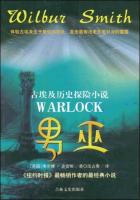两人谈话渐渐融洽,又聊起了田代的个展。这回轮到摄影外行纶太郎受冷落了。他对胶片的正负与石膏直接制范的外范和芯范的共通点已有理解,但是谈到曝光和显影的话题就完全跟不上趟了。但即便如此,纶太郎依然感到把田代领来是正确的选择。因为身穿丧服的江知佳只有在谈论摄影时,才微微露出与20岁女孩相称的神态。可能就是因为出现了触动摄影师心弦的提问,田代的建议也充满了热情。纶太郎心想,不在这种席间而是在别的场合让他们见面就好了。不过,事已至此也只能顺其自然了。
纶太郎也十分清楚,对于此刻的江知佳来说,这不过是非常短暂的喘息机会。正是由于身处这种状况中,她才更需要这样的放松时间。因为,即使现在父亲的死依然沉重地压在心头,她也必须尽早摆脱重负,着眼于自己的未来。
纶太郎摒除了心中艳羡,希望她跟自己所崇拜的摄影师交谈,借此机会摆脱重负。就在这时,田代周平口中突然蹦出了意料之外的人名。
“刚才,你叔叔向我打听堂本峻这个摄影师的情况。”
纶太郎不由得紧紧盯住田代的脸。莫非……刚才给他的教训过猛啦?但田代用眼色制止纶太郎插嘴,他似乎有所考量。
江知佳猛吸一口气,身体僵直不动,刚刚恢复活力的脸庞眼看着就阴云密布起来。那是在不愿触动的伤痕上猛吹一口气的反应。她用前所未有的强硬语调反问:
“他的情况您知道吗?”
“以前知道一点儿。那是个很小的世界,大家都很熟悉。江知佳小姐曾经当过堂本的摄影模特吧?”田代口无遮拦地说道。
江知佳有些戒备似的点了点头。
“三四年前,他通过父亲的熟人介绍把我叫去。那并不是什么美好的回忆。”
“我估计也是那样。对不起,我以前听到过那种流言。听说堂本非常迷恋你,有段时间对你纠缠不休,是吧?就像跟踪狂。”
“那是什么……”
田代用手势阻止纶太郎发问,双眼不离耷拉着脑袋的江知佳的脸,目光像在强调:这没什么难以启齿的。
“那流言真有其事。那是在高中时代,我也还是个孩子。”
江知佳像在整理心绪……沉默了许久,最后终于开了口。
“最初我被他花言巧语捧得忘乎所以。因为每次拍照我都会产生错觉,以为自己变成了另一个人。可是后来,我很快就难以适应那个人的做法了,他就像走火入魔似的从早到晚连续不断地按快门,我就觉得自己像是在每个瞬间被切割成了碎片。我渐渐对那个人产生了恐惧感,于是对他说我不再当模特也不愿再看到他了。他就突然恼羞成怒……”
江知佳吞吞吐吐,异常痛苦地摇了摇头,一定是经历了难以启齿的人间炼狱。纶太郎想起了川岛敦志的话——她曾跟不三不四的男人交往,被忽悠得很惨,指的可能就是堂本峻吧?田代无言地点点头,江知佳像是以此为信号叹了口气……接起中断的话头。
“从那以后半年左右,我不断地被跟踪、被偷拍,还接到骚扰电话。我不想让父亲担心,就一直没告诉他,但后来终于忍到了极限……我痛下决心说明了情况,让父亲采取了应有的措施。父亲并没有报警,据说动用了多方门路,还采取了施压或类似于威胁等粗暴的方式。但父亲并没有告诉我具体情况。不过,这样他总算不在我面前出现了。而且,照片底版也要回来一张不留地烧掉了。”
“作为你的父亲,伊作先生付出了最大限度的努力。即使他已经过世,也请不要忘记这件事情。”田代用有违自己个性的语气说,似乎经过了深思熟虑,“不管方式怎样粗暴,我认为跟堂本断绝来往是正确的选择。如果你向你父亲说得晚了,恐怕你自己就要先崩溃了吧?或许堂本的摄影技术高超,但我无论如何都不喜欢他的照片,因为我觉得他看拍摄对象的目光本身已是扭曲的。这并不是题材和技巧的问题。他最近好像没有什么稳定的工作,也没听说干了什么好事儿,还有传言说他在利用照片敲诈混饭吃呢。”
“是吗?”
江知佳小声嘀咕,表情倒并没有显得非常惊讶。但换一种眼光来看,她只不过是装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而已。
“那些毕竟都只是流言层面上的说法。哦,现在堂本怎样已无关紧要。我是听前辈说到江知佳小姐对当模特产生了抵触情绪,才想到会不会跟这事儿有关。那也不能怪你。你只是被堂本的相机镜头所蛊惑。我就是想让你认清这一点……对不起,刚刚认识就冒昧说这么多。如果令你感到不愉快,我道歉。”
田代点头致歉。
“没有。”江知佳略显犹疑地摇了摇头,“听田代先生对我这样说,我非常高兴。谢谢您。”
7
休息室的门敲响,国友怜香探进头来告诉大家,马上就到离开的时间了,请大家做好准备。
“我打扰太久了。该告辞了。”田代周平看看表不好意思地说道。
可能是堂本峻的话题在两人间留下了芥蒂,江知佳也没有表示挽留。先前那么融洽的气氛就像幻觉般消失了,两人的对话如同陌生人。
收拾好手边的携带物品,远亲们陆续跟正在收拾休息室的江知佳道别。斋戒席说是已在内部送葬时办过,当日不再设宴席。纶太郎觉得,让亲戚们就此解散,其实是打发众人回家的借口。
纶太郎在蓬泉会馆大厅送走田代之后,坐上一辆黑色包车前往川岛伊作的住所。江知佳、怜香伴着逝者的骨灰同行,装在金丝织锦袋里的桐木骨灰盒就放在江知佳的膝头。
出租车驶下町田街道来到市中心,越过小田急小田原线后不久,就停在了南大谷宁静的住宅区一隅。从最近的车站来看,这里位于玉川学园站与町田站中间,以樱花长廊著称的恩田川在路旁流淌。纶太郎曾在川岛伊作的随笔中读到过,川岛曾半夜沿着河畔的自行车道徘徊……
川岛家的正房是两层楼,一座带有门厅引廊和凸窗的西式建筑,屋顶却是山形的覆瓦样式,以现代建筑法模仿战前洋房的风貌。据说川岛伊作喜好东西合璧样式,这座楼是江知佳刚出生时新建的居所。独立的工作室在正房背后,从前面无法看到。
“你们回来啦!葬礼还顺利吗?”
来到门厅迎接的是一位系着新潮围裙、和蔼可亲的大婶,年龄约莫60岁出头儿,身材矮胖动作却很麻利。江知佳随口应答过后,就向纶太郎介绍她。
“这位是精明干练的管家——秋山房枝太太。”
纶太郎后来听说,房枝不是全职管家,而是每周四从鹤川的公团公寓乘公交车再换电车来这儿。她得到川岛家这份工作已十年以上,已是家里的资深保姆,早就被认定为家中一员。只是她得照料经常患病的丈夫,不能把自己的生活完全转移到这边来。
但即便如此,川岛家的主人去世后,她连续留宿多日,包办了所有的家务事,还不遗余力地照顾江知佳。今天婉拒参加告别仪式,就是将留守逝者家中当作了首要任务。据说房枝坚持——工作室里的石膏像遭到了破坏,所以,家中更不能无人留守。
纶太郎打过招呼后,房枝就像久居家中的老猫露出一切了然于胸的神态。
“你是敦志先生的朋友吧?谢谢专程前来。请进吧!雨伞立在伞架上就行了。国友女士也请进。诶?关键人物阿叔呢?”
“他还在殡仪馆。只有我们和父亲一起回来了。”
江知佳说完,怜香接着解释道:
“他还得处理会场的善后事宜和杂务,办完事儿就跟宇佐见先生一起过来。大概还需要一个小时吧。”
“是吗?宇佐见先生也要来啊!这就是全部人数么?那大家晚上都在这儿用餐吗?”
纶太郎望着怜香的脸点点头。马上就到5点了,等川岛敦志和宇佐见彰甚回来后才开始调查工作室的话,晚餐前离开便是无法办到的事情。
在一楼神龛加设的祭坛上安放了遗骨和牌位之后,每人依次向遗照合掌默拜。祭拜完毕,江知佳露出一下泄完了气的忧郁表情,问怜香可否换掉丧服。
“是啊!你太累了,换了衣服顺便休息一下吧!”
江知佳听到这话,像是突然切实地感到自己已经疲惫不堪了。
“那就等阿叔他们回来再叫醒我吧!”
江知佳留下这话,对纶太郎行个礼就上二楼自己的房间去了。
房枝沏好茶摆在面对庭院的客厅餐桌上,随即也撤回了厨房,空荡荡的房间里只剩下全身黑衣的怜香和纶太郎。
怜香一坐到沙发上,就打开提包取出薄荷型香烟和打火机。好像她在告别仪式会场就一直忍着。从她吸上几口旋即放松的表情看,明显跟川岛敦志和法月警视是同一类型。
“告别仪式没看见你。一直在接待处吗?”
“我是幕后啊!快结束时才进了纪念大厅。我也上香了。今天这就足够了。”
可能是一切都想清楚了,她的回答出乎意料地直截了当。
在蓬泉会馆,好像出入休息室都要等远房亲戚全部离开,而现在……可能是身处逝者气息浓郁的房间,她的态度才比在大厅接待处交谈时更为放松。
“你说快结束时?那你没看到……上香时,江知佳叫住了名为各务的男子么?”
“我听说了。虽然我不在现场,但在接待处见过他,所以知道各务先生来了。他是律子夫人也就是阿江母亲的再婚丈夫,你已经知道了吧?”
“是的。那,你以前也见过他吗?”
“见到真人今天是第一次。不过,我看到登记表上的签名立刻就知道是这个人。当时我没对他说什么就那样过去了,我想对方也没把我放在心里。”
“他的全名是什么?”
“各务顺一。顺序的‘顺’,数字的‘一’。住址写的应该是府中市。”
“……是府中市民啊!根据我的印象,从两人当场的对话来看,在各务夫妻和伊作先生之间,依然留存着某种感情芥蒂——就像是隔板吧?而且,据说律子夫人连做母亲的责任都放弃了。不过各务先生在遗照前态度不逊的原因,我现在还搞不太明白。”
怜香像是有些困惑,表情阴沉下来。纶太郎觉得自己已经尽可能委婉地提问,但看样子还是触到了禁忌。怜香把窘迫的叹息裹在紫烟中,做了个缩肩膀的动作。
“请原谅。我没打算故作不知,但关于这件事情,我觉得你最好去问当弟弟的敦志先生。川岛跟律子夫人离婚是在我跟他相识之前,而且川岛也不想说——过去的真实缘由到底怎么回事儿。从我口中说出来不太……”
她像是嗓子有些堵,停下来并摇了摇头。
如果在纪念大厅偶然听到的情况属实,怜香不愿触及川岛夫妻离婚事件的不幸缘由,也在情理之中。她当然会有自己的考虑,否则对待逝者的方式也会有变化。她似乎并不打算明确地表达。纶太郎不想影响怜香的情绪,于是把话题转到较为平稳的方向。
“你跟伊作先生认识有多长时间了?”
“整理随笔集《眼睛上的煤矿工人》是第一次合作。那是1989年出的书。当编辑后交往了十年多。当然,为了维护川岛的名誉我要事先说明,刚开始我们纯粹是工作关系,在私人层面可完全没有这样那样的接触!”
“……是不是有什么机缘,使你们突然接近?”
“哪儿有什么突然接近啊?为了东欧美术馆纪行系列我跟他同行,在布拉格碰到阴损的扒手,两人的护照都被偷走了。我们跑到当地大使馆,好歹算是安全回了国。不过,当时两人都吓得脸色煞白……现在想来,反而觉得好笑。”
怜香嘴唇露出微笑,眼眶看似有些湿润。
“其实,也许我们还得感谢那个扒手呢!因为我们看彼此的眼光有所改变就是通过那个机缘。不过这种故事稀松平常,对于第三者来说,可能什么意思都没有吧?接下来的发展就请自由想象吧!”
纶太郎望着怜香捻灭烟头的动作,做出了稀松平常的想象:在布拉格街头脸色煞白狼狈不堪的主要是川岛伊作,而年轻的怜香肯定比他沉稳得多。当时出现了触动母爱本能的场面,可能……她就是从那时起,下定决心要由自己来保护这个人吧?
“听说几年前提出过再婚的话题,是吧?后来犹豫不决没办手续,好像……主要是顾忌江知佳小姐的存在。”
“听敦志先生说的?是啊,不能说全都是那个原因,但那毕竟是没能踏进婚姻殿堂的最主要的原因。”怜香双臂交抱胸前,用不容否定的语调说道,“她也正好处在情感最为复杂的年纪,性格方面也有……相当不稳定的因素,所以我认为不宜将大人的意愿强加给她。我自己也有那个年代的记忆。阿江懂事之后只有父亲。对不对?这就更麻烦了。我俩左商量右商量,决定把那事儿往后放放。”
“那样行吗?”
“他好像觉得过意不去,我觉得这样反倒轻松。而且对于阿江来说,这应该是最好的方式吧?我到现在,也没有因为发展成这种结果而后悔。”
怜香挺起胸来表示自己心中早就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但是,春天做完手术后,风向是不是有了很大的变化呢?原因你是知道的吧?伊作先生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了。”
“莫非这也是听敦志先生说的?”
“……前晚电话里说的。伊作先生没对你说过,去世前至少去办个登记手续么?”
怜香为掩饰不安神色缩紧双颊,并做出仔细聆听楼内动静的姿态,过了片刻叮嘱纶太郎说——这事儿只能你知我知。
“他在去世一个月前,说过一次。不过我没有点头,他便再没提起这事儿。”
“为什么呢?”
“我一旦决定的事情就不想反悔。而且,如果办了的话,我还怎么有脸面对留下的阿江呀?”
“可跟以前不同的是,这回她为了接受你,也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对吧?敦志先生说到这事儿时,也感觉十分遗憾呢!他说——如果我哥能再多活些日子的话,阿江就会同意父亲再婚了。”
“是啊!那是我最痛切的感受。”怜香坦率地承认事实,“我不知对他说过多少次,不必那样勉强。不过,如果我确定要当阿江的新妈妈,这么大的事情根本不可能瞒着她做出决定。可是真的把话说出来,就等于默认她父亲的死期迫近。我们一直在隐瞒病情,所以这是绝对不能说的。即便不是这样,匆忙办理结婚登记,肯定会有风言风语说我是为了遗产。不是吗?与其说将来一直生活在那种有色眼镜的目光下,还不如保持现状呢!”
她的辩解确实在理,但说到往后怎样发展,就是另一码事儿了。纶太郎明知这是多管闲事,但还是询问怜香今后打算怎么办。
“还是别问这个了。目前,大概要忙于整理川岛留下的成果。撇开母亲身份之类的问题不论,也得作为家长替阿江考虑。不管怎样,在11月的回顾展结束之前,应该无暇考虑自己今后的去路。”
怜香用手指捏着第二支香烟,像指挥棒似的揉搓着。她迟迟没有点着香烟,或许就是不愿考虑将来事情的真情流露。
“说到回顾展,你跟策展人宇佐见先生合作顺利吗?有评价说,他是大野心家。”
“他就是那样的人啊!”或许是因为话题离开了自己,怜香放松了心情,终于点着了香烟,“好像死对头也相当多。”
“有两个家伙说——伊作先生突然逝世都怪他急于发表新作累坏了呢!纪念大厅里我身后座位的两个貌似美术界的人士说的。”
怜香皱眉蹙脸轻蔑地吐出一口烟雾。
“那些家伙的嘴脸就像浮现在我的眼前。但是,那样武断地下结论对宇佐见先生不够公平吧?他精于算计的性格确实令人生厌,但即使以我的眼光观察,他尊敬川岛先生是真心实意的。”
“你能说那是确切无误的吗?”
“我自认看人的眼光还行。如果不是这样,你觉得我会对今天才见面的人这样开诚布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