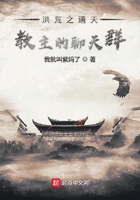北风呼啸,从深夜到黎明,渐渐吹散浓重的雪雾,吹散漫天的层云,待得青光破晓,又将一抹璀璨的旭日光辉吹落归元山巅。
三层祭台之上,九丈长天之下,南门宴长身北向,古朴而又沉实的神龛跟前,黑袍兜头的偃师都身如熟虾,额抵苍雪,口鼻间污血淋漓,眸光惊惧,早已面目全非,纵使有心挣扎求饶,但手足俱缚,舌根尽断,也是回天无力。
祭台之下,山巅南畔,掣老携幼八百余族民簇拥并立,一个个高昂着头,举目遥望那仿若沿阶递相远去的身影,感觉熟悉而又陌生,有的暗自欣慰,有的徒增迷惘。
寒风渐吹渐渺,冬日渐照渐高,直至辰时初刻,方见水木华和金不易携袂而来。二人匆匆登上祭台,看到披着黑袍跪仆在神龛前的偃师都,彼此神色间俱都透着一丝意外与凝重。
南门宴仔细打量了二人一眼,见水木华面色青白,金不易金面透紫,似都消耗非小,又见二人衣袖间隐隐沁染数点血花,心下了然,眉心暗蹙,淡然问道:“老师,金先生,不知淮长老和葛长老身在何处?”
水木华脸色微变,转眼看了看无动于衷的金不易,执手说道:“秉少主,属下明察暗访,多方印证,发现葛青松确与刑堂勾连甚深。数日前,葛青松借故离开,至今杳无音讯,想必是有所察觉,畏罪潜逃了。至于淮炎玉,纵子行凶,协众叛逆,已为属下与金长老诛于北山之外。”
水木华话音朗朗,毫无遮掩,祭台之下八百余族民俱都听得一清二楚,一时间无不胆颤心惊。如果说南门宴昨夜长桥一战败退淮山,令他们感到意外,那么今日北山之外诛杀淮炎玉,则是令他们感到畏服。看着祭台之巅面不改色的少年,无不心生恍惚,众人一曾嘲讽的“废物”,不知从何时开始已然身具威仪。
南门宴容色恬淡,剑眉微蹙即舒,转身向北:“既如此,人已到齐,开坛祭天。”
水木华恭谨称是,神龛上的祭品早已齐备,只需转身宣告:“唐尧九十六年冬,吾皇敬天,少主代为长祭,跪!”
水木华一声宣罢,祭台下八百余族民应声跪倒,五体投地,一股肃穆之气扶摇直上,遍布归元山巅。
水木华长气轻舒,回身与金不易并肩跪立。南门宴端容正步,缓缓走到神龛下匍匐在地的偃师都身前,探手扶握长剑,一寸寸抽拔而起,眼中寒芒渐凝,势必将偃师都斩于剑下,以血祭天。
然而,南门宴拔剑未半,忽又心生感应,抬首望天,只见一人黑袍罩面,负手长立于百丈虚空之外,身姿魁伟,势气凛冽,那双掩藏在宽大斗篷笼罩下的黑暗中的眼眸,锐利如锋,寒芒好似洞穿了百丈虚空,扎得他眼角酸疼。
在南门宴心神震动的瞬间,水木华和金不易俱都心有所感,抬眼相望,只见一道黑影宛若苍鹰一般朝着祭台扑来,霎时间神色激变,弹跃而起,化作两道长虹飞越神龛,于四十丈外和那黑影激战开来。
一时间,长空之上拳掌纷飞,剑芒扑朔,空气爆裂,声如雷动,劲风呼啸,阳辉飘摇,空旷寂寥的归元山巅,一声声惊呼乍起,匍匐在祭台之下的八百余族民俱都骇然相望,心怀惴惴。
南门宴看着激战处偶尔有如血红芒一闪而逝,眼中寒芒更甚,拔剑的右手未止,嘴角边掠起一抹鄙薄似的轻笑,咔一声轻响,寒光出鞘,一阵狂风从天上呼啸而来,正好掀下笼罩在偃师都头顶上的宽大斗篷,剑锋闪烁,在偃师都惊惧莫名的注视之下劈斩而过。
在八百余族民瞩目之际,在久违的冬阳辉照之下,鲜血淋漓若雨,沁染在空旷明净的长天之间,沁染在黑沉如夜的神龛之上,不甚狰狞,反似散落的焰火般瑰丽璀璨。当偃师都惊怖满面的头颅飞落神龛,咚咚然好似钟鼓雷鸣,南门宴稚气中饱含冷冽的声音响彻天地,震动心魂:
“驱我五族者,虞舜;弑我万民者,刑堂。今以刑堂鬼厉之血,长祭九天,日月为证,厚土为凭,吾南门宴在此立誓,必将穷吾三生九世之功,北还家国,诛杀伪帝,若背此信,当如此剑!”
言罢,南门宴抖手扬剑,悍然斩落在神龛之上,只听得哐当一声巨响,青光长剑寸寸崩断,散落满地。
祭台之下,八百余族民怔然若梦,直到南门宴朝天九拜,方才醒觉,顿时一个个相继叩首,虔诚肃穆,砰砰然响彻山巅。
……
……
祭台之外,长天之上,水木华与金不易联手激斗身披黑袍的南昌河,纵是风起云涌,声威赫赫,却也久战不下,从归元山巅到北山之北,又从北山之北到归元山巅,所过处山石崩飞,古木摧折。直至此时此刻,南门宴才对诸如水木华、金不易、南昌河等人的修为有了一个大概的判断——至少俱都身在『玄宫』秘境之上——唯有『玄宫』秘境之上方可御空而行。
眼见战局焦灼,一时难分胜负,南门宴不欲等候,探手扒下偃师都身上的水火不灭黑风袍,又用托盘盛了偃师都的头颅,转身大步走下祭台,径直回往圆盘寨子而去。
回到族长大屋之后,南门宴将堂屋里的篝火烧旺,往东厢草草收拾起一个细软包裹,复又回身堂屋,端坐几前,取炭火煮水烹茶。未及茶过半盏,便听得密集的脚步声奔涌门前,举目相望,正见南昌河扶着金不易跨门而入。
金不易的面色紫中透青,气息衰弱,显是受创不轻。南昌河扶着金不易坐到几前,皱着眉头沉声说道:“送雪儿北上的路上出了点意外,以至于回来得终究晚了一些,水长老已经去了,金长老也身受重伤。”
南门宴端着墨玉青璃盏的双手微微一滞,继而轻轻落盏,抬手为南昌河与金不易斟上热茶,淡然说道:“义父回来得正是时候,此间事情已了,我须趁早南下,族中事务还需义父与金长老操持呢。”
南昌河深深看了南门宴一眼,见其毫无异色,不由凝眉问道:“何故走得如此匆忙?”
南门宴抬手指了指一旁托盘上偃师都的头颅,皱眉说道:“我必须把他带走。”
南昌河转眼看了看偃师都污血淋漓的头颅,皱缩着眉头不言不语。
南门宴自顾说道:“据说南疆会有大事发生,我此去路过谷城,正好借此头颅一用,先搅浑了谷城这潭水,义父也好趁此机会巧作布置,或断除淮炎玉一族与偃家的紧密联系,或进驻谷城反客为主,俱无不可。”
去除淮炎玉,五族归一,此后南门宴南下求仙问道,以期破道修行,这是在南昌河潜送南牧雪离开之前就已定下的决策。此刻纵使南昌河心有不愿,也不好当着门外众族民的面批驳南门宴那名正言顺的理由。
南门宴不管南昌河已然略略阴沉的脸色,昂首饮尽半盏清茶,探腰起身,执手长揖,恳声拜道:“族中长老已五去其三,正是我族力量空虚之际,然刑堂志在于我,恰值义父与金长老刚刚击退强敌,亦是我离开的最佳时机,我一走,刑堂必定跟随南下,藉时我八百余族民无忧矣。”
南门宴直起腰身,见南昌河沉着脸不说话,复又长揖一礼,郑重说道:“义父保重。金长老保重。”
说罢,南门宴转身大步走进东屋,不一时便斜背着一包细软出来,用一只兽皮袋兜了偃师都的头颅,默默朝着南昌河执手一拜,断然转身,昂首阔步,出门而去。围在族长大屋门前的族民,看着他这么一副慷慨赴义般的凛然姿态,不由暗自感动,眼睛里透着前所未有的恭敬。
南门宴目不斜视,径直往族长大屋旁牵了匹龙鳞黑马,转而走出圆盘寨子,走过山风呼啸的石道,走过古朴厚实的长桥,一直到玉溪南岸阳光普照之地,方才探手入怀,抖开那袭水火不灭黑风袍罩落肩头,翻身上马,扬鞭远去。
龙鳞马身高体壮,四蹄健硕,奔行起来宛若风驰电掣,清冷中略微带着一丝暖意的阳光洒落肩头,南门宴的长发逆风飞扬,抛却满腔思绪,破碎的气海丹田尽复如初,借助『安若般若』法门已可入道修行,今又远离居心叵测的南昌河等人而去,一股前所未有的轻松自由的感觉翻涌心头,好不惬意。
日光渐照渐暖,山道渐南渐宽,疾行三十余里之际,南门宴迎风微眯的双眼猛地紧缩,瞳仁间两寸寒芒迸·射乍起,死死盯着前方百丈开外突然出现的十余个身裹黑袍的人影。
风一阵阵呼啸不绝,南门宴左手紧握缰绳,右手五指紧缩,于长袖之中握紧『屈子』短剑,双腿夹紧马腹,毫不迟疑地迎面冲将上去,只要身蜕樊笼,纵死亦不回头。
南门宴决绝向前,眨眼间便到阻敌身前,然而尚未待他出手,忽见一阵红色旋风横刮而至,从那十余个黑袍客身上席卷而过,裹起一股浓烈的血腥之气,翩然飘落隐没在龙鳞马背之上,一道清冷中带着嘲弄意味的话音飘摇入耳:
“你真的以为他们就这样轻易放任你离开?”
龙鳞马穿过未及飘散开来的血雾,迎着阳光朝南远奔,一缕熟悉而又陌生的淡淡清香飘逸在鼻息之间,南门宴的心底一颤而定——刑堂堂主!